十年砍柴:有美麗鄉村,才有美麗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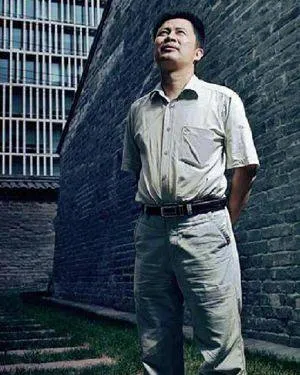
他從湘中山村走入黃河邊的大學,又從偏遠的西部前往滿城冠蓋的首都,從公務員、記者到歷史研究愛好者和知名評論人,“十年砍柴”李勇,用十八年時間完成了進城的過程,鑄就了一把屬于他自己的鋼筋水泥森林里的斧頭。
于是,他持斧伐柯般從故紙堆里尋覓醒世恒言,在這個不斷變幻的國度內尋覓普適價值,包括尋覓自己記憶中的故鄉。2011年,他出版了半自傳散文集《進城走了十八年:一個70后的鄉村記憶》,在城鄉結構巨變、農耕文明幾近消亡的今天,為他在故鄉生活過的片斷獻上了一曲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挽歌。
他說,“我們是唱著農耕文化的挽歌進城的”,在這一代人身后,是日漸消亡的傳統農耕文明。如今,中國的“70后”已跨入四十不惑,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這本書承載了他們人到中年的濃烈鄉愁,也觸動了這代人心中的某一根琴弦。
曾有人問他,“你為什么取十年砍柴這個名字?”他回答,“我確實砍了十年柴禾,我就是記錄鄉下的生活。”
如今,他的孩子和家在北京,房子買在北京,身份證上寫的北京人。但夜深人靜的時候想,他會覺得自己好像不是城市里的一員。原因是文化認知問題,“沈從文先生是我的老鄉,他19歲在北京流浪,他到死覺得自己是鄉下人,這個就是他對城市的認知,覺得城市沒有使他有歸屬感” 。
所以,他腦海中常常有一個念頭,對面那個人他的故鄉在哪里?
鄉村究竟是怎樣的?
《農家書屋》:對于您記憶中的鄉村,可以用幾個典型的畫面來描述一下嗎?
十年砍柴:我18歲前是在湘中鄉村度過的,正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對故鄉的記憶,現在概括起來,有這么幾個詞:清貧、閉塞、不乏溫馨與充滿希望。
一提起故鄉,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門口的一眼井。它不僅是全村二十戶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財產,在祠堂、族譜被迫消逝的數十年里,它是維系村里人的精神紐帶。還有幾個畫面,如我和小伙伴將牛放牧到山坡上吃草,然后聚在一起做游戲。還有就是在稻田里收稻子、過年時看舞龍燈,以及步行幾里山路去給外公拜年。
《農家書屋》:在您的書中,我們看到鄉村發生了很多變化,那最觸及您心靈的變化是什么?
十年砍柴:鄉村沒有了生氣,青壯年都已出去,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小孩,而他們的生活狀況,無論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令人堪憂的。
《農家書屋》:您怎么看待這些變化,或者說這個過程?
十年砍柴:中國人大批進城,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我這代70后農村孩子,可以說是最后一代在耕讀文化中長大的,經歷了中國鄉村社會幾千年來最大的巨變。我們也是最后一代只有精英才能進城的農村人。從我們這代人以后,進城不再是農村精英的專利了,而是大批地成群地進城。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告別“鄉土中國”,走進“城市中國”。耕讀文化幾近消失,這種消逝是不可逆的,因為社會結構發生巨變,“鄉土中國”變成了“城市中國”。
尋根之魅
《農家書屋》:《南方人物周刊》曾經將您評為“尋根之魅”人物,您寫《進城走了十八年:一個70后的鄉村記憶》這本書的出發點是想“尋根”嗎?
十年砍柴:這是媒體的過獎而已,我只想把過去的時光記錄下來,沒有“尋根”那么重要的使命。我覺得自己的經歷雖然平常,但是值得記錄下來,算是見證這個時代變遷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為例,我們兄弟從記事開始,融入以血親、姻親為經緯的熟人社會,那種自然狀態猶如幼魚游水、稚鳥學飛。我們首先要學會分辨的就是親屬尊卑,誰是我的親兄弟,誰是我共爺爺的親堂兄弟,誰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誰又是沒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嬸;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誰又更親近一些;方圓幾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們共一個祠堂,共一份族譜;祖父、父親、自己和下一代的輩分是哪個字;而八華里外的那個王姓聚集的村子,誰是我的親舅舅,誰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親和姨表親的區別在哪兒。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進祖墳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辦紅喜事該說什么賀喜的話,而對長輩的喪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
鄉村的熟人之間沒有秘密,一個家族的爺爺可以隨意在你家吃飯時走進來坐到餐桌上和你父親一起喝酒。這些對我這樣成長經歷的人而言,是常識,而對我們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遙遠的傳說。我覺得這種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的變化是巨大的,我有責任將這個過程記錄下來。
當然,還有一個私人的因素,就在這部書第二稿修改完畢的庚寅年臘月,我的兒子出生了。四十為父,感慨良多。立刻覺得那種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以及揮之不去的憂慮,為襁褓中的兒子,也為自己棲息的這塊土地。在北京這座近2000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里,陪我兒子成長的時候,我將如何給他講述南方那個遙遠的故鄉?如何講述他的父親從鄉村進城的經歷?或許,他會像我少年時對父親講述其成長苦難一樣不耐煩。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憑什么讓他洗耳恭聽父親的“憶苦思甜”?但是,既然將進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記錄下來了,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引發同齡人對那段歲月的回憶,希望更年輕讀者能接受他。也希望在更遠的未來,長大后的兒子通過這本書,讀懂他父親成長的那個時代。因為這個過程,對我來說,進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對整個中國來說,進城走了幾千年。
《農家書屋》:您認為的“根”是什么?“尋根”重要嗎?
十年砍柴:人生總是有來路的,一個人過去的記憶和經歷不可能完全切割掉,那么離開故鄉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尋根”的情感,只是有些人更為強烈,有些人因為謀生的壓力,沒有過多的時間去考慮這個問題。
《農家書屋》:我去白鹿原、高密等地采訪,發現民間出現了很多“尋根熱”這樣的現象,您怎么看這一主題和現象?它的價值何在?
十年砍柴:每個人、每個群落、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行走路徑。如果一條路變化不大,比如說某個人一直在農村里生活,很少離開故鄉,沒有生存環境的巨大反差,處在習焉不察的環境中,除非有高度文化自覺的人,否則很難產生“尋根”的意識。只有離開故鄉,進入一個與舊時生活經驗相差甚大的環境,才會有思念故鄉,從而產生“尋根”意識。一個民族也是如此,長期處在農耕社會,社會結構變化不大,這個民族不可能有“尋根熱”。只有處在現在這種三千年未有之巨變中,過去的剛剛消失或正在消失,“尋根”才會熱。
《農家書屋》 :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來后,很多人產生了回歸故鄉的共鳴,您覺得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共鳴?
十年砍柴:遙遠產生美,產生思念。如果真的現在回到故鄉,多數人會不習慣的。記憶有種過濾功能,我們想回去的,是那些不可能再重新出現的故鄉場景,而且是經過過濾的只剩下的美的場景。
鄉村存在的意義
《農家書屋》:其實,我們都是鄉村的孩子,那么,鄉村對于孩子的意義何在?鄉村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
十年砍柴:至少我們比城市長大的孩子多一種經歷。因為我們現在就身處在城市環境中,比起城市長大的同齡人,我們多一種對比的反差。這種反差帶來的影響,不利的方面可能我們融于現代職場生涯會慢一些,開始會顯得笨拙、土氣;但我覺得好的方面更多,至少對我而言,我們會用一種城市人少有的角度去看待世界。有時候這種角度其實更有利于我們對中國的人情社會、熟人社會的理解。
《農家書屋》:您曾用“突圍”來形容鄉村青年進城的過程,怎么理解這個詞?
十年砍柴:現在鄉村孩子進城容易,因為他們不得不進城,然而進城后獲得成功的難度更大了,因為社會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窮人孩子上升的通道越來越窄了。他們在求 學、求職時面臨的競爭環境確實不如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那樣公平。那時候高考雖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但一旦憑本事考上,會改變自己甚至一個家族的命運。可大學擴招后,農村孩子的努力被稀釋了,幾乎高中畢業都能上大學,而且學費昂貴。農村孩子找工作,拼爹、拼社會資源不如人家。所以更有一種突圍的悲情在里面。
鄉村未來的路在哪?
《農家書屋》:當農村失去了最有活力的青年,她未來的路在哪兒?
十年砍柴:未來的路在哪里?必須靠土地制度和戶籍改革。工業化社會不可能讓那么多青壯勞動者呆在鄉下,工業化社會或者說城市化社會,就是需要城市來吸納大多數人口。但把鄉村有活力的青壯年全部吸納走,顯然也是不正常的。當土地可以流轉,靠市場原則進行生產要素的配置,那么一定會有創造力的、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壯年回到鄉村——因為中國需要更豐富更安全的農產品,商機在鄉村。
《農家書屋》:現在很多城市精英開始從行動上反哺鄉村,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十年砍柴:現在這種反哺是不成規模的,或者說政策上有障礙。我在上個問題已經說到,關鍵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土地可以進入市場自由流轉,而附著于其上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跟上去,那么許多精英會自己選擇下鄉。靠權力主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注定是悲劇,只有市場主導,才可能長久,并步入良性循環。
《農家書屋》:您覺得,現在的鄉村,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她的孩子為她做些什么?
十年砍柴:讓農民真正成為土地和鄉村的主人。他們經濟上、政治上有自主權,再加上政府的引導與投入,教育與環保問題就會得到較好的解決。
《農家書屋》:在您的心中,有沒有一張未來鄉村的圖譜?
十年砍柴:農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不亞于市民甚至高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他們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與城市比沒有明顯的差別。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如此,美麗鄉村可期。有美麗鄉村,才可能有美麗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