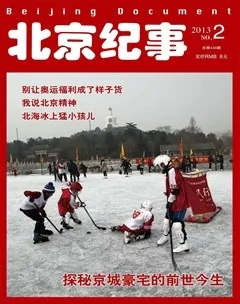吳昊頤:趙派藝術的主體在于內心感受
北京京劇團青年演員吳昊頤在入門趙派之前接觸過多個派別,也曾師從過閻桂祥、楊秋玲等藝術家。直到一次機緣巧合,她在北京京劇院的新編歷史劇《趙氏孤兒》中飾演“卜鳳”一角,出人意料地成功,被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張百發注意到。張副市長把吳昊頤引薦給了趙燕俠,希望她能繼承趙派的衣缽。
其實早先吳昊頤曾接觸過趙派,由閻桂祥老師教授的《白蛇傳》,吳昊頤還憑此戲拿了獎。吳昊頤覺得趙派雖說算是冷門,弟子不多,但是趙派有著強大的藝術魅力,深受很多老戲迷的喜愛。跟隨趙燕俠老師正統地學習趙派后,吳昊頤更是體會到了趙派藝術的博大精深,“趙派是體驗派和表現派的雙重結合,唱念做打舞都很綜合,所有的唱腔吐字都非常清晰。看趙燕俠老師的演出根本不用看字幕,一字一句都非常清晰,這也是趙派的特點之一。”要說趙派最核心的特點,就是以情帶唱。吳昊頤分析道:“就像張君秋先生的張派我也很喜歡,唱腔很華麗,他是以唱帶情,用技巧來渲染表演。但趙派是先入情,以說唱的形式表現人物來體現其唱腔藝術。基本上唱就跟訴說一樣,是一種訴。”
吳昊頤說起膾炙人口的《白蛇傳·小乖乖》一段的來歷,以前觀眾看《白蛇傳》都覺得《斷橋》是高峰,看完《斷橋》有的觀眾就離場了。趙燕俠就想:怎么能讓觀眾從頭坐到尾,讓這個戲不虎頭蛇尾呢?于是趙燕俠跟著名作曲家李慕良商量,再給《白蛇傳》后半段寫段令人叫絕的好戲。李慕良問趙燕俠:“你還不嫌《白蛇傳》唱腔多啊?”趙燕俠說:“我不怕累,就怕觀眾聽著不過癮!有的觀眾是專門沖著《斷橋》來的,聽完就走,所以請你在最后結尾的時候精心設計一段詠嘆調。”沒想到,一夜的功夫,李慕良先生就寫出了這段《小乖乖》。這段融合了兩位大師心血的精品之作甫一問世便震驚四座,成為難以超越的經典,包括里面的疙瘩腔,充分體現了趙派的運腔特點。趙燕俠每每演到此段,觀眾無不為之動容!趙燕俠要求吳昊頤用娓娓的訴說來表達對孩子的愛,“趙老師總說我們這一代演員太淺薄了,總想顯示自己的嗓音特點,總像在喊戲。演戲是演人物,把人物的靈魂展現出來才能留住觀眾。她要求我在唱這段的時候不要用太華麗的嗓音去裝飾,而是樸樸實實地訴說。一旦進入角色,無論你的嗓子出現什么狀況,已經完全超越玩技巧的階段了。最后趙老師小聲唱給我聽,可唱得我特別激動。特別是最后‘親親兒的臉,聞聞兒的腮……’這種母親對孩子的感情怎么能大聲去宣揚?我一邊唱,趙老師一邊小聲指導著我,讓我受益匪淺。”
吳昊頤說,趙派藝術也不只有低吟,該輕的輕,該重的也要重,跳進跳出的技巧、對火候的掌握是最難把控的。《白蛇傳》最后結尾“兩分離”的時候,一般人都唱C調,而趙燕俠要求吳昊頤唱升C調,即她的原調門。“一開始我很有壓力,這段特別難,沒有很深的功底接觸這段很困難。藝術其實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是一種悟性。”當吳昊頤終于將這段呈現到舞臺上時,一個“兒啊——”的叫頭就贏得了觀眾的滿堂彩。因為她的處理非常貼合劇情——拉長音后面有一個哭腔,嗓音從弱到強到帶有顫音,非常有感染力。
“其他派別的《白蛇傳》我都看過,感覺他們都比較俏。而趙派的《白蛇傳》一出場就是反板。我們這行挺怕反板的,觀眾很容易掉冷水盆里。我怕我拿不住,但趙老師就拿得住,她一出場非常大氣。我曾問趙老師:別人的白蛇都很花俏,身段什么的細節很多,咱們趙派這個白蛇怎么什么都沒有啊?趙老師說:你出來不應該被板式束縛住。白蛇不是妖,她是大仙,她的分量在里面。你體現的那種情感是你羨慕人間的愛,但并不拘泥于男女之間的那種小情感、小女人情結。”
趙燕俠演的《花田錯》,臺上沒有一句對詞,就她一人在那里納鞋底,忙忙叨叨地,把鞋底帶著針放在椅子上,又忘了,一屁股坐下被針扎了……一系列動作都是無實物表演,舞臺上沒有任何東西,但底下觀眾無一不被她牽著心,可見趙派藝術的逼真。“這個派別的主體就是本人的內心感受,在趙老師看來表演沒有框架。所以我不建議低年級的學生學趙派,最好是打一個底子之后再來學趙派。趙派就相當于研究生、博士生的課程,它本身沒有特別一板一眼的東西,全部都化在其中了。”
跟隨趙燕俠學過《白蛇傳》《瀟湘夜雨》后,吳昊頤正在學習趙派的經典劇目《碧波仙子》。說到師生情,吳昊頤非常珍惜跟趙燕俠老師的這種緣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百善孝為先,不光孝敬父母,還要孝敬所有有恩于你的師長。老師并不需要什么,眼睛里也沒有錢的概念,他們這一輩子就是為戲而活。我能回饋他們的也就是對藝術的掌握,能讓她看到對自己藝術的傳承也是一種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