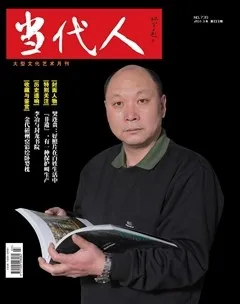一個“假洋鬼子”的命運沉浮
“假洋鬼子”的形象最早出現在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那是個穿洋服、說洋話、裝洋相的中國血統的中國人;《白妮》中的“假洋鬼子”白妮則與他完全不同,她是個穿土布衣、說中國土話、地道的中國打扮、但卻是洋人血統、洋人長相的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她的命運沉浮與中國與西方關系的變化有著密切關系。她的身份本身就是中西關系的象征。
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史,是以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轟開中國的大門開始的。一個帶有白人即西方人血統和長相的陳耀庭(矢群)及其孫女白妮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的人生命運的起伏跌宕就完全超出其個人命運的范疇,折射出一百多年來中西關系起伏曲折的發展變化史。
小說主人公矢秀白(白妮)的白人血統始自她的爺爺矢群。當時,在西方列強加緊瓜分中國的背景下,不僅天津北京被洋鬼子攻陷,保定也未能幸免,連時任護理直隸總督的廷雍及城守尉奎恒、淮軍統領王占魁都被洋鬼子以支持“牶匪”而處死。在西方列強的鐵蹄剛剛蹂躪過的保定大地,一個膚色和長相酷似洋鬼子的矢群突然出現在堤外村,他被周圍人懷疑、鄙視是很自然的。對他的態度,其實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洋鬼子即對西方侵略者的態度。當時的人們還不可能將“洋人”與“洋鬼子”區別開來。
為了擺脫受人鄙視的處境,洗去受人唾罵的白人血統,矢家幾代人進行了不懈的“清淤工程”。雖然似乎有些成效,但生物的隔代遺傳規律使他們的努力功虧一簣。在第三代人秀白身上,她的膚色和長相又恢復了洋人的模樣。這對矢家人來說簡直是滅頂之災:秀紅突然暴病而死,絕望的寧氏自殺身亡,矢群也在不久告別人世。洋人的血統成了矢家無法擺脫的原罪,無法解脫的精神負擔。
秀白雖然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列強已經被趕出了中國。但在冷戰的背景下,中西關系并沒有好轉的跡象。在秀白出生的1954年,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剛剛結束。因為她的白人血統與長相,奶奶不讓她到外村上學,她憤怒地燒毀自己心愛的課本與書包,輟學務農;還是因為她的白人血統,她不僅喪失了在縣農展館轉正的機會,還給家庭招來了“國際特務”的嫌疑,被“立案調查”。這白人血統與長相,就像她頭上的緊箍咒,使她動輒得咎:她一次又一次地遭人陷害無處申辯,甚至不得不替人頂罪,受盡人們的欺負與凌辱。
然874e8738550d13ceee09afe5cd8df2b4而,歷史的辯證法是“物極必反”,改革開放后,國人對西方的態度日趨理性。
大氣候的變化自然要影響到堤外村的小氣候。白妮很快就由被人鄙視的“另類”變成了受人羨慕和追捧的香餑餑。因為矢秀白的白人血統,做買賣經商對她來說好像出于天性的內行。她由擺地攤起家,幾年時間就辦起自己的企業,成了遠近聞名的企業家。
從一定意義上說,矢秀白及其先輩的命運史,就是一部形象的近現代中西方關系史。
既然《白妮》的主旨是要想表現中西關系史 ,它就應該將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天津、上海這些與中西關系有密切聯系的大都市,而不應該放在與西方幾乎沒有任何直接聯系的偏僻的堤外村;其次,從作品的內容上看,作品幾乎沒有任何涉及到中西關系的具體情節和細節描寫,這是為什么?
我認為,這是作者在小說創作上的一種“留空白”的創新嘗試。
傳統的小說理論認為環境、人物和情節是構成小說的三要素。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
《白妮》作為一部反映中西關系演變的長篇小說,卻對中西關系史上一些關鍵時刻的歷史背景都采用了“留空白”的寫法。如作品開頭對寧氏母子第一次出現在堤外村時的歷史背景,在一般長篇小說中都是要大書特書的,而《白妮》只用了一句“公元1904年的秋天”輕輕帶過。對當時歷史背景只字未提,這就是典型“留空白”的寫法。因為每一個稍有歷史常識的中國人都知道,1904年是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不久,北京、天津和保定剛經過西方列強一次血腥的洗劫。兩歲的矢群的白人長相就告訴人們,他出生于西方列強侵占北京天津之后。黃種人的母親和白皮膚兒子就說明了他們與西方燒殺奸淫的侵略者的某種聯系。這種省略的寫法不僅節省了大量的筆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調動讀者的積極性,對故事背景和情節加以補充和充實。也只有進行了這種補充和充實,讀者才能明白為什么一個“白臉、高鼻子、黃眼睛、黃頭發”的孩子在堤外村被視為“另類”,受到人們鄙視和凌辱。
這種“留空白”的寫法還表現在對故事情節的關鍵處的處理上。白妮的身世,即她的白人血統的起源不僅是吸引讀者閱讀的一個興奮點,也是準確把握作品主旨的關鍵所在,然而作品在這一關鍵之處卻給讀者留下了一個空白。作品在最后一節雖然向讀者交代了秀白是天津附近一個大戶陳家的后代,她的爺爺矢群即陳家的二爺陳耀庭。至于陳耀庭何以一出生就呈現出洋人的膚色和長相,作品只用了“難道那次回娘家……”半句話一帶而過,給讀者留下一個極大的空白。
(責編:孫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