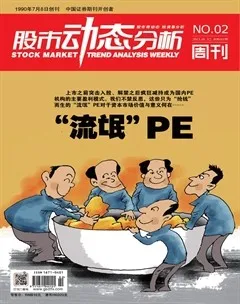新基金法有感:一個老基金從業人員的思考
新基金法出臺,相關政策好到不可思議,我們該怎么辦?本來我們只希望在基金法出臺之后,能夠實現私募基金的法律主體地位,可以堂堂正正的做私募。沒想到,監管部門一紙文件攪亂行業一池春水,私募公司居然也可以申請做公募業務了。由于星石公司基本符合條件,頓時有很多人來問,你們想不想申請做公募?我們都是從公募出來的,當然也想再回去,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在私募行業這五、六年來,我們經歷了極其復雜的心路歷程。第一個階段是失落。我們都是公募基金職業經理人出身,到了私募行業才知道,在國內,私營小公司的平臺是多么低下,原來在公募的金融牌照是多么有用。第二個階段是融入。我們既然已經辭職出來,沒有退路,只能適應。我們發現,由于我們既沒有法律主體地位,又是個私營公司,因此在這個行業里生存,除了把業績做好,別無他路。五、六年來,我們股東從來沒有分過紅,每年把所有的盈利都重新投回公司,全力打造一只國內獨有的“追求絕對回報”投資團隊。在業內也漸漸的有了聲譽。第三個階段是反思。感謝國內財富管理領域的大爆發,私募行業的春天提早來臨,如果說2010年國內私人銀行大舉介入私募行業,把私募行業帶入了公眾的視野,2012年底新基金法的誕生,又為私募行業壯大發展帶來根本性推動。但是,作為經歷過公募和私募的老基金從業人員,我們需要思考,我們的能力有多大?
我們曾經受到了很多誘惑:有做H股的誘惑,有做PE投資的誘惑,有做定增產品的誘惑,有做債券產品的誘惑等等。每一次都看似前景美好、收益頗豐,我們每一次都反復問自己,我們的能力有多大?
看到一個領域的收益機會不難,甚至做出個產品設計也很容易,但把產品業績真正做好很難。2007年,我們看到了機會,立志要做一個“追求絕對回報”的產品,2008年才初步探索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框架;2009年補充設立了“量化目標”;2010年“風險收益配比模型”的雛形才剛剛形成,開始大批的增加投資人員,根據前期探索的結果著手完善投資體系;2011年和2012年兩年間,我們整個團隊都在反復的調整和模擬實驗,不斷優化,終于在結合股市中周期的投資時鐘輪動方面取得突破。直到現在,我們才能信心十足的說,我們有能力做出中國的“追求絕對回報”。從我們的實踐看,證明一個產品真正成功,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那么證明一個公司呢?作為私募公司,我們沒有雄厚的股東支持,也沒有優質的集團資源共享,我們是否有能力進入競爭激烈公募領域,只能取決于我們公司的整體綜合實力。我們如何做出有區隔的市場定位,如何利用既有的投資優勢提供系列的產品線,如何在新形勢下不斷優化自己的股權激勵方案,如何……
也許,證明一個公司,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作者系星石投資總裁、首席策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