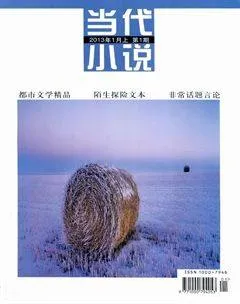錢的顏色
一
原定計(jì)劃星期天下午去給袁順強(qiáng)置一件毛衣,瓦尚春也想置一件毛衣,瓦尚春有好幾年沒(méi)有置毛衣了。翠銀說(shuō),是啊,你也應(yīng)該置一件毛衣穿穿了,那么辛苦,連穿的都顧不上。瓦尚春說(shuō),等等吧。
翠銀生病了,瓦尚春想早點(diǎn)把翠銀的病治好,所以瓦尚春顧不上自己的吃穿。瓦尚春把翠銀帶到洪水市軍醫(yī)院檢查過(guò)了,可檢杳出來(lái)的結(jié)果總是很模糊。其實(shí)也不是檢查下來(lái)模不模糊的事情,而是翠銀剛進(jìn)洪水市市區(qū)就感覺身體好多了。瓦尚春想,可能與他許愿有關(guān),在未送翠銀去洪水市軍醫(yī)院檢查之前,瓦尚春就許愿了,瓦尚春說(shuō),如果檢查下來(lái)翠銀什么病也沒(méi)有,那他就到廟里燒高香。
瓦尚春轉(zhuǎn)念一想,他們從洪水市軍醫(yī)院回來(lái)已有一個(gè)星期了,他并沒(méi)有去廟里燒高香,如果翠銀的病就那么一聲不響地好了,那可不是一兩件毛衣可以等同的事情。所以瓦尚春改計(jì)劃了,他沖翠銀說(shuō),干脆你與袁順強(qiáng)去置毛衣,我去把愿了了吧。翠銀說(shuō),什么愿?瓦尚春說(shuō),廟里燒高香啊。翠銀想了想,到廟里燒高香是為她,她不能讓瓦尚春一個(gè)人去。于是翠銀說(shuō),那我們也去廟里燒高香,改天再去給袁順強(qiáng)置毛衣。瓦尚春說(shuō),也行。
袁順強(qiáng)是翠銀的親侄兒,也是瓦尚春的內(nèi)侄兒,袁順強(qiáng)在泉水縣城小學(xué)上學(xué),寄宿在瓦尚春家。因?yàn)橥呱写盒【俗右呀?jīng)把錢打到他的賬號(hào)上了,聽翠銀這樣說(shuō),袁順強(qiáng)噘著嘴,拉長(zhǎng)了臉,雖然沒(méi)有說(shuō)什么,可感覺那張臉像擰得出水似的不悅。翠銀看見袁順強(qiáng)拉長(zhǎng)的臉,說(shuō),哎呀,順強(qiáng),姑姑又不是不給你置毛衣,可是你姑父要與我去了愿,你要聽話,知道不?袁順強(qiáng)紅著臉點(diǎn)點(diǎn)頭,并很不情愿地從鼻孔里發(fā)出“嗯嗯嗯”的聲音!于是瓦尚春就領(lǐng)著翠銀與袁順強(qiáng)去廟里燒高香去了。
這座廟子雖然修造得那么完備,可是里面沒(méi)有一個(gè)和尚,說(shuō)起來(lái),沒(méi)有和尚的廟子,已經(jīng)不算廟子了,如果要算,也只能算一個(gè)無(wú)人看管的山王廟。但是這里看管的人可不少。瓦尚春不懂這些看管的人算什么,可有人告訴他,凡沒(méi)有剃發(fā)受戒看管廟子的人,只能算居士。于是瓦尚春知道廟子是可以由居士來(lái)管理的。至于泉水縣的這座惟一的廟子算什么教派,瓦尚春就更不明白了。有的說(shuō)是全真教,有的又說(shuō)是道教,如果要說(shuō)起來(lái),這廟子里的菩薩是以如來(lái)佛為代表的,那應(yīng)該算佛教了吧?瓦尚春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思考良久,如果是佛教,那廟子里應(yīng)該全是男居士,可里面全是女居士。這是廟子還是尼姑庵?瓦尚春無(wú)法判斷。你說(shuō)是廟子,里面全是女居士,你說(shuō)是尼姑庵,那建筑又完全是廟宇的宏大建筑。由于瓦尚春無(wú)法想明白,他只好放棄了。只是瓦尚春覺得上這座廟子燒香化紙很靈驗(yàn),至于靈驗(yàn)到什么程度,瓦尚春尚未考證,所以瓦尚春常常到這座廟里來(lái)燒香化紙。
去燒香要路過(guò)瓦尚春堂弟瓦勝利那兒,瓦勝利媳婦生孩子了,瓦尚春與翠銀一直商議著去看看,可始終沒(méi)抽得出時(shí)間。對(duì)此,翠銀提議,順便去瓦勝利家看看。瓦尚春說(shuō),噢,這還比較恰當(dāng),順便就去了。翠銀說(shuō),是啊。可是不可能空著手去,得給剛剛降生的孩子買點(diǎn)什么?通過(guò)協(xié)商,買一套寶寶衣。瓦尚春說(shuō),寶寶衣不錯(cuò),就這樣確定下來(lái)。
瓦尚春與翠銀還有袁順強(qiáng)一同走出美景家園,往門口一站,可不知走哪條路,這兒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直接去廟里的路,當(dāng)然要通過(guò)一條小街道,路過(guò)瓦勝利家;一條呢,是到大街去的路,再折轉(zhuǎn)到廟里去,也要路過(guò)瓦勝利家。瓦尚春?jiǎn)枺吣睦铮客呱写涸趩?wèn)這話時(shí),心里已經(jīng)做過(guò)思考,如果走大街,可以到超市去買寶寶衣,超市賣的寶寶衣,無(wú)論樣式,還是色彩都要新鮮一些,而那些小店里賣的寶寶衣,無(wú)論樣式或者色彩都要陳舊一些。翠銀也是抓住瓦尚春的想法,但是小街道上購(gòu)的東西相當(dāng)便宜。翠銀覺得送人禮物不過(guò)是個(gè)禮節(jié)而已,況且僅僅是堂弟,又不是自己的親弟弟。于是翠銀回答說(shuō),走小街,你那么忙難道還要到大街上去逛嗎?瓦尚春想走大街,但是瓦尚春知道自己的家底,一方面正在為遠(yuǎn)方上大學(xué)的兒子的花銷發(fā)愁,另一方面為翠銀的治療費(fèi)發(fā)愁。所以瓦尚春不得不強(qiáng)迫自己依了翠銀,說(shuō),就走小街吧。翠銀向瓦尚春斜視了一眼,表現(xiàn)出很不高興的樣子。瓦尚春說(shuō),你不要不高興嘛,我不依了你嗎?袁順強(qiáng)看見翠銀針對(duì)瓦尚春的眼神,袁順強(qiáng)暗中高興,心想,你不給我置毛衣試試?瓦尚春與翠銀一邊走,一邊辯論起來(lái)。翠銀說(shuō),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你不外就是想到超市里買寶寶衣。瓦尚春說(shuō),才不是呢,我是說(shuō),走大街上去,賣寶寶衣的小店多,便于選擇。翠銀說(shuō),屁話,你還沒(méi)有翹尾巴,我就知道你要屙屎。瓦尚春開了句玩笑說(shuō),哎呀,不要說(shuō)了,我不正跟黨走嘛。翠銀說(shuō),我不是不想給瓦勝利小孩買件好點(diǎn)的寶寶衣,可是你想想啊,我們一家大小,就憑著你那點(diǎn)收入,多艱難啊,能節(jié)省的盡量節(jié)省吧。瓦尚春生氣了,說(shuō),哎呀,已經(jīng)依了你了,你還要強(qiáng)調(diào)個(gè)啥呢!翠銀覺得自己也有點(diǎn)過(guò)分,只好什么也不說(shuō)了。
二
來(lái)到S小街,瓦尚春一路走著,都沒(méi)有看見賣寶寶衣的地方,但他又不好埋怨,他擔(dān)心他的埋怨會(huì)讓翠銀不高興,原本一件很好的事,讓瓦尚春搞砸了,多不好啊。可是正在瓦尚春心里犯嘀咕的時(shí)候。翠銀把瓦尚春帶到一家賣寶寶衣的小店去了。這顯然不是很正規(guī)的那種小店,里面的貨亂堆亂放,給人的感覺還不如地?cái)偵系呢浳镆?guī)范、整潔。瞅去,像很久沒(méi)有開張一樣。那店主是一個(gè)矮矮的女人,那張臉黑黑的,像沒(méi)有完全從猿猴進(jìn)化過(guò)來(lái)一樣,前額凸出,眼睛深陷,下巴尖而向上翹,兩手只有手心還能夠透出一點(diǎn)顏色,那指甲完全是猿猴的指甲,很長(zhǎng),里面塞滿了黑黑的污垢,估計(jì)打娘胎里生下來(lái)她就沒(méi)有剪過(guò)指甲。瓦尚春瞅了大半天,也沒(méi)瞅到一件像樣的寶寶衣。那女人與翠銀還聊得歡呢,女人從漆黑的角落抓出一件寶寶衣,要翠銀去辨認(rèn),翠銀拿著那件寶寶衣愛不釋手。瓦尚春不太想與這樣的女人打交道,不是說(shuō)她人才差、不是說(shuō)她不惹人心愛,而是她太邋遢。翠銀拿著那件黑不溜秋的寶寶衣愛不釋手地與黑不溜秋的店主侃價(jià),瓦尚春便把錢包掏出來(lái),恨不得直接把錢包扔給黑不溜秋的店主飛也似的跑掉。可是瓦尚春看見翠銀的目光了,是一種暗示,也是一種命令,瓦尚春明白,是叫他不要慌,還沒(méi)談定價(jià)錢呢!
瓦尚春知道,他的錢包里不僅有三張拾元鈔,還有一張伍拾元鈔,這些錢,是瓦尚春頭一天去割豬肉屠戶找的。找錢給瓦尚春的屠戶,看上去非常面善,瓦尚春當(dāng)時(shí)還想過(guò),這么面善的人做屠戶,一定是家庭的確過(guò)不去了。瓦尚春對(duì)拾元的散碎銀子不在意,瓦尚春在意的是那張伍拾元鈔。因?yàn)槲槭霸淼氖俏閺埵霸停僬f(shuō),伍拾元一張的鈔票最容易造假。瓦尚春以前就得過(guò)伍拾元的假鈔。這張假鈔讓瓦尚春整整兩個(gè)多月沒(méi)有睡好覺。瓦尚春為了吸取教訓(xùn),把那張伍拾元的假鈔壓在枕頭底下放了好幾年,可能是枕頭太硬的原因,那張假鈔自覺不自覺地破損了。瓦尚春并不在乎那張假鈔,瓦尚春在乎的是這樣的人世有多恐怖啊。所以瓦尚春把屠戶找給他的伍拾元的鈔票反復(fù)地審視,首先,他要檢驗(yàn),無(wú)論大寫還是小寫,是不是都寫的伍拾,因?yàn)閮H僅從顏色上無(wú)法辨認(rèn),它與拾元人民幣沒(méi)什么區(qū)別,然后從各個(gè)角度審視出這張伍拾元的鈔票都是真的為止。屠戶向瓦尚春笑笑,說(shuō),是真的吧。瓦尚春也很爽快地說(shuō),沒(méi)問(wèn)題。這樣瓦尚春才拎著裝有豬肉的塑料袋子晃晃悠悠地走了
最關(guān)鍵的是,還有好幾張銀行卡,雖然這種銀行卡,那個(gè)邋遢的店主取不出來(lái),可是如果拿給她,瓦尚春也沒(méi)錢了。所以瓦尚春不能做那種傻事。瓦尚春聽見邋遢店主要貳拾伍元,翠銀還她拾伍元。僵持了一會(huì)兒,邋遢店主作了讓步,說(shuō),我也不要你的貳拾伍,你也不要說(shuō)拾伍元,拾伍元,本錢都不夠,不說(shuō)賺錢,起碼本錢要給嘛。翠銀說(shuō),那你說(shuō)多少?邋遢店主說(shuō),貳拾,怎么樣?翠銀說(shuō),拾捌,多了一分,我也不會(huì)要。邋遢店主愣怔了一會(huì)兒,說(shuō),好好好,拾捌就拾捌,賠本我都——
瓦尚春早已從錢包里掏出了兩張錢,邋遢店主話音未落,瓦尚春看也不看邋遢店主的臉,就把錢扔給她了。邋遢店主找了兩元散碎銀子遞出來(lái),瓦尚春接也不接就站到店戶門外去了。是翠銀接下兩元錢。然后翠銀還與邋遢店主笑著說(shuō)了兩句什么,瓦尚春沒(méi)有聽見。翠銀從寶寶衣店出來(lái),也沒(méi)有埋怨瓦尚春就走了。
三
原來(lái)瓦尚春計(jì)劃先去瓦勝利家,然后才去廟里。這一下,瓦尚春又改變主意,瓦尚春改變主意的原因是,如果先去瓦勝利家,然后才去廟里,菩薩可能有意見,菩薩的意見在哪里呢?可能菩薩會(huì)認(rèn)為,你不過(guò)走瓦勝利家順便到廟里看看。所以瓦尚春改變主意,先去廟里,然后到瓦勝利家。翠銀沒(méi)有明確的反對(duì),可是翠銀的眼睛都瞪出水了。瓦尚春不顧翠銀的感受,瓦尚春急匆匆地向廟子走去,他相信翠銀與袁順強(qiáng)也會(huì)向廟子走去。因?yàn)橥呱写弘m然有點(diǎn)迷信,可是其出發(fā)點(diǎn)還是為翠銀好。翠銀果然不負(fù)瓦尚春所望,拎著一只裝有寶寶衣的袋子與袁順強(qiáng)按照瓦尚春的旨意向廟子走去。
才僅僅有一個(gè)月沒(méi)有去廟里,廟里就發(fā)生了很多變化,當(dāng)然廟宇還是那座廟宇,只是人員上發(fā)生了變化,最近廟里總是頻頻換人,換來(lái)的人都有些與佛或者說(shuō)與信仰無(wú)關(guān)了。這次是幾個(gè)破衣爛衫的老頭在銷售香紙,以前是幾個(gè)女居士,難道變成男居士了,或者這些女居士有任務(wù),要這些男居士給她們把守兩天?瓦尚春想,無(wú)論男女,他只要把責(zé)任盡到就行了。他原本想購(gòu)一對(duì)紅燭,一對(duì)很美觀的紅燭,他原來(lái)購(gòu)過(guò)這種紅燭,十塊錢一對(duì)。但是他的這種想法,被旁邊五塊一對(duì)的紅燭給淹沒(méi)了。不是瓦尚春自己淹沒(méi)的,而是翠銀給淹沒(méi)的。翠銀用手肘子從旁給瓦尚春拐了一下,說(shuō),拿五塊的就夠了。在其他方面,翠銀聽瓦尚春的,但是凡沾上經(jīng)濟(jì)方面的事,瓦尚春就要悠著點(diǎn),因?yàn)榇溷y其他方面可以讓步,凡沾上經(jīng)濟(jì)方面,她是寸步不讓。而且可能因?yàn)橥呱写涸谶@方面犯下錯(cuò)誤后,翠銀會(huì)幾個(gè)月不拿好臉色給他瞧。所以瓦尚春在經(jīng)濟(jì)方面只能聽之任之。瓦尚春明白,瓦尚春揀了伍元一對(duì)的紅燭,另外還揀了一把普通的香紙。
瓦尚春在從錢包里掏錢的時(shí)候,瓦尚春打錢包掃描了一遍,除了要掏出來(lái)遞給那個(gè)破衣爛衫的老頭外,里面還應(yīng)該有一張錢,那一張錢,應(yīng)該是伍拾的那張,瓦尚春瞧到一個(gè)大大的“0”,所以他斷定那是一張伍拾元的人民幣。瓦尚春不是瞧不起那些破衣爛衫的老頭,瓦尚春是在這些破衣爛衫的老頭面前吃過(guò)不少虧。
首先是瓦尚春進(jìn)省城的時(shí)候,一個(gè)破衣爛衫的老頭向他乞討,他的確身上沒(méi)有零錢,他不可能拿一張佰元鈔給那破爛老頭,結(jié)果沒(méi)過(guò)幾分鐘,他就被一伙劫匪給打劫了。這次瓦尚春損失可不少啊,是當(dāng)時(shí)兩年的工資呢!第二次,也是一個(gè)破衣爛衫的老頭鉆進(jìn)瓦尚春的宿舍去乞討,瓦尚春吃一塹長(zhǎng)一智,他給這個(gè)老頭伍塊錢,這個(gè)老頭走了,雖然老頭沒(méi)有表現(xiàn)出高興,可是瓦尚春得到了解脫。但是,還是沒(méi)有免去一難,老頭走后不久,瓦尚春的宿舍發(fā)生了火災(zāi)。對(duì)此,瓦尚春只要見到那樣的老頭他就心虛,他不知道將會(huì)出現(xiàn)什么不幸。不過(guò)在廟里遇上破衣爛衫的老頭,瓦尚春相信,不會(huì)出現(xiàn)什么不幸,因?yàn)樗麩讼悖嘈牌兴_會(huì)保佑他及他的家人。
四
燒過(guò)香后,瓦尚春與翠銀,還有袁順強(qiáng)一同到瓦勝利家去。瓦勝利租房雖然不是很窄小,可是由于為了照顧產(chǎn)婦,便封得比較嚴(yán)。于是瓦勝利家屋子里比較熱,所以瓦尚春到了瓦勝利家,就把衣服脫掉放在瓦勝利家沙發(fā)上。瓦勝利給瓦尚春與翠銀各沏了一杯茶,沒(méi)有給袁順強(qiáng)沏,袁順強(qiáng)是小孩,小孩子家,盡量不喝茶,瓦尚春與翠銀都沖袁順強(qiáng)說(shuō),要喝水自己倒去。瓦勝利忘記給袁順強(qiáng)沏茶,聽瓦尚春與翠銀這樣說(shuō),覺得有點(diǎn)尷尬,便要去給袁順強(qiáng)沏茶。瓦尚春說(shuō),沒(méi)必要。袁順強(qiáng)也說(shuō),他不喝茶。于是瓦勝利就沒(méi)有給袁順強(qiáng)沏茶了。翠銀把帶去的寶寶衣送給瓦勝利媳婦說(shuō),沒(méi)買什么,買個(gè)衣服兒給孩子穿。然后由提到小孩的事點(diǎn)燃了話題。首先瓦勝利媳婦闡述了生這個(gè)孩子的前前后后,然后說(shuō)到孩子目前的情況,還特別指出最近他們隔壁搞裝修,那鑿墻壁的聲音時(shí)斷時(shí)續(xù),把孩子嚇著了,整個(gè)晚上都睡不好覺。
瓦勝利附帶提到裝修的聲音,他說(shuō),簡(jiǎn)直是對(duì)大自然的破壞。瓦尚春知道,瓦勝利是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的人。現(xiàn)在火炭落到腳背上知道痛了。瓦尚春覺得,瓦勝利能夠知道這一點(diǎn),也是他的進(jìn)步,所以瓦尚春迎合說(shuō),是啊,現(xiàn)在,特別是購(gòu)買新房子,搞裝修,特別不要提前裝修,要讓別人裝修完了,才裝修,這樣少干擾。瓦勝利說(shuō),那也是,如果早知道隔壁要搞裝修,說(shuō)什么他也是不會(huì)租這套房子。瓦尚春說(shuō),這里大大小小是城市,作為城市,你要想在這里過(guò)上安靜日子,那是很難的。只是做好各種預(yù)防來(lái)適應(yīng)城市。瓦勝利說(shuō),是啊。瓦尚春與瓦勝利聊的時(shí)候,翠銀也與瓦勝利媳婦聊了起來(lái),有時(shí)還拿袁順強(qiáng)作為話題聊了起來(lái)。袁順強(qiáng)沒(méi)有覺得不好意思,瓦勝利媳婦問(wèn)他一句,他就回答一句,需要翠銀補(bǔ)充的,翠銀就補(bǔ)充。聊了一會(huì)兒,瓦尚春提出回家,翠銀也響應(yīng),說(shuō)可以,回家。瓦勝利說(shuō),怎么回家呢?就在這兒吃飯吧。翠銀說(shuō),回去吃,家里還有許多冷飯呢。瓦勝利媳婦也說(shuō),就在這兒吃了去嘛。翠銀說(shuō),不了。瓦尚春把沙發(fā)上的外衣拿起來(lái),穿上,與袁順強(qiáng)、翠銀一起走了。
五
走到菜市場(chǎng)門口的時(shí)候,翠銀叫瓦尚春拿錢給她買點(diǎn)菜回去。瓦尚春想也不想,就從兜里掏錢包,當(dāng)瓦尚春又從錢包里掏出一張鈔票的時(shí)候,瓦尚春震驚了,怎么那張伍拾元突然變成拾元了呢?難道他買香燭的時(shí)候,拿給那個(gè)破衣爛衫的老頭了?翠銀說(shuō),不可能,我明明看見拿的是拾元呢!翠銀說(shuō),是不是買寶寶衣的時(shí)候,你把伍拾元錯(cuò)當(dāng)拾元了?瓦尚春說(shuō),不會(huì)吧,我還仔細(xì)打量了,是兩張拾元的呢。
翠銀一邊拿著瓦尚春給的拾元錢向菜市場(chǎng)走去,一邊嘰里咕嚕地念叨著什么。瓦尚春與袁順強(qiáng)站在菜市場(chǎng)門口,瓦尚春沒(méi)有與袁順強(qiáng)討論錢的事,但并不意味瓦尚春不去想錢的事,那可是伍拾元錢呢!瓦尚春想得最多的是被廟里的破爛老頭使障眼法,他就知道廟里的破爛老頭不是什么好東西,像這樣的破爛老頭在廟子里,不僅不會(huì)把廟子建設(shè)好、保護(hù)好,而且還會(huì)把廟子整得一塌糊涂。瓦尚春在心里暗罵,臭老頭,爛老頭。
翠銀把菜買來(lái)后,沒(méi)有少與瓦尚春討論那伍拾元錢的事!在翠銀的心中,是瓦尚春不小心把伍拾元錢當(dāng)拾元給了那個(gè)賣寶寶衣的又矮又黑的女人了。在瓦尚春的心中,是被那個(gè)破爛老頭使障眼法了。袁順強(qiáng)一句話不說(shuō),瓦尚春理解,因?yàn)樵谶@種情況下,袁順強(qiáng)還小,他不懂得人情世故。瓦尚春與翠銀為那張伍拾元人民幣從菜市門口一直討論到家里。然后保持沉默。但并不等于瓦尚春與翠銀不去想那樁事了。瓦尚春想得可寬了,可是瓦尚春一直堅(jiān)持他的想法,絕對(duì)不會(huì)錯(cuò)拿給那個(gè)賣寶寶衣的又矮又丑的女人。瓦尚春想,也有可能是在瓦勝利家脫衣服的時(shí)候,被弄丟在瓦勝利家了,但是瓦尚春總共不過(guò)四張錢啊,清理起來(lái),給賣寶寶衣的又矮又黑的女人花去了兩張,買香燭花去一張,剩下的就是拿給翠銀買菜的呀!瓦尚春還有一種想法,不知道合不合理,平時(shí)袁順強(qiáng)吃過(guò)晚飯都不做作業(yè),昨天晚上,袁順強(qiáng)在屋子里做作業(yè),瓦尚春本身就覺得蹊蹺,這下子把這伍拾元錢搞拋了,瓦尚春更覺得蹊蹺,是不是袁順強(qiáng)趁瓦尚春與翠銀在火爐房屋子里烤火的時(shí)候,袁順強(qiáng)做了手腳,把他積余的拾元錢塞在瓦尚春的錢包里,把那伍拾元鈔換走了。
最后兩種想法瓦尚春不能給翠銀說(shuō),在瓦勝利家搞丟的吧,如果讓翠銀知道了,她肯定要問(wèn)瓦勝利的,如果真在瓦勝利家,瓦勝利是會(huì)還瓦尚春的,一方面瓦勝利是成年人,另一方面,瓦勝利自己也在找錢,他不會(huì)在乎你那伍拾塊錢。如果不在瓦勝利家,瓦勝利可會(huì)有想法了,因?yàn)檫@樣會(huì)讓瓦勝利丟下一個(gè)壞名聲。所以瓦尚春最好不要把這種想法說(shuō)出來(lái)。第二種想法更不能給翠銀說(shuō),袁順強(qiáng)是翠銀的親侄兒,他們是有共同血系的,如果說(shuō)袁順強(qiáng)做這種不軌的行為,那不等于說(shuō)翠銀也有這種不軌的行為嗎?雖然這種想法富有一種強(qiáng)盜邏輯,可是翠銀如果知道瓦尚春這種想法,那翠銀說(shuō)什么也會(huì)這樣想的,誰(shuí)能杜絕翠銀不會(huì)這樣想呢?
六
這天晚上,瓦尚春為這伍拾元錢徹夜未眠,相信翠銀也會(huì)為這伍拾元錢徹夜未眠,因?yàn)榕瞬槐饶腥耍藢?duì)金錢看得很重。叫瓦尚春考慮到最后,他想到,拾元鈔與伍拾元鈔為什么不好判斷呢?關(guān)鍵是新版本的伍拾元鈔與拾元鈔,顏色容易混淆。于是他動(dòng)惻隱之心,給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銀行寫一封信,建議把拾元鈔與伍拾元鈔的顏色進(jìn)行調(diào)整,最好是用老版本的伍拾元鈔,或者佰元鈔是紅色的,那么伍拾元鈔的就換成金黃色的,像秋收的谷穗一樣金黃,能區(qū)別拾元的顏色,又具有象征意義。
半夜里,瓦尚春打開電腦,翠銀仿佛從夢(mèng)中醒來(lái)似的,追問(wèn)瓦尚春,你怎么了?半夜三更的,難道還要打幾盤游戲嗎?瓦尚春說(shuō),我想給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銀行寫一封信。翠銀說(shuō),寫什么信,你不會(huì)為那伍拾元錢搞瘋癲了吧?瓦尚春說(shuō),誰(shuí)瘋癲了,我是要寫一封信告訴他們,今后造錢的時(shí)候,盡量把伍拾元與拾元的顏色區(qū)分vbxOjzDMBjNT2eoIMl82rndt+vaMsXfv+9Wt8/Qp7MM=一下,不然容易混淆。翠銀說(shuō),你真是瘋了,你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銀行在哪里嗎?鬼扯!瓦尚春是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銀行在哪里,但是瓦尚春可以把他的想法弄在那些名望很高的網(wǎng)站論壇上,讓所有人知道,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總會(huì)被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行知道——翠銀說(shuō),可能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銀行都會(huì)為你那伍拾元錢申冤啰,你曉得不?純屬胡扯,睡覺哦。
瓦尚春是一個(gè)非常固執(zhí)的人,他確定的事一定會(huì)照辦。所以他是不會(huì)聽翠銀的,他堅(jiān)持把他對(duì)伍拾元鈔換顏色的想法寫成《給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總行的一封公開信》發(fā)布在網(wǎng)站論壇。他希望得到大家的關(guān)注。當(dāng)瓦尚春第二天打開論壇的時(shí)候,他看見點(diǎn)擊率不少,他感到后悔的是,他應(yīng)該用真實(shí)名字,這樣,他也會(huì)跟著他這封信而出名。可惜呀。但是,只要能夠把他的想法告訴給大家,特別是銀行部門的人,他就心滿意足了。
七
無(wú)論是掉包計(jì)也好,還是障眼法也好,總之,瓦尚春那伍拾塊錢是沒(méi)了。都過(guò)了很久,瓦尚春打S街路過(guò),他突然感覺背后被什么東西捅了一下,瓦尚春掉頭瞅,那人正舉著手準(zhǔn)備捅第二下,瓦尚春說(shuō),你要干什么?那人一邊招手,一邊沖瓦尚春說(shuō),大哥,隨我來(lái)。瓦尚春莫名其妙,瓦尚春再仔細(xì)瞅,原來(lái)那人竟然是那天賣寶寶衣給翠銀的女店主。瓦尚春一直對(duì)她不感興趣,瓦尚春瞄了一眼后,什么也沒(méi)說(shuō)就走了。可是瓦尚春剛起步,感覺背后又被什么東西拽住了,瓦尚春很難施展腳步。瓦尚春再次掉過(guò)頭仔細(xì)瞅時(shí),是那店主死死地用雙手拽住他往店里走。瓦尚春說(shuō),你要干什么?那店主說(shuō),是好事,絕對(duì)不騙你。瓦尚春想,你那么小一個(gè)女人,說(shuō)什么你也強(qiáng)不過(guò)他,所以瓦尚春好奇,到底是什么樣的好事?瓦尚春跟著女店主向里屋走去,可是當(dāng)?shù)曛靼阉麕У脚P室的時(shí)候,瓦尚春心虛了,瓦尚春并不是怕女店主,瓦尚春是怕女店主后面藏有黑社會(huì)。瓦尚春準(zhǔn)備跑,正在瓦尚春準(zhǔn)備跑的時(shí)候,女店主把衣褲脫個(gè)精光,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
女店主又矮又黑,赤身裸體,除了她下身那處叢林般的地界外,其余的地方,幾乎都相當(dāng)于穿了一件油膩膩的衣服。她說(shuō),來(lái)吧,大哥。瓦尚春嚇得一跳,喝斥道,你要干什么?她說(shuō),你不是要上我嗎?瓦尚春說(shuō),我什么時(shí)候說(shuō)要上你了?她說(shuō),那天你們?cè)谖疫@兒買寶寶衣的時(shí)候,你不是給我小費(fèi)了嗎?快點(diǎn)上嘛,我還要守店呢!瓦尚春說(shuō),我什么時(shí)候給你小費(fèi)了?莫名其妙!她說(shuō),你還沒(méi)給呢!你不是給我兩張錢嗎?一張拾元的,一張伍拾元的,寶寶衣花去十八元,我找你兩元,還有叁拾元。這叁拾元難道不是小費(fèi)嗎?我記得清楚,我不會(huì)忘記的,終究我會(huì)讓你如愿以償。瓦尚春還是難以想起他什么時(shí)候給過(guò)她小費(fèi)?因?yàn)樵谕呱写旱拇竽X里,他的伍拾元人民幣弄丟并不是因?yàn)橘I寶寶衣,而是廟子里那個(gè)破衣爛衫的老頭子搞的障眼法,趁瓦尚春不小心,把伍拾元鈔偷換成拾元鈔,以此麻痹瓦尚春,哪里知道是自己當(dāng)小費(fèi)拿給那個(gè)又矮又黑的女店主了?瓦尚春看見又矮又黑的女店主,他哪里有心思上她。瓦尚春氣急敗壞地甩出一句話,上你個(gè)頭!于是掉頭便走了。
可是那個(gè)又矮又黑的女店主并不示弱,抓了一把零角票兒向瓦尚春走的方向一扔,嚷道,去你的吧,把你那臭錢拿走,老娘不稀罕!
瓦尚春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傻傻地瞅著地上的零角票兒,覺得這事兒不知從何說(shuō)起。
責(zé)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