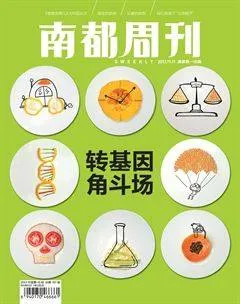用痛經的表情俯瞰人生

某天,我在大學Q群里看到了一句話: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站在廣場卻看不到城樓上的毛主席,而是打開錢包卻看不到毛主席。
這句話呼嘯而來時,我正陷于遮天蔽日的霧霾中。每天駕車在宛如仙境的長街穿梭,我在琢磨那些巨幅戶外廣告的品牌是否應該索賠,因為這種鬼天氣沒人能看清商標,而那些買豪車耍酷的人只怕也會涌起淡淡的惆悵—濃霧撲面,人人都像得了白內障,誰還能看清你的車是奧迪還是奧拓、捷豹還是獵豹?電視上看到哈爾濱的大霧,更是夸張,學校直接停課,估計劫匪都不用戴面罩就可以搶運鈔車了,反正一米開外只有黑影。
無錢果腹,這是人生最大的苦痛,想必所有經歷過饑餓年代的人都會同意這個觀點。但人活在世間,不當餓死鬼似乎不應成為最高目標。去年夏天我忽然發現天空驟然變得澄澈了許多,當時感慨地想,如果藍天白云和青山綠水能夠重來,我寧愿忍受經濟衰退的苦痛,寧愿收入少一大截,就當花錢買一個心曠神怡的生存環境。而今時今日,我才發現最大之痛是:收入沒增加,物價在上漲,存款在貶值,稅賦要增加,而中國大地的霧霾卻越來越嚴重了,亦即是說,錢包里的主席和城樓上的主席已經攜手遠去,而我們,都是策馬直撲延安卻撲了個空的胡宗南。
隨著時空的遷移和心境的變異,我們的痛點經常在轉移。有回我喝骨頭湯時憶起了往事:小時候,母親所在的學校養了幾頭大豬,過年時宰殺分給教師,幾十垛肥肉如女神般娉娉婷婷地臥在案板上,等待著婆家。每垛肥肉邊照例有骨頭和下水拱衛,去得早的老師定是選肥肉最多的,眉眼里的幸福簡直噴薄而出,去得晚的老師只好選骨頭和下水多的那份,扭頭就黑下了臉,如喪考妣地罵自家的跟屁小孩拖了后腿。那個年代,吃肉即富貴,吃骨頭是賤命,哪像現如今,排骨和豬下水比肉貴多了。
人終究是一種得隴望蜀、見異思遷的動物,總在惦記著得不到的物事,并且為此痛苦。某次我參加某系統的會議,他們想多推些本行業的典型,我說:出名毫無意義,當大眾遺忘你們的時候,才是你們工作最成功之處;你想起醫生必是有恙之時,你惦起消防員必已火光沖天,你念叨交警必是馬路水泄不通;老子曾曰:最好的政府是人們感覺不到的政府。
我初入新聞行當的時候,最痛苦的是不知如何才能出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成了新聞的主角,那時才覺悟出名是最悲催的一件事。時至今日,我依然認定,當新聞人成為新聞的主角,那一定是大禍臨頭了。
每個人的痛苦指數,與他自己對幸福的定義有關。孩童最痛苦的是玩具被搶走,青年最痛苦的是失戀,這些在中年人眼里都不算個事,因為無數玩具可以用錢買到,許多愛情也可以用錢買到,能用錢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及至中年,健康漸漸出了問題,花再多錢都不可能康復如初,待到茍延殘喘的暮年,死神更不是能用金錢行賄的。所以說,當鮮衣怒馬的人生忽然闖入一個不能返頭的死胡同,才是最甚之痛。
有導演在微博上說:飯局上聊天,居然席間十多個朋友全都辦好或正在辦移民手續,除了他自己。我們現世最常見的便是這種痛:有心無力。正如李蓮英碰上賽金花,彌留老人中了六合彩,捆在椅子的美食家眼睜睜看著滿漢全席魚貫而過,那都是近在咫尺卻不能觸摸的幸福呵。每次我接到大洋彼岸的舊人郵件,我那蒼老的心房都會被強拆一次,只能默默地訓誡自己:貧賤,不能移。
劉原
專欄作家,現居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