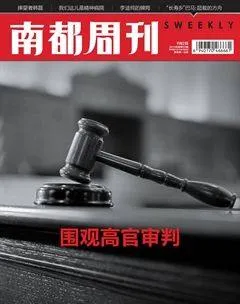詩人在左,瘋子在右
女,1964年生,“非非主義”代表詩人之一。畢業于軍醫大學,后轉業至地方精神病醫院做護士。代表作品有《種煙葉的女人》、《路上一盞燈》、《我們來寫詩》、《內心世界》、《夫妻生活》等。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國詩年選》、《中國新詩年鑒》、《中國最佳詩歌》 等詩歌選本。2013年4月,出版《我們這兒是精神病院》。現居成都。
精神病院里的愛
那一年春天,我從鄉下,光著腳,翻山越嶺,奔跑而來,穿過一大片油菜花地,我走進精神病院,看見一個女人,跳進落滿櫻花的河里,再也沒有起來,我因為不知所措,而寫過一首詩。當然了,我只是一個護士,當然了,我還想寫我和他們,那些瘋子。
—小安 《我們這兒是精神病院》
打電話去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找小安。
“哪(lǎ)個小安?”對方說,“我們這里沒有你要找的那個詩人,那個作家,我們這里只有個安護士,安學蓉嘛。”
在成都,四醫院不能算是個好單位。就像香港人說起青山都知道是精神病院,四醫院?成都人會告訴你:那是瘋子呆的地方。
而寫詩的小安,就是那個安護士,確實在這里上班。
小安當了三十年的安護士了。三十年前,她坐著火車,從重慶到成都,她是來結婚的,來投奔那個她認識不久的男人的。那時他們多么年輕,才20出頭,他剛見到她時,她還在軍醫大學念書,在窄小的宿舍里苦著臉讀黑格爾。是他帶來了詩,詩打開了她,然后他們又一起更新了詩——他成了詩歌運動“非非主義”的扛旗人,而她是那個不喊口號不說主張不聲不響卻寫出了這個流派中最美麗詩句的核心詩人。“我們聊也聊的詩,談也談的詩。詩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詩。”她的老朋友劉濤很多年后還記得她那時候最喜歡嚷嚷的:“寫詩好高興好幸福喲。”
詩人小安來到了四醫院上班。她被詩沖昏了頭腦,根本沒工夫考慮作為精神病院的四醫院和二醫院、三醫院有什么不同。不就是個工作嘛。第一天報到,她還是有點怵的,想到要面對瘋子,她化了個大濃妝,還是止不住見到每個瘋子都點頭哈腰,請求他們關照。老資歷的護士罵她:化這么濃的妝干嗎,又不是去相親!羞得她當場就想把臉抹掉。而瘋子們呢,擠在病房后面朝她指指點點,一個三十多歲的瘋子對一個二十多歲的瘋子說:“新來的,長得還可以,像天使。”她臉紅了。另外一個瘋子又鄙夷地宣布:“天使算個啥?老子是玉皇大帝。”
小安說,瘋子們是那么的瘋啊,你不可能不難過。就在她剛到四醫院的那一天,一個美麗的女瘋子,飛快地跑出了人群,脫光衣服跳進落滿櫻花的河里,再也沒有起來。在四醫院里,你不知道這樣的事什么時候會發生,它大概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而安護士們的工作就是竭盡全力地阻止它們的發生。每個護士分管一群瘋子,她們要像老鷹捉小雞里保護小雞的母雞一樣,24小時地照看他們,保證他們不被老鷹叼走——病魔就是那只老鷹。為此,她們每天要給瘋子們量體溫,喂他們吃藥,帶他們放風,舒緩他們的情緒,還要在任意兩個病人打架時及時出現,遏制住任何“瘋”的苗頭。小安說,精神病院護士們掙的錢里,有一項就是叫挨打費的,因為被瘋子襲擊是不能還手的。她年輕時值夜班,碰到過三更半夜兩個女瘋子吵架,互相抓住對方的頭發不放。“我跑上去試圖拉開,結果被兩個女人當成了又一個對手,揪住我的頭發,三個人互相不松手。我只好大叫,‘放手啊,放手,我是護士,我是護士!’最后總算有另外一個人瘋子跑出來,認識到我的地位,把我救了出來。”
和外頭一樣,瘋子們也喜歡自封為大人物—或許會比外面的人更肆無忌憚一些。四醫院里長年游蕩著“國王”、“上帝”、“玉皇大帝”,還有“委員長”。“委員長”是個女的,醫生護士看到她都會喊,“委員長”好,她對此十分享受,聽到了就像委員長一樣舉起右手說,大家好。如果不這么喊,她就會發脾氣,那么大家一天都不要清靜了。也有些出世之士,自稱“詩仙”的、“書圣”的、“孔老二”的。但瘋子們還都算識相,知道哪怕自己是國王,在這里也沒醫生護士大,而院長則在萬人之上。他們認為,只要院長判誰沒病,誰就能立即回家了。可是院長怎么會說這么傻的話呢?更何況,對于大部分長期精神病患者來說,他們的家,有等于沒有,大多都回不去了。
在小安看來,精神病人最大的痛苦是孤獨:病發的孤獨,有家不可能回的孤獨,作為“瘋癲”群體被文明邊緣化的孤獨,還有性的孤獨。老有瘋子跑去找院長申請:“院長,給我一個女人吧!”院長也都假裝很大方的說,“嗯,給你一個。”在四醫院里,瘋子們是不能談戀愛的,但總有人忍不住要拉拉小手。男瘋子們睡覺前一樣喜歡談論女人,有的瘋子會向往地問另一些瘋子:你們說,院長那么大的人物,會有多少個女人?五個?七個?還是十個?
一些瘋子會愛上護士,一些瘋子會愛上醫生。愛上護士的大抵是直接就被駁回了,愛上醫生的,安護士曾經收過一封信,一個瘋子拜托她過目、轉交:
“李細醫生:您好!我1971年6月23日出生在一個軍人工程師家庭。我父親是四川大學畢業的工程師,我母親是東北師范大學大學畢業的中學教師,1985年病逝。哥哥是技校畢業,姐姐是高中畢業,我是本科畢業。一家人都畢業了。很多人不懂的文化,我懂,我能看懂很多人看不懂的書。我現在很想和你成立一個家庭。”
除了情書,小安還收到過瘋子們寫的很多信。最常見的是寫給上帝或者溫家寶的,信上都說,自己是天使或黨員,是由其他某瘋子介紹加入的,現在被搞錯了,當成了瘋子,請上帝、國務院下達死命令,趕快把他們接出去。
“接的時候請帶一套衣服來,謝謝!”
看護瘋子們的人
一個混亂的人/在玻璃上眼淚汪汪的樣子/我們沒有辦法理清你的大腦/把你洗得更干凈些/也許你是最好看的那一個/又是最完整的那一個/在任何地方/你都如此顛三倒四
——小安《精神病者》
2008年的時候,小安開了一個博客。由于沒什么好貼的(她的詩歌出產量一直不高),她就開始寫點四醫院里的事情來玩。她寫“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故事,寫三十歲的王大立,每天蠢蠢欲動地想把地球當足球踢,寫每天站在窗邊、等待中央指示的國安局干部李名。還有發明家何筆,號稱掌握了宇宙的天機,喜歡給瘋子們解釋地球為什么在二十年之內還不會爆炸,后者們每天朝圣般地聽完,然后愉快地散去……“玉皇大帝”、“基督徒”、“上帝”、“委員長”、“護士小情”,這些人或確有其人,或是幾個人的拼貼—她是個詩人嘛,文學自然是離不開虛構的。
這些文章先是定期發表在一本雜志上,如今又成了一本書,《我們這兒是精神病院》。有一天小安居然看到她的一個病人在讀,神色如常,看到她還抬頭說了句“寫得好”。小安認為,外界對精神病院的想象歷來都是恐怖的,感覺籠罩著很大的黑暗,她作為一個護士,在里面確實度過了緊張、忙亂的三十年,目睹和經歷了非常多的病人的痛苦—但當她寫下這些的時候,她忍不住略去了那些痛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謙遜,她不認為自己有能力理解他們背負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她一貫的文字品格使然—詩人韓東說過,小安從未失讓她的語言失去優雅平靜的調子。

小安考慮過,她為什么沒有稱他們為病人,或者精神病患者這些可能更政治正確的名稱,而是用了“瘋子”這個直接的稱呼。想來想去,她認為:可能是因為她喜歡,她愛他們吧。她不能真的理解他們的痛苦,只能看著他們的天馬行空,看得她多少有些崇拜。瘋子,這個詞帶一點點嘲諷,一點點自嘲,看上去更能表達她對他們的感情啊。但愿他們會喜歡。
盡管已經在四醫院工作了三十年并且打算干到退休,小安的詩人朋友們仍然對她的職業感到驚奇。“她是個天生的詩人,卻又能在四醫院這個地方安之若素,真是讓人費解的事情。”詩人何小竹說。他曾試著設身處地去想象小安的職業生活,卻仍然想象不出她是怎么“熬”下來的。直到最近讀了她寫的“瘋子的故事”,他才有所理解。在小安筆下,瘋子們是快樂的,這種快樂也常感染到我們的安護士,這讓他相信小安平日里說的她喜歡和瘋子們在一起,并不討厭自己的工作是實話。事實上1998年的時候,何小竹曾接手過一本周刊,他把小安從四醫院里拉出來,短暫地做了幾個月的編輯。而小安在那幾個月里表現出來的不適應、不自在,讓他最終也不忍心再勉強她、挽留她了。
為什么會就這樣一直在四醫院呆下去了呢?有時候,小安也會想。當然不是說瘋子,瘋子么,總是一直在的,他們是四醫院和其他精神病院存在的理由呢。而她自己呢,以及護士小情、非哥、門衛老頭和院長呢,他們這些人,為什么會陪著瘋子們瘋一輩子呢?有一次她在花園和一個瘋子聊天,瘋子說,一切都好,就是沒有花姑娘。能不能給他一些花姑娘,讓住院生活變得激動人心?小安說,這個主意好。她發現自己呆得太久,已經習慣站在瘋子的立場上想問題了。或許這樣才是對的:把自己看成一個瘋子,因為在這里,瘋子才是普通人,像瘋子一樣,她沒有什么要求,也不敢去其他什么時空,只是站在這里,習慣性地、渙散而自由自在地呆在這里。
這兒是精神病院。有瘋子,有看護瘋子的人。繼續讀下去,護士小情,要離婚了,跟丈夫吃散伙飯,問護士小安,散伙飯吃點什么好。“我說吃火鍋,整濃烈點兒,辣得那個男人以后一吃火鍋就想你。小情說要得要得,就吃火鍋,還喝白酒,如果流淚,也是被辣出來的。她抽著煙,眼淚卻無聲無息流下來。唉唉,一個人,一生之中,總會有許多許多眼淚要流的。”小安的朋友,作家潔塵說,讀到這一段,她也要流淚了,整本《我們這兒是精神病院》,講的哪里是瘋子,講的是有這么一群人,他們跟我們所有人一樣,只是他們跟現實搞不好關系,于是就下了大路,走到一邊去了。
天上掉下來的詩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個人/站在太陽和月亮之間/你要做渾身爬滿雨水的鳥/你說雨呵/落在我頭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樹/再做一回銀杏/螞蟻和魚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著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徹底消磨一整天/做那個最懶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處》
始終存在的一個江湖傳言是:小安的詩,是天上掉下來的。
“哪里的話嘛。”小安說。她在微博上發過一條:詩非常難寫,恨不得把它殺了。
小安的詩不曾在大眾中走紅,她是那種詩人中的詩人:只有寫詩的人才知道,要寫出她的詩需要多么奇異的天賦。她最大的問題是寫得太少:上世紀80年代,她大概寫過100多首詩。而90年代,她只寫了30首。
90年代的小安干嗎去了?她坦言,離婚,然后心情不好嘛,喝酒,還有成日打麻將。
問她:牌桌上輸了幾十萬,后悔嗎?
——怎么可能不后悔嘛,不輸的話能買一套房子哩。
那時候她和詩人們來往得少,一圈子人為她干著急。韓東、何小竹、吉木朗格是其中批評得最起勁的幾個之一,他們怪說小安在麻將桌上耗費了太多的時間,而小安在面對朋友的批評時,也從來都是唯唯諾諾,承認自己懶,檢討自己沒有多寫一點。詩人中流傳著一個對小安的評價:跌在高處。他們認為小安從來不是那種因為向往好于是可以寫得更好的人,她從來沒想過要寫得更好,她只是寫了,便樹立了標桿。
小安的寫作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民間詩歌運動“非非主義”,她也是“非非”發起人楊黎的前妻。作為一個詩歌團體,“非非”素來以叛逆、喧嘩著稱。而身在其中的小安卻是安靜的,她“從沒有參加過任何情緒激動的爭論,也沒有任何自我確立的詩歌言論或主張,甚至連對批判的批判都沒有,好像這一切都于己無關”(韓東語)。小安的寫作因此而特別,當特別成為今天這個時代的自我標榜、自我夸贊、成為很多人的重大寫作目標甚至唯一目標的時候,小安的特別與眾不同。“她使用最單調的語言寫最不起眼的詩,毫無外在特征可言,卻能夠氣象萬千,實屬奇觀。”
每個寫作者與當時當地的環境總會構成某種關系,最常見的兩種是:緊密,或者刻意的疏離。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過一本詩集,《種煙葉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個功利效果上積極進取的詩人,但她也不是遺世獨立的拒絕者,“沒那么憤懣也沒那么緊張。”在韓東看來,小安的姿態就是沒有姿態,寫作對她來說,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沒人待見時很安詳,有人鼓噪時不擺譜。有足夠真誠卻絕不阿諛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準確,“我只能說那是一種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靜靜。詩歌觀點嘛,她說她還真的沒有。“我想,詩人,就是要一直寫,別停下。這個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