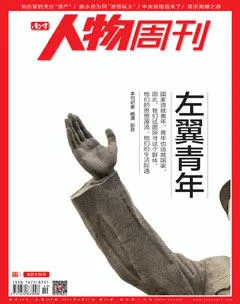當(dāng)左右在這里相逢

“開始扯吧——各位!”
5月的一天,下午3點,“黃河青年讀書會”(內(nèi)部簡稱“黃讀會”)的組織者王曉川,招呼QQ群“政治思想”里的左中右,群聊起第9期線上話題:反茅現(xiàn)象。
“既然談的是長沙反茅集會,我給大家推薦一篇文章——《“長沙會戰(zhàn)”中的河南兵團》,作者是鄭州毛派的一個頭目葛黎英。2011年以來,因為路線問題,已和我們分道揚鑣。借此我也想說明,他們只是毛派的另一派系山頭,我等不認(rèn)同他們思想的毛派也很多,不能一概而論。”
七嘴八舌中,王曉川逐一亮出議題:1、茅于軾引起爭議的觀點有哪些;2、茅于軾的觀點為什么引起輿論的激烈反應(yīng);3、反茅和擁茅所折射的社會現(xiàn)實……
有“黃讀會”成員告訴我,那次在群里,右派們擔(dān)心“反茅”妨礙言論自由。左派們則認(rèn)為,茅于軾是學(xué)者,擁有一定話語權(quán)。他的反對者多來自草根基層,沒有自己發(fā)聲的渠道,只能以過激行為引起社會關(guān)注,
他透露,“有時候,曉川是‘舌戰(zhàn)群右’。前兩年,網(wǎng)上集體公訴茅于軾,在他看來,那是時代進步的表現(xiàn)——懂得走法律途徑。”
恰同學(xué)少年
“強調(diào)一下,我是毛左里的新左。”王曉川說。
他生于1982年,曾在河南大學(xué)主修公共事業(yè)管理,目前在河南省某商會辦的一份內(nèi)刊任編輯,自稱,受20世紀(jì)中后期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國內(nèi)新左派學(xué)者汪暉的學(xué)術(shù)影響頗深。
“茅于軾不應(yīng)該是當(dāng)下的核心議題,我們也不想讓某些人樂見左右相爭。盡管我反對他的一些觀點,可我覺得不能將官商結(jié)合、國企改革后涌現(xiàn)的弊端算在他頭上。”他還表示,如果茅于軾肯來鄭州,他愿意幫助其開辦講座。
“不怕發(fā)生抗議?”我故意問他。
“不怕。我有經(jīng)驗。”那張圓臉泛起微笑。他的自信,來自河南左中右對“黃讀會”的公論:各派在這里各抒己見,觀點碰撞,但遵守基本的辯論規(guī)則。

王杰比王曉川小4歲。這位熱衷三農(nóng)問題的農(nóng)家子弟,渾身透著書生氣。他是“黃讀會”里“進步青年讀書小組”負(fù)責(zé)人,也是讀書會最早發(fā)起者之一。
2006年從河南農(nóng)大畢業(yè)前,作為校內(nèi)農(nóng)研會骨干,他與其他老會員一樣,不愿就此隱退,于是眾人醞釀,把過去的下鄉(xiāng)實踐融入日常學(xué)習(xí)中去,黃河青年讀書會由此而來。經(jīng)他人引薦,王曉川加入進來。很快,兩人一拍即合。
2007年9月9日,10名成員“特意挑選毛主席逝世日”,宣布“黃讀會”正式成立。王杰記得,那天在鄭州紫荊山公園里,他們與一些老工人在毛主席像前獻(xiàn)上鮮花。祭奠完后,大家圍繞“青年毛澤東”交換心得。
他解釋,選擇這一議題時逢電視劇《恰同學(xué)少年》熱播,“另外,我們的傾向都偏左。”
一年后,王曉川繼任,“他們或工作或考研,一個個走了。我一直很積極,既然我來做,就要完全實現(xiàn)我的理想——我要讓熱心政治時事的各派人物,聚集一處,充分交流。”
早在“黃讀會”成立前,他就拜訪過鄭州思想沙龍的元老袁庾華,并由他引入到沙龍。“他想成為青年理論家。”沙龍的另一元老級人物邵晟東說。
邵的父親在世時,曾任洛陽地委書記、河南省副省長等要職。他是偏自由派觀點,90年代中期,與“思想西化”的林楠、“永遠(yuǎn)的造反派”袁庾華,共同建立“鄭州思想沙龍”,從而奠定沙龍基調(diào):左右兼容。如今的“黃讀會”也秉承這一特色。
沙龍里,袁庾華的經(jīng)歷最傳奇。“文革“中,袁由肉聯(lián)廠工人造反起家,擔(dān)任過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頭目,參加了7個造反派組織的“奪權(quán)”行動,當(dāng)過幾天省政法領(lǐng)導(dǎo)小組負(fù)責(zé)人。曾因是極左,3次入獄。“文革”結(jié)束后又被判刑12年。
邵晟東住在父親留下的機關(guān)住宅,再過幾條街區(qū),是袁庾華的家。那里毗鄰的是一個已被政府取締的“廉價紅燈區(qū)”。
極其雜陋的屋中,一張毛澤東與江青的合影畫像非常醒目。袁庾華坐在舊椅上大聲說,“北京發(fā)起公訴茅于軾的活動時,河南有很多人簽名。據(jù)一些年輕人反映,他們的名字是冒簽上去的。這事你可以問王曉川和‘進步青年讀書小組’。對于茅于軾的言論,我們是不贊成,但批評歸批評,絕對不會阻撓。我們反對別人對我們的壓迫,同樣也反對壓迫別人。”
當(dāng)初,也是他建議王曉川不要讓“黃讀會”與鄭州“老毛左”攪和在一起——“自由派陳子明在《中國左派的光譜分析》里,將左派分為馬左、毛左、新左。馬左與毛左的根本分歧是,馬左與官方一氣,否定‘文革’。而像我這樣,‘文革’中遺留下來的老毛左,與尋找中國出路、找到毛澤東主義的年輕一代,組成現(xiàn)在新的毛左。雖然同是左派,曉川的出發(fā)點與我們畢竟不同。我們明確是要推動社會運動。他們辦讀書會,是為了認(rèn)識這個社會。”
各方登場
劉源斜挎書包,匆匆趕來。他是中學(xué)老師,喜歡近代史,即將去上海讀博。在“黃讀會”,他組織“銳釘讀書會”和“鄭風(fēng)電影沙龍”。他關(guān)心時政,源于閱讀哈耶克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書籍,“那時腦子里還沒有左右的概念。”
2009年,他在鄭州大學(xué)讀研,同學(xué)介紹他認(rèn)識王曉川。之后,他去過“黃讀會”,發(fā)現(xiàn)政治氣氛較濃,“大家都認(rèn)真談?wù)撘粋€個嚴(yán)肅話題。”
那年9月,王曉川帶他到卡內(nèi)基學(xué)校,聽袁庾華講美國保守主義。歸途中,他們在夜色下暢談。“那一刻感覺真好。身邊的人不關(guān)心公共生活,整天盡聊網(wǎng)購、韓劇,與我沒有共同語言。”劉源當(dāng)即決定加入。
他慢慢摸清讀書會的流程:在豆瓣、飛信、博客上發(fā)帖。聚會地點常是“南邊一咖啡廳”、“北邊一茶館”,后來也與學(xué)校合作。至今讀書會都恪守“零成本運作”,遵循著“反資本主義實踐”。2011年,“黃讀會”有意識淡化政治色彩——組員憑興趣,自組傳統(tǒng)文化、科普、哲學(xué)、財經(jīng)小組,但仍然保持了左右交流。
“我們講究秩序。沒有主講人時,先擬問題,每人闡述自己想法,之后自由討論。有主持人時,主持人要把控每人的發(fā)言時間,哪一位說得激動了,主持人馬上喊停。”劉源比劃著,他已主持過幾期講座。
2011年夏,“黃讀會”開設(shè)“鄭風(fēng)講壇”,最牛的一次是請到學(xué)者秦暉來演講。那一次,劉源才真正意識到,王杰原來比王曉川更左。
那場演講中,秦暉再次肯定土地私有化,提問時,王杰向秦暉談到資本限制、公屋住房,“更多像在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站在學(xué)術(shù)角度,他是對的。可是,中國土地兼并不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農(nóng)民是在社會不提供信用機制、生活被迫無奈下,才將惟一的生活資料賣掉。這不是正常社會邏輯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應(yīng)該制止,我不贊同自由放開土地。整個社會是自由遷徙,不能為讓農(nóng)民待在城里,將他們趕出土地。總要讓他們手上存點東西,保有選擇的余地。他還提出,在城市,為混得不好的農(nóng)民建‘貧民窟’,我也反對。政府應(yīng)該對這一群體給予照顧……”王杰談他的不認(rèn)同。
“烏有之鄉(xiāng)”代表人物之一韓德強也曾來主講“反經(jīng)濟全球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說法。他們支持經(jīng)濟市場化,反對政府壟斷,反對搞計劃經(jīng)濟。”
是否限制經(jīng)濟全球化,在“黃讀會”內(nèi)部,從來各執(zhí)一詞。左派反對一味全球化,它致使中國陷入農(nóng)業(yè)、自主產(chǎn)權(quán)等方方面面的挑戰(zhàn);右派則認(rèn)為,資本本身無對錯,社會問題當(dāng)屬政府管理,資本意味著繁榮商機、就業(yè)機會增加。

劉源與王曉川都提到,2010年,“黃讀會”請來歷史學(xué)者雷頤。那一次,雷頤先在咖啡廳講晚清史,后來又在小型聚會上講少年時期他在鄭州親歷“文革”。因為左派的廣而告之,袁庾華、葛黎英等人紛紛到場。
“主持人是左派——王曉川,邀請我的卻是兩名自由派。現(xiàn)場更奇特,有人支持改革開放,有人別著毛澤東像章,還有人戴著孫中山像入場。大家共處一室,大體相安無事。”雷頤回憶當(dāng)天的情形。
會上,雷頤講到“文革”中有人考大學(xué),政治成分不好,無法通過政審,不得不行賄。自由討論時,葛黎英否認(rèn)道,當(dāng)時的社會沒有腐敗,分配公平。雷隨后反駁。
“聞出點火藥味”時,“黃讀會”一名右派跳出,加重對峙。戴孫中山像者則向兩派宣揚“民國熱”……
“居然有人仍打出‘文革’口號”,雷頤反思起運動中武斗雙方為對國家領(lǐng)袖表忠心甘愿獻(xiàn)身。可那樣的死,算不算犧牲?到底值不值?結(jié)論是,無論哪一派都是被政治左右,都是受害者。
“袁庾華卻說,我的同情是對造反派的一種侮辱,盡管他在‘文革’中飽嘗牢獄之苦,卻依然贊揚‘文革’偉大,造反有理。”雷頤說。倒是有一點讓他意外——期間有人打斷葛黎英發(fā)言,她溫和地說,請你讓我把話說完。“歲月也許真的會改變?nèi)恕O氘?dāng)年造反派中,她的性情何其激烈。”
那場講座后,劉源想去探索“文革”史,“歷史述說太單一。要么官方語境,要么右派控訴。”為此,他采訪了袁庾華與葛黎英。過后感觸尤深:“有些人永遠(yuǎn)活在那個年代。他們所有的邏輯、生活基礎(chǔ)、看待事物都以那一時代為標(biāo)準(zhǔn)。”
誰立場先行?
2011年,應(yīng)袁庾華之約,他的朋友,廣外教授張寧領(lǐng)來兩名學(xué)生與王曉川等人,在一茶樓展開對話。
“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看得出來,雙方都缺少對話的必要準(zhǔn)備,都認(rèn)為自己握有不容質(zhì)疑的真理。他們爭論的,都是容易上火的問題,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文革’的評價。”張寧聽到年輕的左派聲稱,我們懷念毛時代,不是要回到毛時代。
王曉川概括他的“文革”觀——“關(guān)于‘文革’,首先是她失敗了,中間出現(xiàn)過巨大悲劇,毛澤東主動終止了她。其次,更重要的,這是毛澤東和中國民眾關(guān)于在政黨政治外,通過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防止革命退化、推動民主深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對60年代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青年運動和新思潮,起了重要的啟示和鼓舞作用。”
他承認(rèn),“我對某些正面態(tài)度的東西會用‘她’來代替‘它’,比如指代中國。”
“為什么現(xiàn)在越來越多青年人、勞動人群趨于左派?”王杰說,“不是說他們信仰毛澤東,而是他們切實感到,通過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變命運。市場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法則教育他們,中國沒有自由競爭,他們沒有平等向上層游動的機會。他們會思考,為什么社會不公平?同樣具備能力,卻實現(xiàn)不了自己的理想?他們會得出答案,這不是自身問題,而是社會結(jié)構(gòu)有問題,這個社會規(guī)則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會,追求一種公平?這恰好構(gòu)成他們左的思想。”
他提到,“進步青年小組”里有個叫大寶的搬運工,每天起早貪黑,肩扛四百來斤重荷,晚上又臟又累回到出租屋,為了省錢,初冬時節(jié)也只能洗冷水澡。
我看了一段視頻:大寶一天的血汗錢——兩張印有毛澤東像的鈔票攤在桌上,他大聲質(zhì)問:我做過8年煤礦工人,今年42歲,在這座城市沒有立足之地,沒有結(jié)婚。難道我沒有勞動?我的勞動果實哪去了?都是被官僚資產(chǎn)階級剝削去了,被資本家剝奪去了。
“可他們不相信1959年的信陽事件。”邵晟東面色沉重地說。有一次,“黃讀會”內(nèi)讀報,讀到一篇對大躍進的報道時,一個左派懷疑:餓死人是有的,可官方公布的數(shù)字準(zhǔn)確嗎?又惹來一場爭論。
“對信陽事件,袁庾華嚴(yán)重立場先行。起初他否認(rèn),后見否認(rèn)不了,就把全部罪責(zé)推到走資派身上。他向青年人散播謬論,還說他到過信陽,深入調(diào)查過死亡人數(shù)。我說那是蜻蜓點水。”邵對此很不滿。有一次兩人僵持不下,他曾指著袁庾華說,你要是再執(zhí)迷下去,我就給你的人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不清楚老袁的說法,我只談我的。信陽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過訪問,據(jù)說嚴(yán)重程度沒那么大。會不會是統(tǒng)計或政治原因,造成數(shù)字夸大?從責(zé)任上講,我們應(yīng)去批判官僚體制異化——地方官瞞報災(zāi)情,人民的公仆淪為特權(quán)階層。所以,這不是一個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責(zé)任。”這是王曉川的觀點。
“他們怎么形成今天的思維?”張寧很想探知。他曾與“黃讀會”的年輕左派討論,他覺得:這些年輕人往往從理論上理解過去,比如“文革反權(quán)威”、“毛主席說中國人民會解放”。他們會先驗性取材——一旦接受運動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里暴露的“負(fù)面”。
“你們不能總拿經(jīng)歷來壓我們。說到先驗性——有些右派正因為經(jīng)歷,放不下個人恩怨,將自己承受的痛苦賦予整個社會群體。今天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他們的敘述必定站在精英XBtKH0GcAuSObhuS6yz3Lg==角度上。那么,平民老百姓的回憶呢?”王杰反問道。
“一個地方餓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錯。可如果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餓死人的現(xiàn)象呢?”雷頤追問。他曾文分析,改革開放初期,有段時間允許公開評論“文革”,后來禁止具體談?wù)摚皇欠穸ā拔母铩薄?0年代后,雷頤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描寫知青歲月,藍(lán)天白云能夠談,殘酷事實不能談”。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烏有之鄉(xiāng)”運營人范景剛專程趕來鄭州,會見這批新老毛左。
這一年,中國左派內(nèi)部從分歧走向論戰(zhàn),繼而分裂。學(xué)者陳子明將左派分為兩大陣營,一方是以“烏有之鄉(xiāng)”代表人物張宏良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華等“造反派”。
“張宏良在重慶的演講很讓我們反感——因為我們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來就該站在下面。”在王杰看來,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機心理的人劃出去,讓關(guān)心底層與社會進步的力量更純粹。”
當(dāng)天,范希望在座左派能接受他們的觀點,“聲明他們的選擇,也是為與高層左的力量相呼應(yīng)……”袁庾華等人的表態(tài),讓范景剛失望而歸。
“老袁不像其他老左派一樣緊盯上層變化。他主張21世紀(jì)是社團政治時代,社會變化不在黨內(nèi)而在民間組織。他認(rèn)為‘文革’是群眾自發(fā)組織。我從西方社會運動上思考,即便社會上存在比較理想的政黨機制,但作為一個組織,也會與自己的理想出現(xiàn)差距。這時怎么辦?誰來監(jiān)督制約它們?這時更需要自主性的民間團體。民間力量成長起來,就能對社會統(tǒng)治形成制衡,我覺得這就是民主。民主是上下得到緩解,得到均衡。”王曉川說,這一想法在“黃讀會”得到認(rèn)同。
這個新左派在以一種驕傲的目光審視他的前輩——“他們的立場比較徹底,更認(rèn)同共產(chǎn)黨早期的理念。他們會對毛的言論著作,包括各種奇聞軼事掌握較多。他們更民族主義一點、更國家主義一點,基本上還是老一套思維。而我們關(guān)注的是,處理好3個方面的關(guān)系,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guān)系、不同派別山頭之間的關(guān)系、民間與官方之間的關(guān)系。”
在這個圈里,也有一些根本是不變的——“當(dāng)體制內(nèi)精英侵犯弱勢群體,大家一致憤慨。比如鄧玉嬌事件。”從“鄭州思想沙龍”到“黃讀會”,無論老中青,左中右,有一問題是相通的:中國將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