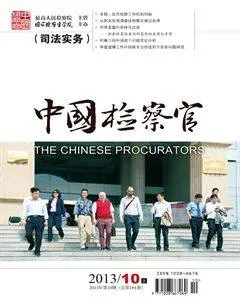完善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的思考
在我國,對刑事審判進行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責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我國檢察機關擁有刑事審判法律監督權,是當前我國訴訟監督權配置的一種既存狀態,同時也是歷史發展自然延續的一種結果。不容置疑,檢察機關在過去的監督審判權正確行使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國民素質的提升,黨和人民群眾對訴訟監督工作的要求不斷提高,刑事審判法律監督一直未能充分有效地體現制度的設置初衷,現行的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暴露出不少問題和缺陷。我們應當積極利用全面貫徹實施修改后刑訴法的有利時機,充分認識我國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進一步健全刑事審判法律監督體系,以促進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面對的困惑
(一)監督理念:“重實體處理,輕程序正義”存在
由于我國的歷史背景和法律文化的影響,以強職權主義為核心的執法理念在我國的檢察實踐中表現得相當明顯。長期以來就存在著只要實體處理公正了,程序只不過是一道道無關緊要法律手續的“重實體處理,輕程序正義”的傾向,使得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形成了這樣的特點,即對刑事實體問題和訴訟程序問題分別采用剛性監督和彈性監督的方式,這顯然不能滿足維護程序公平和正義的需要。一是“庭后提出”的規定影響監督效果。無論是“六部委規定”還是《規則》都規定,檢察機關對于法庭違反法定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的時間是“庭審后提出”,而非當庭提出,從而影響了對某些重大程序違法行為的監督效果。二是對庭審前后的一些程序性行為的監督缺乏法律依據。如法院開庭前對當事人委托辯護人、委托訴訟代理人及附帶民事訴訟的告知,開庭、宣判日期的通知,判決書的送達時間,等等,都直接關系到對當事人訴訟權益的保障,但實踐中檢察機關對此類問題缺乏知情權,無法開展法律監督。三是對法院隱性侵害被告人權利的行為監督不到位。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隱性侵害被告人權利的行為時有發生,如案件久拖不判、隨意延長審限、決定延期審理,被告人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案件,法院的審理期限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期限等等,造成了對被告人尤其是在押的被告人合法權利的隱性侵害,檢察機關對此監督往往不到位。
(二)職權行使:普遍存在著“四個難”
一是法定幅度內量刑不均衡的案件改判難。雖然法院在法定刑幅度內量刑不公正的現象時有發生,但在司法實踐中,二審法院對待抗訴案件的一般認識是,只要是在法定刑幅度內適用刑罰的,就視為量刑適當。上述做法,導致相同的案件得不到平等對待,導致法定刑幅度內量刑不合理、不均衡的判決無法糾正。二是適用緩刑的案件抗訴難。我國刑法對于緩刑適用的條件是“確實不致危害社會”,因為這個條件相當原則,可操作性不強,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難以準確把握。尤其是對于一些本該判處三年以上實刑的案件,法官卻“法外開恩”,“一竿子插到底”而對其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對此類判決,檢察機關即便認為量刑畸輕,適用緩刑不當提出抗訴,二審法院一般都不予以支持。三是有法定和酌定情節的案件抗訴難。有法定和酌定情節的案件,依法應當或可以從輕、減輕或從重處罰,這是刑法明確規定的。但是,應當或可以從輕或從重幾格幾檔,刑法的規定是不明確的,主要依賴的是法官主觀判斷上的因素。這樣,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自由裁量權濫用的現象不可避免,比如,只要是具有重大立功的,無論重罪還是輕罪,就予以免除處罰。對此情況,檢察機關即使抗訴,法院維持,檢察機關也顯得無所適從。四是有爭議的案件改判難。有爭議的案件有兩種,一種是法律適用問題存在爭議的案件,另一種是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存在爭議而導致適用法律存在爭議的案件。對第一種情況,抗訴的案件較多,很多時候也得到了二審法院的支持。而對第二種情況除對無罪案件提請抗訴以外,因擔心案件爭議較大,同時也怕影響兩家關系,檢察機關抗訴較少,即使檢察機關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法院認定事實或量刑錯誤而提出抗訴,這類案件也很難獲得二審法院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抗訴案件改判率。
(三)監督范圍:存在一些“盲區”
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這其中當然包括對法院整個刑事審判活動進行全方位的監督。但從實踐中看,卻存在以下“盲區”:一是自訴案件監督出現空白。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存在錯誤認識,認為自訴案件是法院單獨管轄的案件,與己無關。因此,審判監督也只監督公訴案件。對于不經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自訴案件,由于從訴訟程序上講,不經過檢察院,所以也不在檢察院的審判監督范圍之內。另外,對自訴案件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自訴案件都是些犯罪情節較輕,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案件,或者不告不理,對這類案件的審判監督可有可無。二是附帶民事審判活動監督出現盲點。由于附帶民事審判活動監督附屬于刑事訴訟,刑事審判人員存在“重刑輕民”思想,當事人的民事權益往往得不到充分考慮,再加上刑事訴訟法及《規則》又均未有相關的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公訴部門還是民行檢察部門對附帶民事訴訟,都很少關注。三是檢察機關對刑事審判的監督還是局限在對未生效或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提出抗訴上,而法院的判決或裁定形成過程往往是在不公開狀態下產生的,也無法對其程序性違法行為進行監督,監督的著力點僅僅是落在結果上
(四)監督職能:正在不斷地趨向弱化
長期以來,檢察機關的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查起訴、監所檢察等與公安機關有關的監督程序,都是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一物降一物”,這決定了公安機關接受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比如,偵查監督環節的監督者(檢察院)對被監督者(公安機關)報送的案件嫌疑事實及其法律評價擁有完全的裁決地位,即使作為被監督者不服監督者的不批準逮捕決定,進而提請復議和復核,決定權也仍然在作為監督者的檢察機關手中,對此,檢察機關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也相對高一些。但相比之下,刑事審判法律監督的最終裁決權在法院,也就是說,在法庭上法官、法庭就代表法律。我們的抗訴權僅僅是一個程序啟動權,監督是否準確,最后都應當服從于法院。由此而導致,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在整個訴訟監督體系中的地位實質上呈現下降趨勢。檢察機關作為憲政層面上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理應承擔更加重要的任務,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實踐中我們卻發現,人們往往抱著“法治不如人治,人治不如批治”的信條,總是把目光投向了“領導批示”或“清官私訪”上,意欲通過信訪渠道來實現其監督作用。由于批示的結果究竟是惡或善,往往取決于領導的個人素質和個人魅力,因而這種“不批不治、一批就治”的現象不但影響了司法獨立,而且對整個法治建設都有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如果本該由法律最終解決的問題卻總仰仗批示,那么,中國的法治建設只不過是繞了一個怪圈又回到了人治而已。[1]“批治現象”的盛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正好折射出了檢察法律監督職能在弱化。
二、完善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的思考
(一)制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監督法》
目前,我們開展刑事訴訟法律監督工作的具體依據是修改后《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規則》等,應該肯定,上述國家基本法和部門規則所構建的刑事訴訟法律監督制度的基本框架大體上是符合我國憲法所確定的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基本理念及我國的實際情況的。但是,筆者認為,無論是散見于國家基本法還是規定于部門規則中有關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內容都仍過于原則,可操作性與細化不夠,特別是在有關增強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剛性和力度方面更顯軟弱和不足。所以,要在條件成熟時,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國家立法機關提出立法建議,制定具有一定法律階位的、系統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監督法》(以下簡稱《監督法》)。我們尤其是要在《監督法》中明確賦予檢察機關切實可行的、具備一定強制性的刑事審判法律監督權,如確認權、糾正權、建議權、復議權等。建立和健全行使監督職能的相關程序,賦予監督者以必要的手段,規范監督者運用監督手段的行為,明確監督者的責任和被監督者的義務以及相應的追究責任機制,不履行義務的消極后果和救濟措施,通過合理分配監督機制中的權利義務,保證監督機制的有效運行,增強監督的剛性和力度,[2]這樣,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制度在我國的實行才不可能出現尷尬的局面。
(二)擴張刑事審判法律監督的范圍
在系統制定的《監督法》專章“刑事審判法律監督”中,應當在其第一節中獨立設定“刑事審判法律監督范圍”專節,具體而明確框定檢察機關開展刑事審判法律監督的范圍。因為檢察機關對BO5NkI/tdcyjhbDsjWLBxA==法院審判活動進行全方位監督,即除了對法院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及案件受理、審理和送達期限、法庭組成人員、庭上審理程序等進行監督外,還應該將對公訴案件庭前審查程序、自訴案件的審理程序、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程序和死刑復核案件的審理程序一并納入到刑事審判法律監督的視線中。同時,還要增加對二審法院書面審理案件、法院庭外進行的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等調查活動,采取逮捕等強制措施以及判決書、裁定書的執行活動的監督,以形成一個完備、嚴密、科學的刑事審判法律監督體系,從源頭上避免監督盲區的出現。
(三)賦予檢察人員當庭監督的權力
“六部委規定”及《規則》有關“庭后監督”的規定,有違刑訴法立法本意,應予糾正。開展當庭監督能及時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程序正義。同時,對庭審活動的監督應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法庭組成人員是否合法;(2)審判程序是否合法;(3)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是否得到保障;(4)是否違反法定訴訟時限;(5)就程序問題所作裁定或決定是否合法;(6)有無枉法裁判,挾嫌報復或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7)有無漏罪漏犯;(8)裁判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上是否正確、合法;(9)宣判程序是否合法;(10)其他違法問題。[3]
(四)強化二審抗訴阻卻一審無罪判決的生效和執行力
修改后刑訴法第249條規定:“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免除刑事處罰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應當立即釋放。”從該條的立法原意來看,是指只要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免除刑事處罰的,無論檢察院是否抗訴,一審宣判后立即生效。從保障人權和維護審判權威的角度分析,這一規定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法院裁判確實存在錯誤,一些被告人唯恐自己受到法律的懲處,在法院宣判無罪或免刑之后,立即逃跑,這樣,即使檢察院提出抗訴,二審法院因為被告人不能到庭而無法開庭審理。基于以上理由,我們認為,有必要將刑訴法的上述條款修改為,“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無罪、免除刑事處罰的,如果被告人在押,而人民檢察院在法定抗訴期限內又沒有提出抗訴的,應當予以釋放;若人民檢察院在法定抗訴期限內提出抗訴的,應當變更為取保候審。”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檢察機關按二審程序的抗訴順利進行。
(五)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內設立監督司法機關工作的專門組織
實際上,1954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7條已經有過類似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如果對審判委員會的決議不同意,有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處理”。這必將有利于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的法律監督作用,解決司法機關在執法中存在的混亂現象,督促司法機關糾正違法、錯誤的決定,促使司法日趨公正、客觀。[4]因此,筆者建議,最高檢對最高法已經生效裁判提出的抗訴,最高法裁判駁回的,最高檢仍然認為最高法裁判確有錯誤,可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司法工作的機構應根據事實和法律,并在充分聽取“兩高”的意見后作出審查決定,對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兩高”必須執行。
注釋:
[1]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改革理論與制度創新》,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頁。
[2]謝鵬程:《監督權的控制和運用》,載《檢察論叢》,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頁。
[3]馮耀輝:《論審判監督的完善》,載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編:《檢察理論研究集萃》,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頁。
[4]馮耀輝:《論審判監督的完善》,載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編:《檢察理論研究集萃》,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