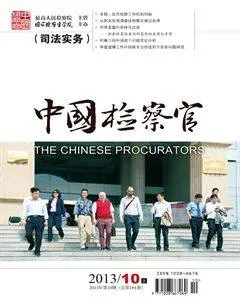多元化監督格局下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初探
一、新格局下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內涵
2012年修訂的《民訴法》第210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因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需要,可以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有關情況。”它首次從國家基本法立法層面確立了檢察機關在民事檢察中的調查核實權,有效地保障了檢察機關信息獲取的全面性和及時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雖然法律的規定精簡而原則,但結合新法對民檢職能多元化的配置,民事檢察的調查核實權應具有以下內涵:
(一)目的的監督性
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其所有的職權都由檢察監督權派生而來,必須圍繞法律監督目的的有效實現和職能的充分履行來展開。[1]因此,民事檢察中調查核實權是為了實現對民事訴訟運行全過程的正確評價,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而設,這不同于當事人一方為維護自己權益而進行的調查,也不同于人民法院已解決糾紛為目的進行的調查。
(二)范圍的有限性
根據民訴法中民事檢察監督職能的構建,調查核實權的范圍也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對案件事實的調查,主要通過對原審中相互矛盾的證據進行辨別,排除虛假證據,從而對原審判決是否存在證據采信不當的錯誤作出認定,重在對已知證據的核實。另一類是對訴訟活動中各方行為的調查,通過形式審查,作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認定,重在對隱蔽違法行為的調查。除此之外,檢察機關不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否則極易破壞民事訴訟的平衡。
(三)地位的中立性
民事檢察監督是超脫于原審的,因此民事檢察中的調查核實權具有比原審法官更中立的屬性,它不僅不介入當事人的利益,甚至也不介入對民事糾紛實體權力義務的評判。核實原審中的證據并非對為了增強某方證據的證明力,而是體現了檢察機關慎用抗訴手段的指導思想,也與再審程序的補充性、救濟性相適應,目的在于實現保障當事人再審訴權與保障法院裁判穩定性之間的協調。[2]因此,不論所調查核實的證據是否有利于當事人,均應同等對待。而在訴訟活動監督中針對違法行為開展的調查則更體現了檢察機關超然于原民事糾紛之外的中立性。
(四)措施的非強制性
民事檢察的調查核實措施不能超越民事訴訟的領域,不能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帶有國家壟斷性強制力的調查措施。即便調查的對象是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也旨在查清是否存在影響民事訴訟司法公正的情形,而不是出于懲罰犯罪的目的,故而從民事檢察的角度,也不能采取強制措施。
(五)功能的社會性
修訂后的民訴法賦予了民事檢察更多的社會化職能,凸顯了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護以及對訴訟行為正當性的監督。因此,新格局下民事檢察中的調查核實不僅僅局限在原審訴訟范圍內,而在對訴訟調解侵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監督中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此外,檢察機關為保護社會弱勢群體而探索開展的支持起訴等工作,也在一定范圍內依賴于調查核實權的行使,這也同樣也是調查核實權功能社會性的體現。
二、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規范
修訂后的民訴法賦予了檢察機關在民事檢察中的調查核實權,但這條規定比較原則,而原來關于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規定已不能完全適應發展后的民事檢察職能,相關的具體權力運行規范亟待建立。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五個方面對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進行規范:
(一)限定調查核實權的適用范圍
在進行抗訴監督時,應堅持以書面審查為主的原則。在證據不充分時,應主要依據舉證責任作出事實認定。就案件事實方面,僅在對同一事實出現兩份矛盾的證據時,可以圍繞該證據進行核實。此類調查核實,目的在于排除矛盾證據,增強內心確信,除特殊情況外,不超出原審調查新證據、新事實。而在進行訴訟活動監督時,只要有一定線索表明可能存在違法行為或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則可以圍繞該線索展開調查,而不以原審范圍為限。具體而言,有以下情形:1.原審裁判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2.原審當事人或第三人在原審中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而未調查收集的;3.申訴人在申訴時提出的證據符合再審中的“新證據”標準,但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4.民事訴訟活動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5.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可能有貪污受賄、循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的;6.雙方當事人對同一基本事實提供的證據相互矛盾,原審可能采信虛假證據的。
(二)嚴格調查核實程序
首先,要限制調查核實的內容,僅僅圍繞訴訟監督的目的,就需查明的事實開展。在抗訴監督中,原則上不就新的證據進行調查。其次,要嚴格調查的手續和方式。在承辦人認為有必要進行調查時,應當并書面報領導審批,并寫明調查的內容、原因、方式和目的。經審批同意后,應當由兩名以上檢察人員攜帶介紹信、工作證或其他證明材料共同調查。調查材料應當由調查人、被調查人、記錄人簽名或蓋章。再次,嚴格區分啟動調查的情形。對“新證據”進行的調查應當依當事人申請而啟動,因此時的調查實際是為彌補當事人舉證能力不足而設,當事人享有法律范圍內的處分權,檢察機關不能主動行使。而其他類型的調查核實,檢察機關可依職權啟動。
(三)明確調查核實的措施
在調查核實過程中,檢察人員不得采取惡意威逼、欺騙或其他侵害被調查人合法權益的方式,不得限制和剝奪被調查人的人身權利,也不得采取查封、凍結、扣押等限制財產權利的措施。筆者認為,《人民檢察院民事檢察辦案規則》征求意見稿中第53條所列舉的調查方式的前四項可以作為規范調查措施的規定,即:1.向有關單位查詢;2.詢問當事人、證人、知情人;3.委托鑒定、評估;4.現場勘驗。但第五項“其他必要措施”的規定,實際為調查權提供了無限的解釋空間,難免留下權力濫用的隱患,該項兜底條款的規定值得商榷。此外,在審查環節進行重新鑒定須以原審鑒定程序違反相關規定為前提,避免一個案件多次有效鑒定相互矛盾的情形。
(四)保障調查核實權的正當行使
沒有保障機制的權力不是權力。為了保障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效果,必須建立配套的保障機制。一是明確被調查人接受調查的義務,包括當事人、證人、知情人接受詢問,提供證據原件鑒定、評估等;二是明確有關單位協助調查的義務;三是建立異地檢察機關委托調查、上下級檢察機關協助調查的制度,確保調查核實高質高效;四是明確調查核實權行使的后勤保障制度,如需進行鑒定、評估、勘驗時,相關費用支付的問題;五是明確對妨礙調查的法律責任。
(五)正確對待調查取證的效力
檢察機關在訴訟行為的監督過程中所調取的證據作為發出檢察建議或糾正違法通知的依據,具有直接的證明力。這類證據應附在移交的卷宗之內,但無須對此作專門的說明,除有充分證據推翻外,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而在抗訴監督中則應當遵循證據開示原則,依據《民訴法》第68條“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之規定,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仍應經過庭審的質證方能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這類證據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關于詢問筆錄的證據效力。檢察機關在審查環節制作的詢問筆錄,其目的是作為是否提出抗訴或檢察建議的依據,而依據民訴法的規定,證人證言原則上應當出庭作證才具有效力。因此,除非證人具有不能出庭作證的法定原因,否則檢察機關的詢問筆錄不具有證人證言的證明力。二是檢察機關委托的鑒定、評估的效力。同樣,其目的也是為評判原審是否錯誤而提供參考,原則上其效力不能及于再審中的事實認定,但若雙方當事人對該鑒定意見不持異議,再審也可直接引用作為裁判依據。三是證據展示主體。檢察機關調查核實證據系出于監督原審的目的,故原則上檢察機關應當庭出示調取的證據,并作出說明。但若該證據是依據當事人申請而調取的,則應由當事人自行舉證。總之,檢察機關在民事檢察中調查核實證據,不僅應當確保證據具有“三性”,還應當具備檢察機關調查核實證據的正當性。
注釋:
[1]鄭青:《民事法律監督調查權的內涵與實踐功效》,載《人民檢察》2011年第11期。
[2]趙信會、宋聚榮:《論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的證據調查權》,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年第16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