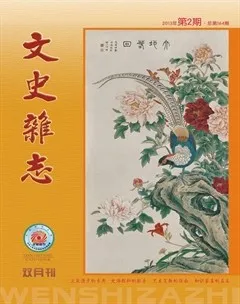延安整風(fēng)運動中王實味冤案始末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xué)典禮上所作的《整頓黨的作風(fēng)》,2月8日在延安干部會上所作的《反對黨八股》兩次演講中,強調(diào)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xué)風(fēng),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fēng),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fēng),這就是我們的任務(wù)。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wù),必須要完成這個整頓黨內(nèi)作風(fēng)的任務(wù)。”“……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毛澤東同志這一重要論斷,對整風(fēng)運動的方針、目的、任務(wù)和方法,作出了明確深刻闡釋。為使整風(fēng)運動順利開展,中央倡導(dǎo)發(fā)揚民主,讓群眾“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黨內(nèi)干部中存在的黨風(fēng)問題提出意見和批評。1942年3月5日,中央主管整風(fēng)運動常務(wù)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大禮堂召開干部大會,對整風(fēng)運動作了動員報告,強調(diào)“要發(fā)揚民主,讓群眾大膽講話,提倡出墻報,批評領(lǐng)導(dǎo),對錯誤觀點不要立刻反駁,也不要加以壓制。”[2]黨的號召很快得到黨內(nèi)外干部群眾響應(yīng),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新黨員反響更大,一場轟轟烈烈的整風(fēng)運動由此展開。
延安知識界、文藝界積極貫徹中央整風(fēng)指示精神,走在整風(fēng)學(xué)習(xí)前列。他們在各種學(xué)習(xí)會上提出批評和意見,不少人還通過墻報、小字報、漫畫、打油詩,或在報刊發(fā)表文章,提出各種批評意見。1942年3月,《解放日報》文藝副利上接連發(fā)表了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等雜文,反映對當(dāng)時延安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問題的不滿和意見,對一些老干部棄舊娶新,官僚化作風(fēng)以及生活待遇等級制,包括衣分“三色”(高級干部深藍色斜紋布、中級干部灰青色平布、基層干部黑色土布)、“食分五等”(小灶、中灶、大灶等),進行了尖銳批評,立刻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強烈反應(yīng)。“王實味是這當(dāng)中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寫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shù)家》(刊3月15日《谷雨》刊物),又連續(xù)在研究院辦的《矢與的》壁報上寫出《我對羅邁同志(李維漢,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坐鎮(zhèn)主持中央研究院整風(fēng)運動)在整風(fēng)檢查動員大會上發(fā)言的批評》、《靈感兩則》,攻擊李維漢等同志,言詞尖銳,冷嘲熱諷,而且有片面性,把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描繪成‘骯臟和黑暗’的封建專制社會,主張文藝家‘首先針對自己和我們營壘進行工作。’一時間把延安都轟動了。”[3]
文藝家們的這些批評,在延安一些領(lǐng)導(dǎo)人中引起很大反感,有人很快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文章,提出批評;還有在內(nèi)部簡報、墻報上予以責(zé)難。“有的領(lǐng)導(dǎo)同志從前方回來發(fā)了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后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lǐng)導(dǎo)干部,攻擊我們的黨。”[4]對此,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他在夜間提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等人在墻報上的批評文章,但并未表態(tài)。當(dāng)時他并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yán)重,也沒有把王實味看做是敵人。他只是讓秘書胡喬木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給后者寫過兩次信。信中有如下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是寫作的技術(shù)。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立場。”[5]這說明毛澤東同志對王實味等人是看重的,所以要其注意提意見的立場和方法,不要走偏方向,頗有愛護之意。4月初,毛澤東同志在所主持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上,談到整風(fēng)中文藝界一些人提出的批評意見時說:“他們的批評意見確實此較過分一些,個別嚴(yán)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系統(tǒng)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6]但仍稱王實味為同志,并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輕易對過分批評者上綱上線,強調(diào)思想“落后分子”不都是反革命,提出要“爭取落后分子”。這再次說明當(dāng)時王實味的問題,仍屬于思想問題。
從4月初至5月底,王實味所在單位中共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展開批評,開大小會70余次,且問題不斷升級。“開始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批評會議持續(xù)到5月下旬時,有人揭發(fā)王實味曾同‘托派分子’有過聯(lián)系,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1929年,王實味在上海從事翻譯工作期間,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過接觸,幫助他們翻譯過《托傳》中的兩章,沒參加‘托派’組織。1940年他在延安已向黨組織作過交代。)這時,康生插手了,他決定徹底追查王實味與‘托匪’的關(guān)系,使問題成為敵我矛盾;并把同王實味接近的四位同志,也一起定為‘五人反黨集團’。”[7]6月11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文藝界對王實味應(yīng)有的態(tài)度及反省》文章,稱“王實味有‘托派’思想”。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批判王實味,并一致形成決議,認(rèn)定王實味在政治上是敵人。
此時,毛澤東同志開始改變對王實味的看法。在6月19日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明確表示贊同文藝界座談會決議的意見,指出:“現(xiàn)在看來,王實味的有系統(tǒng)不是偶然的。這個人多半是有組織的進行托派活動,抓住時機,利用矛盾,進行托派活動,向黨進攻。”[8]10月23日,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作出決定:開除王實味黨籍,認(rèn)定王實味從1929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nèi)的反革命“托派”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正式將王實味逮捕入獄。
1945年,黨對在“整風(fēng)運動”中錯定為政治問題的大多數(shù)同志做了改正,但王實味仍戴著“反革命‘托派’分子”帽子,繼續(xù)關(guān)押在監(jiān)。1946年2月,康生等人再次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jié)論。1947年6月,關(guān)押王實味的山西興縣監(jiān)獄被國民黨飛機炸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對王實味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副部長李克農(nóng)作出批示:將王實味秘密處死。1947年7月1日夜,王實味被秘密殺害,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據(jù)楊尚昆回憶,“處死王實味,事前毛主席不知情。他知道后,拍著桌子向林伯渠同志要人(按:林時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9]
王實味屬于受五四民主和科學(xué)思想影響,滿懷烏托邦社會改造夢想,從而接受馬克思主義,投身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那一代左翼知識分子。1926年,他時年20歲時就在北京大學(xué)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7年,他離開北京到上海,依靠譯著獲取稿酬維持生計;期間,同原北京大學(xué)黨支部里的劉瑩結(jié)婚,先后育有兩女(但長女夭折)。1937年10月,王實味安排妻、女返回劉瑩老家長沙后,只身抵達革命圣地延安,開初在“魯藝”學(xué)習(xí),繼被分配到陜北公學(xué)任第七隊隊長,幾個月后調(diào)出版局,從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翻譯。1938年5月,他被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洛甫(張聞天)指名調(diào)馬列學(xué)院編譯室工作,同年12月調(diào)中央研究院文學(xué)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享受中灶伙食,月津貼四元五角,著中級干部服待遇)。王實味個性傲誕,頗具書生氣,看不慣學(xué)院某些領(lǐng)導(dǎo)的官僚作風(fēng),尤其對陳伯達等諛上壓下種種表現(xiàn)不滿,與之關(guān)系不和。但他對張聞天、王學(xué)文、范文瀾等領(lǐng)導(dǎo)卻十分尊重。1938~1942年,王實味譯出《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雇傭勞動與資本》《價值、價格與利潤》及《列寧全集》18卷中的兩集等馬列主義理論書稿達200萬字。“文革”后,王實味妻女積極為其冤屈申訴;曾在延安工作知情的同志亦通過不同形式、途徑為王實味案的平反積極奔走。直到1992年,王實味在蒙冤50年后,才終于得到中央有關(guān)部門的平反昭雪。
注釋:
[1]《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第814頁、829頁。
[2]轉(zhuǎn)見《新華文學(xué)史料》1982年第2期。
[3][4]見《黨的文獻》,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5]轉(zhuǎn)見《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6]轉(zhuǎn)見《延安—文學(xué)·知識分子和文化》,中華文藝出版社版。
[7][9]見《楊尚昆憶延安整風(fēng)》,香港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8]轉(zhuǎn)見《中共黨史研究》,華夏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四川省作協(xié)(成都)會員、四川公安文協(xié)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