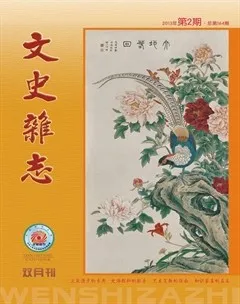雙“九”、對稱與中庸之道
《易經》把“九”定為陽數(陽爻為九),將“六”定為陰數(陰爻為六)。而農歷九月九日,日月并應,兩九相重,故稱為重陽。我認為重九日之所以會成為一個特殊的日子,除開它本身的起源傳說外,這之中還隱含了數千年來中華文化圈內對數字“九”的崇拜。對古代中國人而言,“九”被認為是天數,極具神秘色彩。《易經·乾卦》說:“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其以龍為神物,龍騰而居上,故以“九五”喻帝王,謂“九五之尊”。他如“九天”、“九州”、“九華”、“九服”、“九品”、“九流”、“九鼎”、“九子母”、“九折臂”、“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詞語,無不體現出人們對“九”的偏愛。
“九”是陽之極數,陽極生陰,所以“九”也是變數。《素問》說:“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九。”“九”在其中即為無窮,所以古代數學家“作九五之數以合天道”(《管子·輕重》),所謂“九九歸一”即謂“九九”窮盡而回歸初始狀態“一”;在自然界,則顯示循環往復的運行規律。舊時有《消寒九九圖》,意謂“九九”盡而天氣轉暖,寒意消除。“九”的魅力可想而知。
由“九”為數極可以引出人生之極之意,且“九”又諧音“久”,寓意長長久久,所以重陽節慢慢由最初的祛晦避災演變為祝壽、敬老、祈福的好日子。“九”文化至今還影響頗大,如人們選號碼、日子仍傾向于含有“九”特別是雙“九”的吉祥數;在中式建筑中,像臺階數或紋飾數等等都大量選用“九”的倍數;在文學作品中,與“九”相關的意象也往往有著不可言說的深刻寓意,即如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所引高密東北鄉民歌:“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
雙“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中國人的對稱、平衡哲學。九月九本身就是一個數的對稱,而九月九又與上半年的三月三對稱,古代俗語中說三月三人們應當“踏青”,而九月九人們則當“辭青”。事實上,這類兩兩相應相對的平衡,在傳統社會乃隨時可見,隨處可見。正因為這種對稱理念,人們對單獨的不對稱事物便覺美中不足。我們相比而言更喜歡“好事成雙”、“福祿雙全”等說法,而在房屋內部的擺設上也更主張在家中擺上兩個相對的花瓶而不是一個。
故宮、天壇、天安門廣場等著名的古建筑,若用中軸線從中間將其分開,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兩邊是完全對稱的;甚至在清朝時整個老北京城的布局都是對稱的。這樣的規劃不僅具有美學上的效果,也被眾多的實踐證明是符合城市的規劃與發展的。就連成都在特定范圍上也具有一定的對稱性,而成都的平原地形,使得其有意識地對稱性規劃成為可能。比如從天府廣場的中軸線一線割開,成都這座特大城市就像一個巨型攤餅被分成東西兩部分;沿著人民南路往出城方向也是一線到底,路旁的路燈、綠化建設也較為對稱,使人看后倍感和諧。
像國內外熟知的中國結、瓷器、玉雕、紅燈籠、太極圖案、旗袍等等傳統中國元素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一種和諧對稱的平衡狀態。這種審美上的訴求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人生哲學——“中和”思想的體現。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和”思想不僅在舊時,而且在當下也融通、貫穿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人生觀念、價值取向與審美情趣中。《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的“中”,就是儒家主張的“執兩用中”,是在兩個極端中找到最適合的那個,即不偏不倚、適中;“和”就是和諧、恰到好處。“中”、“和”都有適中、平和等意,后來漸漸形成一個共同的范疇。“中和”思想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內涵。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庸之道于中國人是這樣重要,以至于每一個中國人在行為處事方面都深深地烙上它的印記。大體上看,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是含蓄、內斂的,這與強烈表現個體意志的西方人截然不同。
《禮記·中庸》寫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見古代思想家對“中和”這樣的道德修養論的推崇程度。而“中和”從哲學角度上講,是一種具有辯證思維的、對立統一的方法論,是認識矛盾和解決矛盾時強調適度的原則;并不是過去所解釋的一味折中、不講斗爭的調和主義。這種方法論原則能使紛紜復雜多變的社會維持一種上下浮動的平衡。這種動態的平衡在宏觀上也就是“時中”。《禮記·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這就是說,立身行事,應隨時合乎中道。《論語·學而》則講:“和為貴。”以“和”最可寶貴。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提倡多元共生、和諧穩定。我們正在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的核心價值體系,就包含了“中庸”、“中和”等優秀傳統文化的因子。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2011級對外漢語專業(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