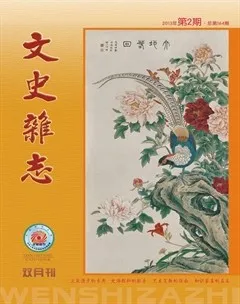但抄不解 何益后生
有學生說起,某些報刊文章里存在只顧抄錄文字,不予必要講解的問題,往往使讀者不知就里,莫名其妙。舉例有2012年5月7日某報所載《曾蘭——揮筆為劍爭女權》中的一段:
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說月報》第六卷第十號,刊出了《孽緣》。作為執民國文壇牛耳的《小說月報》刊登出小說,又加之編輯主任惲鐵樵的這封稱贊信,足以讓曾蘭與《孽緣》進入民國小說史了。吳虞比曾蘭還高興,同一天恰好遇到有人請他作對聯以懸掛于新繁李德裕東湖公園,夜不能寐的吳虞將自己的愉悅之情寫進了對聯:
功業感籌邊,更思文苑儒林,
有叔本公儀,同留勝跡;
窮愁何足志,只合登仙成佛,
繼桃推法進,共寫靈襟。
照作者謝先生所論,吳虞所撰的對聯似與曾蘭的小說《孽緣》受稱贊有關,但讀謝文具體內容卻只字未提,缺少講解;也就是說,文章只有論點,并無論據和論證,生拉活扯往一塊兒湊。
“叔本公儀”和“桃推法進”指的是什么?怎么會與“文苑儒林”和“登仙成佛”聯系到一起?讀了再讀,依然一頭霧水。謝先生抄而未解,實際寫猶未寫,說是不說。
為明真相,還是先研究對聯。
中國楹聯學會常務理事馮修齊先生在《新都楹聯》中曾經評介過吳虞先生這副楹聯:
聯語歌頌了唐代在四川籌邊立下功業、在東湖留下勝跡的李德裕等人,以及新繁歷史上的著名人物。
上聯意為:李德裕的功勛、德業最感人的是謀劃西川的防務;再想到文壇和學術界,還有任叔本、梅公儀等,共同留下東湖這處名勝古跡。
下聯意為:窮困和憂愁不必管它,只希望登仙成佛,跟隨朱桃椎和法進和尚,一起抒發坦蕩的胸襟。
所加注解有“叔本:任末字叔本,蜀都新繁人,教育家,事載《后漢書·儒林傳》。公儀:梅摯字公儀,新繁人,官至龍圖閣學士,《宋史》有傳。”“桃椎:朱桃椎,唐代新繁人,儒林隱士,事載《唐書·隱逸傳》。法進,隋代新繁人,高僧。”
再看吳虞為勉勵桑梓后生,曾著新繁中學(現新都二中)校歌:“任先經苑起儒宗,桃椎法進著高風,勾濤梅摯擅文雄,張惠在元顯世功,費家父子宏道隆,丹山楊氏詩人崇。繁江文雅盛前古,莘莘學士其追蹤,國事艱難匹夫責,同心力學志無窮,豈惟歐美夸俊杰,復興民族期大同。”
這樣我們知道聯意,解開疑團,同時也據此得知謝先生沒有讀懂吳虞之聯,所以無法解說。他甚至沒弄清楚“桃椎”是誰,否則文中引述楹聯也不會把“桃椎”錯寫成“桃推”!
《揮筆為劍爭女權》中還有值得商榷的一段文字:
曾蘭亦為著名的女書法家。她學篆書時,先從師于合州戴光,后來由湘潭王壬秋輔導,專攻繹山刻石、李陽冰城隍廟碑,整整二十年,筆法純正,清勁圓暢,古樸剛健,其造詣深為行家贊賞。時有四川井研書家王麟引用東坡句,為她治印曰“千年筆法留陽冰”。
《女界報》創刊時,主編孫少荊專程登門,請曾蘭賜寫“女界”二字。《家庭》雜志的刊頭也是曾蘭題寫的。南社盟主柳亞子也曾從上海寄來宣紙斗方一幅,請曾蘭題“分湖歸隱圖”五字。南社社員、四川書法家謝無量得其墨寶后,作詩為謝。這讓吳虞也為妻子高興,興味盎然地寫下《讀謝無量謝香祖篆書詩題示香祖》詩,其二為:
篆室千年幾服膺,藤箋遺跡見飛騰。
偶傳玉箸斯冰法,莫被人呼管道升。
首先說“先從師于合州戴光,后來由湘潭王壬秋輔導”,此言失實。證據在《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364頁所載《悼亡妻香祖詩》:
嗟予不善書,弗識臨池趣。
君思補予闕,弄墨兼朝暮。
時時摹鐘王,片楮人傾慕。
合川有戴氏,篆法晚始悟。
教君學斯冰,廿載脫千兔。
融[1]扁擅高明,鄧派驚卻步。
平生玉箸跡,到此空珍護。
他年比蘭亭,入我繁中墓。
謝先生從《吳虞集》生發串聯演義文章,得出王壬秋輔導曾蘭的結論,其失誤在于未曾認真閱讀吳虞原注之:“合州戴子和,業專靈素,篆法鄧石如。湘潭王壬秋嘲之曰:‘戴光學醫太高,學篆太卑。’戴始改學斯冰。”“君初學篆書,予請張星平先生詢戴氏,教以從《繹山》、《城隍廟》二碑入手。近二十年則以《謙卦》為主。井研王圣游為君刊一印,文曰:‘千載筆法留陽冰’。東坡句也。”
王壬秋的確曾經評點過戴子和的篆書,讓戴改學李斯和李陽冰。但王壬秋并未教過曾蘭;指點曾蘭從《繹山》《城隍廟》二碑入手學習篆書的是戴氏。如果王壬秋曾經輔導過曾蘭,吳虞怎會不提此等榮耀之事?
無視吳虞原注,無中生有,斷然臆說,捏造事實,誤導后生,殊不可取。
其次,謝先生引述吳虞《讀謝無量謝香祖篆書詩題示香祖》詩,仍然抄而不解。他只提“陽冰”,而未解釋讀者需要理解的“玉箸”、“斯冰”、“管道升”。
按,《繹山》即《嶧山石碑》,傳李斯所書,古雅妍妙,為后世敬仰。惜此碑毀失已久,現所傳者,為南唐徐鉉臨寫重刻,現存西安碑林。杜甫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碑字筆畫的線條非常挺拔,因嫌偏于肥厚,故世稱“玉箸體”。 《縉云縣城隍廟碑》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陽冰擔任縉云縣令時,于本縣城隍祈雨有應之后篆寫刻石的。
管道升,字仲姬,一字瑤姬,浙江德清茅山人,趙孟頫之妻,封吳興郡夫人,世稱管夫人,是元代著名的女性書法家、畫家、詩詞創作家。
如果謝先生能細讀吳虞原注,并查閱辭書,就會理解“玉箸”是“玉箸體”,“斯、冰”是“李斯、李陽冰”,并能注意解釋“管道升”。這樣更能幫助讀者理解吳詩的深意所在,否則但抄資料,有何補益?
結尾愿引《四友齋叢話》所記:“歐陽公晚年,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畏后塵笑。’”與謝先生共勉。
注釋:
[1]詩中原字結構頗異常,無法打出。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云:“至于字體,……西周后期則筆畫停勻,不露鋒芒,如毛公鼎之長方,散盤之螎扁,此一變也。”據此則該字當作“融”(按“螎”同“融”)。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