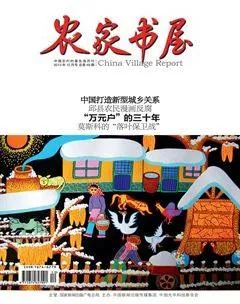中國首度放開承包地和農房抵押融資
11月15日,中國政府網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指出,農民承包地可抵押、擔保,同時農民住房財產權也可先行試點抵押、擔保和轉讓。至此,爭論十余年的農民承包地和農村住房抵押、擔保終有突破性進展。農民最重要的兩塊不動產——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有望進入公開市場交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認為,“改革三十多年來,農村改革重在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權的界定,但在轉讓權方面的改革進展并不順利,更不用說由轉讓派生的抵押權和擔保權。此次《決定》明確放開了承包地的抵押、擔保和農房的抵押和轉讓,是重大突破。”具體而言,主要有三點:
首先,農村住房可抵押、擔保、轉讓。一旦農村住房抵押實現了抵押權,或直接賣掉,這就意味著農民的房屋將轉手。而根據中國現行“地隨房走”的政策,農民的宅基地也將隨之轉讓。也就是說,允許農民住房轉讓或抵押,就變相實現了宅基地的轉讓交易。
此次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其次,集體建設用地可直接入市交易。此次《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當然,《決定》此次也明確,要“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這意味著,中國決策者對土地制度改革已經有了整體部署,并正在按計劃全面推進,下一步將全面修訂《土地管理法》,出臺相關的實施細則。
第三,中國開放了農地承包權抵押、擔保。這將使農民的承包地權利更加完整,同時也更加有利于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有利于推進城鎮化。這等于給8億農民一個選擇的權利,可根據自己的家庭和就業情況,決定是否保留承包地。中國現有超過18億畝耕地,90%以上由8億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承包經營,還有不足10%的耕地歸村組集體和鄉鎮集體經濟組織經營。
“農民享有承包地的抵押權、擔保權,實踐中他是否會抵押、是否會擔保,還取決于農民及其家庭的理性計算。比如是否需要抵押,這種抵押是否會導致失地風險,必然要認真權衡;同時,即使農民愿意抵押,能否抵押還取決于銀行是否愿意接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如此指出。
李力行在近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內部論壇上也指出,“不允許流轉的土地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只有流轉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才能提供高水平的財產保障。若因強調土地的保障功能而限制流轉,就限制了農民的土地財產權,違背市場經濟規律。”
不過,他也強調說,農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和轉讓,首先要“清晰確權”。所謂產權清晰就是要在實測的基礎上確權到戶。但是,現有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記錄,往往與實際地塊的面積和位置不相符。中國政府應盡快建立土地統一登記系統,及時更新;應常設農村產權登記機構,辦理確權登記業務,把提供財產權利登記保障作為基本的政府公共服務,不能靠一次運動解決農民財產權利問題。
其次,要徹底打破政社合一的農村治理體制。目前農村治理主要靠鄉鎮黨委和村級黨支部委員等。作為自治組織的村委會,雖是民選,但決策往往受到上級影響,或變成村黨支部的執行機構,難以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目前,村莊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于村黨支部和村委會,農村承包地的分配和宅基地的批復主要受到這兩個機構的控制。這意味著,農民財產權的分配,需由行政體系決定,農民的財產有可能被剝奪,民主權利缺乏保障,也難以避免其尋租行為。
11月20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財經》年會上表示,農地在直接入市后會明顯增值,但增值部分也不可能都給農民。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必須有一部分用于公用設施或其他方面。
陳錫文進一步表示,在土地利用性質改變后產生的巨大利益,至少要有五個群體得到分配:第一,政府要拿到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從而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使土地產生更高價值;第二,必須保證開發土地的企業有一定投資報酬;第三,大多數市民,因為他們要利用土地生存生活;第四,貢獻土地的農民;第五,遠離城市的農民。
另外,陳錫文表示,近來人們關于土地問題的討論出現了一些偏頗,更多偏向了土地權利人權利的實現,而忽視了對土地的用途管制。
陳錫文稱,三中全會針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三項政策,在整個農地管理中仍是非常細微的部分,仍需大量深入推進。將來在中國農村建立一套完善完整的土地規劃,并按規劃進行農村土地管理,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