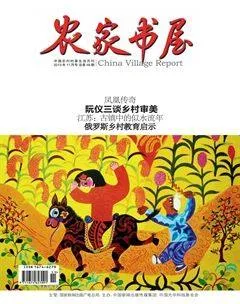鉆天有術唯洞庭



四時果品、油鹽醬醋,古樸的店招,上翻的店鋪門板,這就是江蘇蘇州東山陸巷古村落里的遂高堂,正在恢復重建的明代洞庭商幫(又稱“山上幫”)的店鋪風格。據了解,遂高堂原為明代宰相王鏊胞弟王銓的故居,當年王銓曾在一樓開過店鋪并保留至今。這次修繕除了恢復明代店鋪,還將開設洞庭商幫博物館。
東山鎮陸巷村書記葉慶榮說:“洞庭商幫中有很多經營之道對現代企業和個人生活都有啟發意義,但現在記得洞庭商幫的人不多了。”當年,這個不以蘇州、也不以當初的吳縣為名,而只以洞庭東西山揚名的“山上幫”,揚長避短,闖出一條奇特的成功路徑。
從蘇州地圖上看,洞庭東山是一個伸入太湖的半島,西山則在太湖中。這樣一個風景綺麗的地方,從來不乏浪漫的傳說:相傳2000多年前,“商圣”范蠡助勾踐滅吳后,曾攜西施泛舟太湖,在太湖漁隱;就連金庸也把筆下的曠世才女王語嫣安排在太湖曼陀山莊出生。
因為臨湖,從東山鎮到陸巷古村的K629 公交算是一趟浪漫的班車:藍天白云下,車輛悠悠行駛在盤山的柏油馬路上,窗外就是太湖,山湖之間遍布綠樹,閉眼呼吸,空中彌漫著桂花香……路邊不時閃過一個個小村莊,大約一村一站,直到在一個叫陸巷的太湖漁村下車。
初進陸巷,沒走幾步就見到一家仿古的酒坊,老板鄧帥是本地人。說起洞庭商鋪,鄧帥說:“老一輩人說,以前的店鋪都是前店后坊。”許是訪客多,村民見怪不怪,除了偶遇一家小店門口掛著一塊寫有“本店謝絕照相,沒有為什么”的土黃色紙牌,透露了店主不愿被打擾的情緒以外,多數村民怡然自得。村中有不少農家樂,印著“咸肉菜飯、碧螺春茶”字樣的紅旗在白墻黛瓦中煞是好看。
因現存三十多幢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明清古建,陸巷被稱為“太湖第一古村”。村中筑有六條直通湖畔的巷弄,相傳,陸巷的興盛最早始于南宋,當時大批官員、戰將隨宋南下,途經太湖,便有陸、王、葉、李、姜、張等家族安頓于此,慢慢發展成一座有六條巷子組成的山村,遂名“陸巷”。
陸巷是明朝著名宰相王鏊的出生地。村中至今存有一條長達一里的明代古街,全由兩米多長的花崗石條鋪成,路上豎著“探花”“會元”“解元”三座明代牌樓,據陸巷村人介紹,這是紀念當年王鏊連捷解元、會元、探花而建的。王鏊的世祖在南宋時為太原府千七將軍,到元末明初,朝廷在此推行重稅,迫于生計,當地農民在種地之外,外出經商。
山島外出,全賴水路,風里來,浪里去,“山浪人”走南闖北,乃至漂洋過海,少則數月多則數年。王鏊曾描述:“湖中諸山,以商賈為生,土狹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魏、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
洞庭東西山兩地面積僅各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從地域而言,洞庭商幫是中國十大商幫中最小的。對于這個“長期以來連設縣資格都沒有”的彈丸之地誕生出列于晉商與徽商之間的洞庭商幫,民國期間福建大學者傅衣凌在《明代江蘇洞庭商人》中說,晉商來自整個山西省,徽商來自徽州地區,而洞庭山只是兩個小鄉,卻能與之并駕齊驅,讓人費解。
借著山湖之利,洞庭東西山“遍種果實,既繁且美”。因游客多,陸巷村民葉根在門口賣起盆景,但他的生意可不只盆景一項。葉根在名片上列出了東山土特產:3月到5月,碧螺春茶葉;5月到6月,白玉枇杷和桃子;6月到7月,楊梅、桃子和棗子;9月到10月,白果、板栗和桔子;10月起,太湖清水大閘蟹和桔子。
順著王鏊故居往后山走就是一片桔林,洞庭山是著名的桔子產區,當地的桔子稱“洞庭紅”。據《唐書·地理志》記載,早在唐代洞庭紅柑桔就被稱為“貢桔”,且有“桔非洞庭不甘”之說。在《初刻拍案驚奇》中,凌濛初編著過一個“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的發家故事,說是蘇州有個叫文若虛的破產商人,一次偶然出海經商,因無本錢只好帶了只值一兩多銀子的洞庭紅,不料到了海外竟賣了八百多兩銀子,大發橫財……
在洞庭東西山,水一直是個重要話題。據載,東西山人“以舟楫為藝,出入江湖,動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從地理位置上看,洞庭東山西至無錫69公里,西南至宜興108公里,南到湖州45公里、南潯27公里、長興80公里;洞庭東山,東至吳江25公里,北至胥口25公里。東西山人到經濟發達的蘇松常嘉湖少則半天,多則一兩天。
洞庭商幫所在的太湖流域是棉花和桑樹的主要種植區,煙草、苧麻、靛青、茶樹、豆類等經濟作物相當發達,明清時期“比戶習織”“萬家機聲”的說法反映當地紡織業的發展,加上交通便利,這里一度成為明清時中國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至于商幫為何沒有出現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這和東西山的情況相關。明清時,洞庭東西山人均面積僅1.4畝,適于種植糧食的水田僅為0.5畝,畝產比蘇州平原低很多。這里“山地草蕩居多,耕地極少,約計可稼之田不足五千畝,尚有荒墳桑柴錯離阡陌之中,能產米者僅四千余畝,歲收不過僅可供全山一月之量,余則悉仰外來。”
因水而聚的商業,改變了東西山人的生活。“我們葉家祖上就是在太湖里開船的,我爺爺說過太湖里有湖盜。”葉根的父親、64歲的陸巷村民葉金元說:“我父親從小也跑船,直到他二十幾歲分地以后才棄船。”據葉金元回憶,東山商人常載著楊梅、琵琶、桔子等果子往外運;再載著家具、古董等返回。
在偏遠鄉村,房子成為輝煌時光最忠實的記錄者。“老地主的房子蠻漂亮咯!”抱著茶杯站在院落中的大樹下,葉金元踢了踢一塊偏白色的雕紋石頭說,當年葉家是三進大院,這是門前的石雕,不遠處還有同樣的另一塊。曾有游客開價一萬想買這對石雕,葉金元拒絕了。
指著一旁的老嫗,葉金元說:“這是我伯母,今年90歲了,她年輕時在上海十六鋪碼頭當過挑夫,卸過糧食!”生存需要加上交通便利,使得洞庭東西山人很早有經商習慣。如北宋元豐年間西山人夏元富,明洪武永東年間西山人蔡仲銘,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就連當年鄭和下西洋中也有不少東山人。《林屋民風雜記》轉錄的《五湖漫文》中載有東山人傅永紀于明正德初商游廣東的事例,當時他“泛海被溺,獲附木舟,三日夜流至孤島”,隨后偶遇的漁翁告訴他這是“佛郎機國”,并“以女妻之”。永紀“善為紙竹扇,一扇鬻金錢一文,不二年至于巨富。”
明代昆山的歸有光也說過“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當然,“天下所至”也有前提,那就是在洞庭商人的主要活動區域運河沿線和長江沿線。東山翁氏后人翁澍曾記錄:“東山多大賈,走江、淮間。”康熙時洞庭東山人汪琬說:“西山之人商于湖廣者多。”
從今天東山鎮整理出來的洞庭商人的故事中可見,明清時期洞庭商人的經營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糧食、絲綢、棉花布匹、木材、花木果品、藥材、山地海貨、瓷器、紙張書籍等,但以糧食、布帛及相關行業為主,皆因衣食為生活必需品,量大利厚。目光敏銳的洞庭商人幾乎不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上爭奪市場(目前所知洞庭商人經營鹽業的唯有東山蔣灣葉巷的葉氏),無需官商結合,因而發展偏穩定,這一點被廣贊為“揚長避短穩中求勝”。
同為洞庭商人,兩山商人的活躍區域和經營內容不完全相同。據目前擔任陸巷洞庭博物館設計的民俗家章本義分析,東山商人多通過一條從南向北的大運河,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鎮等為起點,以運河重鎮山東臨清為終點,過江涉淮,北走齊魯大地,中轉后將絲布供應京師,通達邊塞九鎮,主營布匹。而西山商人多以蘇州為起點,通過長江,經湖廣、四川而沿途分銷于閩、粵、秦、晉、滇、黔等地,以南京、漢口、長沙、蕪湖為重要活動場所,主營米糧、綢布。
在“三言”、“二拍”中,馮夢龍和凌濛初以通俗小說形式對洞庭商幫有不少描述和刻畫,其中,馮夢龍最先在《醒世恒言》中的小說《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里提出“鉆天洞庭”,寫道:“話說兩山之人,善于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鉆天洞庭’。”據章本義解讀,“鉆天”是夸贊洞庭商人“腦袋削尖了般聰明,看事物尖銳,本事大到通天。”如王鏊的叔祖王惟貞,“自小歷攬江湖,深諳積蓄之術,江湖豪雄,尊為客師。”王惟貞是公認的理財大師,因為他不僅會做有本錢的買賣,還會做無本的生意。
洞庭商人十分講究經營手段,這些手段看起來也很符合現代經商要求。尤其是及時掌握各種物產的季節、產地、價格、數量及運輸里程和方式,甚至氣候變化、年成豐歉等信息,洞庭商人都是這方面的行家。明清時期蘇州等地人口眾多,春夏之交常缺糧鬧荒,而“地勢饒食,飯稻羹魚”的長沙、漢口,盛產大米,洞庭商人就將大米運到蘇州,“故楓橋米艘日以百數,皆洞庭人也。”又如東山漾橋村的沈萊舟,年輕時曾在上海德記洋行當跑街,后與人合開恒源祥人造絲毛絨號,他以舉辦絨線時裝展覽推廣絨線編結技藝,并贈送絨毛線編結書籍,成功打開銷路。
學會預判為洞庭商人帶來了諸多機會。如東山葉氏,先在開封經營,后“買布入陜,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又如翁氏家族中,翁贊可以“達百貨之情,審參伍之變”,翁啟明“不出戶而知萬貨之情,不杼軸而以東南之女工衣被半海內”。到明中期七世孫毅和其子永福時,父子為商,永福原在北京經營布業,適逢朝廷犒賞軍士需要大量彩綢,便“易布銷綢,一下獲利百倍。”
洞庭商人善于行商,也忠于職守。如翁籩常告誡手下人“不要多求,不要妄取,不要在商品中夾雜窳敗之貨”,往往獲取“一倍以上利潤”。再如東山桔社的金汝鼐,自幼習經書,十幾歲到席家做幫手。他為人忠厚清正,經營中善出奇計,同樣資本、同樣商品,常獲利幾倍于人,為此席本楨讓他節制“諸客行賈”。和其他商人喜歡賣便宜貨不同,金汝鼐“尤求其貴良者”。很多人根據市場波動乘機提價,卻因“曠持日久,積壓變質受損”,金汝鼐采取平價出售,以薄利多銷加快資金周轉。他輔佐席家20多年,進出資金以萬計,但“未嘗取一無名錢”。有人勸他借機自潤,他呵斥道:“人輸腹心于我,而我負之,鬼神亦不饒恕!”
在籌資方面,洞庭商人會根據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采取多種獨特的方式:第一是獨資經營,包括直接經營和委托經營,前者多為中小商人,后者是有資本者雇用職業經理人經營;第二,領本經營,類似借貸資本;第三是合資經營,類似合伙制,如秦氏與蔡氏合作幾代人之久,非常成功。其中,領本經營最值得一提,這種“領本”制是富者出資、窮者出力,按成分紅。據載,席本楨常將資本大量借貸給他人營運,“恒例三七分認,出本者得七分,效力者得三分,賺折同規。”
今天,東西山人仍樂于自稱正因當年“宋室南渡,挾中原文化俱來”,所以兩山之人的經商思路活躍。和其他商幫組織形式類似,洞庭商幫主要是兄弟及親戚聯手式的家族經營,如王惟道、王惟能、王惟貞兄弟,翁參、翁贊兄弟,席氏左源、右源兄弟,而洞庭人“兄弟同居,財不私蓄,一人力而求之,三四昆弟均得析。”
陸巷村民說,王鏊的胞弟王銓就是商人,相傳王銓也曾考取功名,只是身在朝中的王鏊為了避嫌,便力勸王銓轉而經商。據陸巷村委會的朱文敖介紹,陸巷近期正在修繕的古建遂高堂便是王銓故居,當年王銓曾在其一樓開過店鋪并保留至今。原先這里住了三戶人家,因年久失修古建已破舊,陸巷村采用集體收購、村民異地置換方式,購下該古建加以修繕,期望恢復明代店鋪樣貌,并開設洞庭商幫博物館。
今天,東山鎮收集整理了東山明清兩代商賈近千人,有影響的商人達300多人。其中,東山著名的家族有翁、席、葉、嚴四大家;西山著名的家族有秦、徐、馬、鄧、蔣、沈、孫、葉。這些家族多維持數百年以上,或與商人家族之間互相通婚有關。學者范金民在《洞庭商人的經營方式與經營手段》中提出,據他考查翁氏五代108人的婚嫁情況,發現翁氏主要通婚對象就是席氏、葉氏、周氏這三個經商世家。
不只聯姻,洞庭商人同樣注重鄉誼,王惟德在《林屋民風》中寫道:“至鄉人之寓,如至己家,有危必持,有顛必扶,不待親族也。即或平素有隙,遇有事于異鄉,鮮有不援助者。如其不然,群起而非之也。”不僅如此,雍正元年(1723年)西山商人在漢口建了金庭會館,嘉慶四年(1799年)東山商人在南京建的洞庭會館。他們通過會館實現同鄉的互助,這使洞庭商幫許多家族維持了數百年,成為名門望族。
與洞庭商幫經濟地位相提并論的另一個顯著現象則是洞庭商幫家族后代的詩禮傳家。1431年,東山出了第一位狀元施槃;1475年,東山又出了一個探花王鏊,洞庭因此文風大振。說起來,施槃和王鏊都出身經商之家,其中,施槃的父親經商淮揚,王鏊的伯父王公榮在景泰年間“貨殖留毫,積十余年”而“業大起”。
王鏊之后,王家中舉者眾多,著名的有其曾孫王禹聲(1589年進士)、八世孫王士琛(1712年狀元),清末還出了進士王頌蔚、王季烈。明清兩代,東山出過2名狀元、1名探花、2名會元、28名進士;西山出過12名進士,至于舉貢、諸生,則不計其數。
文商融合的洞庭商幫家族延續了耕讀詩禮之家的傳統,從歷史資料來分析,東山進士家屬或本人90%以上經過商,他們始為農家,后外出經商積聚了資金,供子弟讀書,又通過科舉進入上流社會。
今天,這樣的傳奇還在延續:東山近現代獲高級職稱的知識分子達400多人,其中任過博士生導師的教授32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學者42人,這些教授大多在清華、北大、復旦、交大、同濟、南大等大學教書育人。作為“鉆天洞庭”的后代,他們的祖上逾90%都經過商,大多是祖父輩就到上海經商、生養在上海。翁氏后裔翁世榮,現為著名文學藝術家,為原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翁世榮說,翻查東山家譜時,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隨處可見的家訓格言,如“一念之善,吉祥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富時不儉貧時悔,閑時不學用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同樣,在東山席氏一族后裔席時珞的印象中,席家先祖席溫的第27世孫席洙就曾撰寫過一部叫《居家雜儀》的書,提出了重讀書、重經營的觀念——不去科場,即去商場;不能讀書,就去經營。或許正是這些特質,讓洞庭商幫位列中國十大商幫,而又與其他商幫有著本質區別。洞庭商幫不同于其他商幫多從小販、學徒起家,他們有傳統的經營經驗,并有大量資本,所以起點不低。
想來,以一彈丸之地而成著名商幫,終究唯洞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