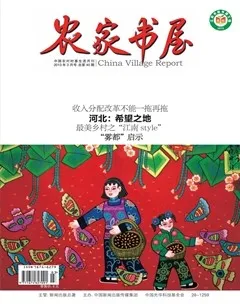廢墟上崛起的幸福鄉村
正值年關,東八里鋪村接連飄了四天雪,從玉田縣城進村的馬路牙子上已經結起了一層薄冰。司機老王是玉田當地人,說到東八里鋪,他便笑著說,你找宋志永吧?隸屬于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縣的東八里鋪本是一個普通村落,2008年初,該村宋志永、曹秀軍、楊國明、楊東、宋志先、王寶忠、尹福等13人因在南方抗擊冰雪災害和四川抗震救災中兩度馳援災區而被媒體贊譽為“唐山十三義士”,這個偏安在冀東的小村隨之一夜成名。
2010年,馮小剛在拍電影《唐山大地震》時找到宋志永,將13人的故事作為電影的一部分搬上了銀幕。如今,時隔多年,十三義士中的王寶國幾個月前因為車禍不幸離世,其余12人中,宋志永在村中開起了合作社,楊國平隨兒子遷至遵化久住,王金龍、王寶忠、楊東在開車跑運輸,楊國明在倒賣蔬菜,宋志先以蓋樓房為生計……
直至今日,曾親歷當時地震的一些人還習慣于在7月27日晚上“守年歲”。對東八里鋪村而言,這場災難同時像一股巨大的外力,加速其步入一條與眾不同的城市化軌道。2008年“唐山十三義士”賑災出名后,當地市、縣不僅把東八里鋪村列為“科學發展示范村”,還為村里修路、裝燈、安太陽能熱水器。被村民選舉為村主任的宋志永,開始創辦一個集養殖、農業觀光、采摘園林、餐飲、住宿、公益敬老院、志愿者服務基地于一體的合作社。
一群人,一個合作社和一個村。東八里鋪的上空,漂浮著蛻變前的躁動和期許。
玉田歷史悠久,春秋時稱“無終國”,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依志怪小說《搜神記》中“陽伯雍麻山種石得玉”的美麗傳說而更名為“玉田縣”,沿用至今已1000多年。八里鋪村因距離玉田的中心點——鐘鼓樓(今天的百貨大廈)正好八里路而得名。
東八里鋪有500多人,耕地總面積886畝,村民主要種植玉白菜、蘿卜、西瓜、甜瓜等,收成好時,一畝地能有兩三千元收入。這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農村,規劃整齊的村道兩旁多為并排整齊而建的平房,門口通常有一片不大的自留地。一大早,49歲的村民曹秀軍穿著黑皮衣,騎著電瓶車開往縣城方向,路過玉田中學時,他放慢了速度,停下車踮著腳,對著路邊圍著頭巾正在賣煎餅的老伴說:“買點肉,中午包餃子吃。”說完便騎車離開了。
下午二姑爺要從廊坊來,曹秀軍琢磨著喊個小工修一修南邊小屋堵塞了的暖炕,自打有一回大閨女睡在南屋被一氧化碳熏昏迷后,這個屋子再也沒燒過煤餅。曹秀軍的平房建于上世紀80年代,和多數村民家一樣,紅磚黑瓦的平房分前后院,左右兩個廂房里擺著兩臺電視機和一臺電腦——東廂房內,曹秀軍的二閨女曹志佳剁好了白菜、肉泥,正拌餃子餡;西廂房內,曹秀軍的母親倚著拐杖坐在炕邊看電視。中間屋子安著一個齊膝高的灶頭;后院有一個安著玻璃門的磚石墻小屋,內飾跟都市公寓的衛生間無異;院中用鐵鏈拴著一條狼狗,當地村民說,好狗看三家。
從曹秀軍家往東走三五米,就到了宋志先家。宋的農房建于2000年,外觀較新,且是二層樓,外墻貼著白色瓷磚,屋頂還安著太陽能熱水器。平時,宋志先以種玉米、麥子、紅薯等為主,冬季農閑他就找些蓋樓房的活。宋志先的兒子以開挖掘機為生,兒媳在醫院當護士,一雙女兒均在縣城商店當營業員。宋志先說:“像我家這樣的條件在村里算中等水平。”
1976年7月27日晚,16歲的宋志先在睡夢中聽到父親大吼一聲“地震啦,快跑”,還沒反應過來怎么回事兒,宋志先就聽見一陣“嘩啦啦”、“轟隆隆”的響聲,“就跟火車開過來的聲音差不多”,接著屋頂掉了一大塊泥。宋志先穿著褲衩,光著上身赤著腳,擰開房門就沖到了院子里。天微微亮時,東八里鋪來了不少人,“很多人都是光著膀子,一步一步從唐山市區走來的。”
此后幾天,宋志先見到有直升機在村莊上空盤旋,丟下一袋袋衣服、餅干等救援物資。慢慢地,村莊的空地上建起了藍色簡易棚,還有住不下的,就到村民家里借助幾天。隨后的五六天里,心驚膽顫的宋志先在床頭倒立了一個空的玻璃酒瓶,“地一晃,玻璃瓶就會倒下來”,惟恐余震。直到1979年去錦州當兵,宋志先還堅持每周寫信回家,“最怕有地震,當了3年兵,寫了3年信”。
住房,是大地震后唐山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八里鋪村的房子多為泥坯平房,誰家的房子要是有青磚外墻算是相當不錯的了。然而,這樣的泥坯平房抗震性卻很強。大地震后,東八里鋪多數農房雖然不是屋頂塌了,就是墻角裂了,其中以房屋后檐坍塌居多,但完全坍圮的不多。1995年宋志永結婚,還住在父親1975年花960塊錢造的泥地面的平房里,“買了兩桶油漆,在墻面齊膝高的位置刷一層綠色油漆,很后來才把地面重新整整,換成水磨石。”宋志永說:“那就是在石灰里拌一點麻繩頭造的房子,但土坯墻本身并不容易裂。”
那一陣,更多的唐山人在廢墟中撿起整磚、木材等,加上外地支援的油氈等建筑材料,蓋起了一座座簡易房,整個城市進入了“簡易城市”階段。當時唐山有個順口溜——“登上鳳凰山,放眼望唐山,遍地簡易房,磚頭壓油氈”。直到1985年左右,東八里鋪農房才慢慢出現紅磚墻。有些住房保留至今,只作簡單的翻新,卻較少推倒重建。只是,村中始終鮮有二層樓房,據曹秀軍形容:“撐多了也就十來個。”
曹秀軍排行老五,但因在三兄弟中最小,人稱老三。“以前的日子,太苦。”說了這么一句,曹秀軍的母親突然哽咽。今年81歲的曹母,生育了三子三女,如今輪流在兒子家養老,一年一換。事實上,她共生育了7個孩子,有一個孩子活到一歲多餓死了。村中常有另一個老太找曹母聊天說起當年的日子有多難捱,曹母常回答一句:“易不易,都得生活啊。”
1963年,曹秀軍出生時,口糧雖然緊缺,勉強能糊口。曹秀軍的童年是在河套或田地里抓著泥鰍、蝦子、蛤蟆、螞蚱度過的,他樂滋滋地說:“有一種蛤蟆顏色偏黃,皮特別亮,那是有毒的,得抓泥土色的蛤蟆才能吃。”
談起兒時印象最深的開心事,曹秀軍的眼中亮出一道光,回味說:“我11歲那年,村中的河套里還有水,不像現在這么干,有一回逢著發大水,我哥把褲腿扎起來,就這么空手逮著一條十五六斤重的鯰魚。”
到了十六七歲,曹秀軍在八里鋪生產隊跟車、裝車,收麥子,看水泵等,到了暑假就給生產隊割草。有一回,隊長趙富和(音)安排大家拆舊屋,起瓦片,由于著急將活干完,趙隊長“誘惑”大伙說:“要是太陽下山前能拆完,晚上就吃烙油餅。”在那個餐餐皆是玉米餅的年代,烙油餅簡直就是一頓大餐。拼著一股勁,大伙兒愣是提前忙活完了。一撇腦袋,曹秀軍“嘖”了一聲,說:“那烙油餅,忒(太)好吃!”曹秀軍記憶中的這個烙油餅,跟宋志永心中的一份菜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農村幾個要好的哥兒湊一起,打點兒高度的散酒,炒幾個雞蛋,拌點白菜心,弄點花生米,醬豆腐、韭菜花、白菜炒豬血、尖椒辣肺絲……”如今天天下館子,宋志永搖搖頭,說:“找不回那個味道了。”
2008年,跟著宋志永前往湖南賑災的12人多數沒有出過遠門。曹秀軍說:“我就想去溜達溜達,這一不小心溜達大了。”王寶忠說:“過年一直都是在家,出門活動活動筋骨也好。”——這正是唐山人的幽默。當然,東八里鋪的年輕人還是以在外工作、生活的居多。曹秀軍的女兒曹志佳就曾在北京通州住過一年半載,她是一名汽車保險的電話銷售員。
早些年,東八里鋪的村民也很少離開村莊。“有人要出去,那簡直就是新鮮事。”想離開村子的人不僅得經過生產隊批準、簽字,而且得按一個工分4毛錢計補交錢。曹秀軍隱約記得,1982年時只有3個人離開村莊外出當建筑師了,“留在村里的人每個月才掙10塊、20塊,出去的都掙大錢了。”
曹秀軍曾經也算得上一枚“潮男”。上學時,他就養兔子掙零花錢,最多時養了100多只。放學后,他帶著一筐兔子到縣醫院前門口的街上趕集,“最小的兔子兩只賣一塊三毛錢,大兔子有5斤、7斤的,4毛錢一斤。”忙活了一年半,曹秀軍攢了百來塊錢,他果斷花了120塊錢買了一塊上海全鋼手表。曹秀軍20歲時,村中慢慢有人開始穿西裝了。“對服裝特別稀罕”的曹秀軍跟著潮流,買了一套六七十塊錢的西服,又搭配買了一雙九十多塊錢的三節頭皮鞋。只是,穿了一陣后,曹秀軍就不那么愛穿西裝了,“領口有點冷”。
1982年,八里鋪生產隊散隊后,曹秀軍開了一個面粉廠,兩臺機器開工,掙點加工費。“用一個黑兜子裝錢,一分、兩分、五分、五毛,幾天就能裝滿兜。”盡管掙得多,曹秀軍只干了一年多就不干了,因為一個人忙不過來,累得慌。“到后來,我見到鹽都想咳嗽。”
當時,生產隊有一個21吋的黑白電視機,擱在面粉廠由曹秀軍管理,這是全村第一臺電視機。曹秀軍就盼著天黑,“天黑了就有人來看電視,可以陪我說話,幫忙看看機器,搬搬重袋。”那一陣,大家最愛看電視劇《霍元甲》,曹秀軍也不例外,他尤其喜歡劇中人物陳真穿著一套中山裝的帥氣模樣,還跑到縣城花了七八十塊錢買了一套類似的中山裝。
如今回到家,曹秀軍依然喜歡照照鏡子,看看發型。他還隨身帶把小梳子,得空梳幾下。就連曹志佳也笑著說:“我爸可講究了。”指著老照片上一個穿著深藍色背帶褲的小姑娘,曹秀軍哈哈一笑說:“這是我大女兒曹志松兩歲時的照片,這條褲子就是我親手做的。”
東八里鋪村的西側有一條長街道,曾名“無終街”。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就是一條熱鬧的街道,“道挺寬,車挺多”。正如其名,此道往西可以通北京,往東北可以通遼寧。1989年后,無終街重新修整,從東八里鋪村穿過,后改名為102國道東八里鋪段。今天,東八里鋪村的道路規劃工整,地面是水泥路,路邊澆注了水泥臺垃圾箱。然而,在過去漫長的時日中,村莊道路一直是泥土路,晴天,路上塵土飛揚;雨天,路上泥濘不堪。
宋志先對村中道路的變化最有體會。1982年,當兵3年的宋志先回村后,看到村中造房的人家多,便湊了900塊錢,找人合伙花2000元買了一臺拖拉機,靠拉砂石料、磚頭掙錢。這是一輛老式的、帶大轉輪的拖拉機,發動起來非常響,噪音特別大。每當拖拉機噼里啪啦的聲音傳來時,村里的孩子們都會跑出去觀看,拖拉機開到哪里,他們就追到哪里。
當時,村中其他人每個月不過掙三四十塊錢,宋志先開拖拉機跑一趟掙六七塊錢,刨去一毛錢一斤的柴油錢,一個月下來也有1000多塊錢盈余。賺錢后,宋志先花一兩千塊錢造了一個新屋,準備結婚。結婚那年,宋志先給女方家的禮金是300元,買了一臺錄音機100多元,一塊手表100多元,還有一臺縫紉機約四五百元……
1985年,宋志先把舊的拖拉機折價賣了1000多元,轉手花5000多元買了一臺“北京12馬力”的四輪拖拉機。說到四輪拖拉機,東八里鋪村還流傳著這樣一首打油詩:“遠看像吉普,近看蓋缸土,開車的一身油,坐車的一身土。”村中路況之差,可見一斑。
宋志先買四輪拖拉機的這一年,東八里鋪村剛開始修整道路。說起修路一事,曹秀軍笑著說:“我其實記不得哪一年修路了,就是剛有游本昌演的《濟公》(1985版)的那一年!”這一年,村莊的男人們扛著鐵鍬,齊心協力開始在泥土路上鋪上一層碎石子,“先是粗石子,再是細石子,最細的在最上面。”曹秀軍隱約記得有一次全村人聚在一起,鎮長在臺上告訴大家說:“村莊的自來水由水利局管,村里的公路由交通局管,電路更改由電力局管,綠化由林業局管……”
東八里鋪村雖小,但村民卻非常講究規矩。用宋志永的話說就是,什么都能變化,唯獨對“好與壞的是非判斷不能變。”曹秀軍六七歲時,村中有一戶趙姓人家,家丁興旺。許是因為家中人多,趙家老太太特別講究行事規矩。有一回,趙家小兒子對長輩說話無禮,趙老太手持荊棘條將其堵在屋中準備教訓,不料小兒子推開門窗跳了出去。老太氣鼓鼓地喊:“要不挨我這頓訓,你就甭回來了。”沒想到,小兒不僅沒再回來,還入伍當兵去了東北。幾年后,小兒行將結婚,老太一人獨行至東北,一上炕,見到兒子顧自抽煙不給自己遞煙,老太一聲不吭轉頭回了玉田。
和曹秀軍“抹著泥巴”、玩著當地一種名為“娃娃堵”的游戲長大的王寶忠出生于1965年,去年他剛買了一輛小車,在家門口跑運輸,每個月有兩三千元收入。王寶忠的印象里,10歲以前,沒少挨父親的批評,說:“我一淘氣,我爸就提溜著一個燒火棍追著打我。”
在東八里鋪村,再靦腆的男人,對著淘氣的孩子都會“兇神惡煞”起來。宋志永的父親是鐵路職工,常年在天津工作,通常一個半月回家一次。宋志永十六七歲時,常跟著朋友出村打牌。有一回朋友開車來接宋志永,不巧被宋的父親碰見。宋父掄起一塊石頭,怒道:“你不下車,我就把車砸了。”看到宋志永不以為意,宋父二話不說,砸了車玻璃。父親這一砸讓宋志永掏了不少修車費,更成為一個警鐘,烙在他的心中。正如2008年賑災的舉動,在宋志永看來,那本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是非判斷。
最近幾天,曹秀軍一直在東八里鋪村的養老院值班。正值年前,多數老人已經被接回家中過年。即便如此,這個高峰時期多達100多人的院中仍留有10多位老人。其實,這個占地約200畝的養老院正是“宋志永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項目之一。
2008年賑災無意間出名后,“唐山十三義士”為村莊帶來了大變化:當地市、縣不僅把東八里鋪村列為“科學發展示范村”,還先后投資300多萬元,完成村莊道路硬化3500米,綠化工程1500株,在主要街道安裝太陽能路燈10盞,家家戶戶全部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并直接帶動了114戶旱廁改造,有幾十戶安裝了秸稈氣化爐,十幾戶修建了沼氣池。在新的一輪選舉中,村民也選舉宋志永擔任村主任。
2009年11月,“宋志永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唐山市玉田縣東八里鋪村正式開業,其理事會成員就是抗震抗雪災的13位農民兄弟。根據宋志永的初步計劃,該社定位是:一個集養殖、農業觀光、采摘園林、餐飲、住宿、公益敬老院、志愿者服務基地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農業產業機構。據了解,該合作社的注冊資金是960萬元,現有土地約200畝,建筑面積15000多平方米。其中,資金絕大多數是宋志永個人籌集,其他成員主要是采取“土地入股”。理事會成員之一楊國明說,他家就有幾畝地被合作社占用了,每畝地每年約有1000元租金。
目前,該合作社的萬頭養豬場、苗木區等已初具規模。村頭的養豬場旁邊用鐵柵欄圍了一個“母豬活動鍛煉區”。宋志永解釋說,和傳統養豬注重防疫不同,這是提高免疫力法。“我們還計劃給豬舍裝上小喇叭,進食時放點輕音樂,白天放點歡快的,讓豬運動起來,晚上放鋼琴曲,讓豬聽著音樂睡大覺。”
如今,村頭的廢水坑也被投資開發為垂釣場,搭了十幾口供游人烹飪用的大鐵鍋。宋志永說:“我想建立散養雞、垂釣等,通過農家樂讓收入水平偏低的老百姓也能玩得起,還可以解決全村甚至是周邊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除了養豬場,合作社產業園的其他養殖還沒有全面啟動,有活大伙就來做“鐘點工”,沒活就自己外出找活打工。即便如此,產業園也已為東八里鋪村提供了約60個固定就業崗位。
宋志永算了一筆賬,每天喂豬的成本就是4000多元,這還不包括水、電和消毒,以及員工的工資,一年就是100多萬元。采訪中,宋志永沒有詳細說出合作社究竟掙多少錢,但從他笑瞇瞇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對合作社的未來還是相當看好的。關于村中的養老院,除卻對村中孤寡老人免費,其余老人每月支付600元、800元等不同等級的費用,宋志永補充了一句:“目前,養老院基本實現收支平衡。”
事實上,還有更多的合作社成員對于年末分成抱著太多疑惑——這幾乎就是一個問號,誰都不確定合作社是否能掙到大錢,更不確定掙錢以后自己又能分得幾杯羹。采訪中,其中一位社員委婉地說:“多少給了一點錢吧,誰知道賺了大錢后怎么分呢?”也有死心塌地跟著宋志永干活的社員說:“不能怪老宋,你說,那些人都不在忙活的,怎么分錢?”
最近這段時間,宋志永承包了一個1000多畝地的山頭,計劃打造一個高端山區別墅。此外,他還在找一些價格雖貴、口感卻不一樣的水稻種子,琢磨著做點兒什么。“我不想過多解釋,我會盡最大能力把合作社發展成具有帶頭作用的農業品牌,用行動應對質疑。”宋志永淡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