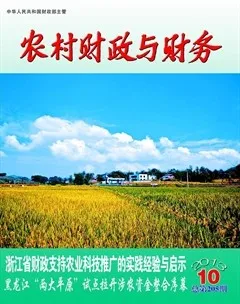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未來經濟發展新動力
一、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遇到阻礙,發達國家對中國需求下降,一些發展中國家還從供給環節替代中國。另外,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的出口產業利潤空間在向零趨近。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產能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加快城鎮化是最好的選擇。同工業化相比,城鎮化創造需求,工業化創造供給。城鎮化可以從投資和消費兩大方面大量產生需求,這為下一步經濟增長提供了空間。因為大規模的人口城鎮化具有巨大的收入增長和消費效應,實踐表明,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能帶來人均國民收入的明顯增長,由此提高了國民購買力。同時,大量農民進城落戶后,他們的消費傾向、消費結構變化也會利于增加工業品的消費。另外,城鎮化還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一國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后推進城鎮化可以增加第三產業的就業和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即使制造業升級也離不開城鎮化,城鎮一般是技術創新和推廣的平臺。當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后,城鎮化是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新發動機,而且也是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階段的一個必然選擇。我們對城鎮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一個模型分析,結果是:一、城鎮化與GDP密切相關。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對GDP是正向作用,相關性很大。二、城鎮化與就業關系密切。城鎮化程度的提高與第三產業的就業是正相關,而且彈性很大,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超過一個點。但是對第二產業的就業關系是負相關,即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是負增長。
二、我國城鎮化面臨的三個矛盾
我國工業化長期快于城鎮化,是國內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中國現在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城鎮化慢于工業化。世界上有三個類型的工業化與城鎮化關系。(一)工業化與城鎮化同步的國家,發達國家一般是這樣。(二)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的國家,像中國就是典型。(三)城鎮化超前于工業化的國家,比如拉美國家。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化長期超過城鎮化的國家,這種國家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內需不足。中國政府集中的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過于強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政府有這么大的聚財能力,當她從工業化獲取巨大財力后沒有及時轉向城鎮化方面,沒有為城鄉居民提供充分平等的公共服務,由此形成政府錢多,農民、邊緣人群和落后地區公共服務極差,這是由體制和發展模式造成的。用世界視角看,中國人均GDP水平處于中上等收入國家,但產業結構和城鎮化都是中低收入國家水平。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達不到70%以上很難邁入高收入國家。鄧小平說過到本世紀中前期我國經濟發展要達到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習近平總書記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的時候,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偉大復興的核心是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是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都是在75%以上,沒有75%是不可能的。美國大概80%多,英國90%多,日本、韓國也都在75%的水平。要想實現中國夢,城市化率達不到70%是不行的。對擴大內需而言,城鎮化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必須讓大規模的農業人口市民化,才能有效地拉動國內需求。不然的話,中國的需求結構永遠是投資拉動。城鎮化不但可以擴大內需,同時還能為培養壯大中產階層創造制度條件。中產階層一般大都集中在城市,沒有城市的人口集聚,中產階層擴大是不可能的。像非洲一樣,都生活在原始部落,沒有中產階層。像中國這樣的中上等收入國家,中產階層人口只占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幾,比重太低了,遠不足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第一個矛盾。
第二個矛盾是城鎮化與農民工市民化的矛盾。中國當前城市化水平是52.6%,即使是這樣的數據還有兩個部分是虛化的。(一)城市郊區被市民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通過城市大規模擴張,把城市郊區全部變成市民,把地收歸國有,但是郊區的農民沒有完全城鎮化。他們的戶籍可能是城鎮,但是他們的消費結構、生活方式仍然是農民。(二)大量的農民工被城鎮化。他們人進了城市,由于二元體制障礙,并沒有真正過上城市生活。所以減掉這兩塊以后,中國的城市化人口不到40%。中國要從不足40%城鎮化率上升達到70%以上水平,路還遙遠。中國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農民工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無法獲得市民身份,在公共服務許多領域是二等公民,原有城市居民是一等公民,造成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根源是二元城鄉制度。從表面上看,這種二元制度是割裂了城里人和農民工之間的階層結構,這種階層結構不流動,它是一種固化的狀態。這種狀態導致的結果是,看似這個國家是一個垂直一體化的威權國家,但實際她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分化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對立的,因此不利于社會進步和穩定。另一方面,人口城鎮化快于土地空間的城鎮化。比如說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面積從1.3萬平方公里擴大到5.3萬平方公里,增加3.1倍。同期城鎮人口從3億增加到6.9億,僅僅擴大了1.1倍。城鎮用地的增長彈性系數達到2.8,而國際公認的標準是1.12。在現有體制下出現這種情況的核心原因是各級政府誰都想在現有體制下分享要素流動帶來的紅利,但誰都不想承擔農民工轉移進城的成本。農民沒有遷徙自由的同時失去發展資本,所以不可能真正城鎮化。在二元體制條件下,農民的自由是有限的。農民工進城后看到城里人,他會覺得自己是劣等人。當農民看不到有改變身份的希望時,社會正在積累不穩定的泡沫。一個征地,一個拆遷,一個突發事件有可能會引發一個群體事件。第一,他們不信任政府。第二,他們既羨慕又嫉妒這些比他們優越的人,當他們無望改變身份時,最后就造成社會不穩定。近幾年群體性事件的爆發與征地、拆遷、農民工維權都有關系。
第三個矛盾是城鎮化與城市管理制度的矛盾。中國的城鎮化按照行政級別而言是一種縱向行政層級管理體制,有直轄市,有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鄉級鎮。這種層級管理帶來的結果是以大管小。越是級別高的城市權力越大,官員級別也高,大管小,高壓低,小城市必須為大中城市分割公共資源,把好的公共資源集中向上。導致越大的城市發展越好,越大的城市機會越多,越大的城市公共服務能力越強。這樣帶來的結果是用行政力量發展城鎮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口集聚,大城市過于膨脹,不得已又用行政管理辦法來限制人口進城,所以積重難返。因此,想用市場力量來引導人口進城就進入了死胡同。另外,這種行政體制下城市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行政分割。大城市吸取好的要素,對中小城市形成一種虹吸效應。誰都想搶好資源和好產業,誰都不想干那些出力不討好的爛事,最后城市之間是互相孤立的,競爭多,聯盟少。
三、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思路
傳統的城鎮化是重物輕人、城鄉分割,高污染、高排放、粗放型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應該是四句話,一是以人為本,把人放在第一位。二是理性發展,不是狂熱非理性的。三是城鄉一體,就是城鎮化的成果能及時輻射、滲透到農村,帶動農村發展。四是綠色低碳集約型,包括四個:資源集約、空間集約、產業集約、人口集約。現在中國的城鎮化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全國無論什么級別的城市,它們的城市廣場在世界上是最大的,政府的辦公樓是最好的,飛機場是最豪華的,這是因為政府的公共資源沒有科學合理配置。新時期中國城鎮化的總體思路應該是:(一)要協調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關系,不能讓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過多地向工業化傾斜,應該協調兩者的關系。就目前來說,應該調集一些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利向城鎮發展,用于城鎮化,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雙輪驅動。(二)要在制度上推進農民自由遷徙,從制度上“漂白”農民。不應該把農民當成中國的二等公民。憑什么城里人的公共福利就高于農民,看病、養老、就業、住房等公共福利都比農民好,需要從社會進步思考這個問題,這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四、新型城鎮化改革的框架
(一)以城鎮行政體制改革為核心,加快推進體制改革。一是減少行政層次;二是優化城鎮區劃;三是調整大中小城市的權責關系;四是創新城市群治理模式。(二)以城鄉二元制度改革為核心。一是戶籍制度改革,一定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總體思路應該是城鄉一體化,城鄉在戶籍上最終是沒有區別的。但是要注意,要采取漸進式、分層化推進。二是推動土地改革市場化,土地天然是農民的。要按照市場化交易,不是簡單將土地國有化。目前的征地制度實際上是利用政府的公共權力將農民的地強制變為國有土地,給農民的補償價比較低。下一步應該是市場化,不應該搞國有化,這種國有化是一種掠奪或者剝奪農民的方式,是不利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三)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路、水、電、氣、網在大中小城鎮和農村間應該是一樣的。(四)要建立覆蓋城鄉的均等化公共服務體系。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但現在誰也不愿意覆蓋所有常住人口,因為每覆蓋一個外來人口,省會城市大概要10萬元以上,特別是對副省級城市而言一般大約15萬元左右,這還不算一些硬件設施。因此,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地方的分擔機制。(五)要啟動“城市群共同體”的公共資源配置工程,北京跟周邊的9個城市,上海跟周邊的15個城市,珠三角周邊的幾個城市在公共資源配置上應該是一體化的,要聯盟發展,無縫銜接。(六)要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政策自治體系。過去我們太偏愛大城市,下一步能不能給中小城鎮一個偏愛,在公共資源、公共權力上向他們多一些傾斜。(七)在城鎮化推進中要嚴防掠地建城,投資擴張。現在很多地方一聽說要大力發展城鎮化,就開始占地、搞廣場、建大樓。這絕不是新型城鎮化所倡導的,應圍繞常住人口進行公共資源配置,以人為目標而不是借助城市化大搞投資建設,大肆掠奪農民的土地。
在現有的體制下,誰都在侵蝕傳統體制下的殘余紅利,傳統體制的紅利會很快吃完。但是傳統體制下積累的矛盾比如說農民工戶籍、農民工社會保障、農民工住房、農民工培訓及子女教育等等農民工的生存發展權問題誰也不愿意解決。各級地方政府都在侵蝕既有制度紅利的背景,是中央沒有一個很好的科學頂層設計。比如說下一步能不能在社會保障方面搞一個中央和地方的分擔機制,戶籍制度改革列個時間表,大中小城市間財權事權關系改革策劃一個行動方案等。當前中國已經到了加快改革的轉折點,三十年的改革紅利已經基本被掏空。當前推進城鎮化的核心是防止城鄉居民階層分化、固化,從制度上打通城鄉人群階層流動通道,推進城鄉二元結構一體化,為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創造制度條件。
(作者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
郭慶旺:馬院長全方位的、深入淺出的、系統的關于新型城鎮化與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發言,我很受啟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特別是最近改革開放以來更高的經濟增長,其背后的動力需要我們重新思考。過去的動力能量已經釋放殆盡,未來三十年中國繼續保證較高速度的增長靠什么?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馬院長對工業化和城鎮化關系的論述非常好。工業化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是什么關系?一個是創造供給,一個是創造需求,我覺得這個定位非常的精準。講到兩者關系的時候,馬院長講到了新型城鎮化的“新”,提出了四大標準,這既符合中國的國情,也符合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聽完他的講演,給我一些遐想的空間。他提到了中國工業化的速度超過了城鎮化的速度,我按照他這個思路繼續聯想一下,到底這兩者之間有沒有個先后順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尤其是對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而言工業化的速度超越了城鎮化的速度有沒有它客觀的歷史的必然性?
城鎮化引起了新一屆政府的特別關注,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就在思考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到底應該有多快?城鎮化的發展有沒有一個時間點?比如我們五十年實現一定水平的城鎮化,到一百年以后再達到什么水平?有沒有一個時間段的問題?因為整個社會都在討論城鎮化,似乎是只爭朝夕,時不我待,沒有給出一個時間段的問題。而且大家研究的問題非常深入,有的好像是四十年以后才能遇到的事。如果按照最近中國設想的城鎮化,我覺得15年之后中國就沒有村了,這符合不符合規律?這是一個問題。另外,社會到底有沒有分層?我有一個粗淺的看法:如果人類社會沒有社會分層,那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但是可能不是人類的實際生存狀態。只要有人類就肯定有分層,但是層與層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從哪個角度出現的分層?這又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過去咱們提過中國新農村建設,最近不怎么提了。問題在于在中國的城鎮化過程當中,是先解決農村的問題呢,還是直指現代化城鎮的發展問題?這也值得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