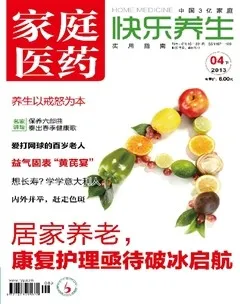中醫處方傳奇③:《本草綱目》藥方故事(3)
李時珍于采藥、品藥、研究藥理藥性的同時,還特別看重食療在中醫臨床治療中的效果,力主從百姓日常的膳食果蔬當中,合理調配,平衡陰陽,達到養生健身的目的。
發現“小人參”
據明《蘄春縣志》載,為了研究中草藥的藥理和藥性,李時珍常常只身一人,身背藥簍到深山去采藥。一日,天近中午時分,李時珍來到一處懸崖絕壁旁,遠見對面山崖上有位銀發老翁正攀懸于絕壁上采藥。但見老翁鶴發童顏,氣色紅潤,手腳利落,令李時珍十分驚嘆。
李時珍趕緊趨前攀談,得知這位老翁是隱居在這深山里的老隱士,雖已年過百歲,卻眼不花,耳不聾,身板硬朗,思維敏捷,且非常健談。問及老翁有何養身延壽之道時,老翁淡淡一笑道:山野之人,淡食為道……隨手指了指背簍里同草藥夾雜在一起的胡蘿卜說:“喏,就是常常吃這個。”
老翁的一席話給了李時珍很大的啟示,回到家中后他反復琢磨,品味胡蘿卜的藥理和藥效。他認為:胡蘿卜屬中性食物,于陽虛者,可扶陽;于陰虛者,可滋陰,實為菜蔬之王、養生佳品……經常食用胡蘿卜對于人的健康非常有益,對調理人的心臟疾病尤為有效。于是,李時珍就把這一食療方法介紹給更多的人。時至今日,在湖北蘄春一帶民間仍然盛行長年食用胡蘿卜的食俗。當地人視胡蘿卜為食中補品,譽稱為“小人參”,成為每餐必食的養生佳蔬。
據調查考證,在蘄春一帶,百歲以上的老壽星在萬人中的占有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且中老年人群中體內血中的膽固醇含量以及心血管疾病和腫瘤的發病率,亦低于全國其他地區,胡蘿卜功不可沒。
檳榔傳情
李時珍不僅醫術精湛,而且頗有文才。
有一年,李時珍外出尋訪名師,在湘潭生活了5個月。期間,李時珍的夫人曾經給他寫了一封別致的中藥情書:“檳榔一去,已過半夏,豈不當歸耶?誰使君子,效寄生草纏繞他枝,令故園芍藥花無主矣。妾仰觀天南星,下視忍冬藤,盼不見白芷書,茹不盡黃連苦!古詩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結雨中愁。’奈何!奈何!”
在這封情書中,檳榔、半夏、當歸、使君子、寄生草、芍藥、天南星、忍冬藤、白芷、黃連、豆蔻、丁香都是中藥。李時珍的夫人采用了連綴寫法,把中藥的名字串聯起來,表達了自己對夫君的思念之情。
李時珍看了夫人的情書,感慨萬千,心中也油然生起對夫人的思念之情,他立刻回信寫道:“紅娘子一別,桂枝香已凋謝矣!幾思菊花茂盛,欲歸紫菀。奈常山路遠,滑石難行,姑待從容耳!卿勿使急性子,罵我曰蒼耳子。明春紅花開時,吾與馬勃、杜仲結伴返鄉,至時有金相贈也。”
李時珍的情書中寫的紅娘子、桂枝、菊花、紫菀、常山、滑石、從容(肉蓯蓉)、急性子、蒼耳子、紅花、馬勃、杜仲也是中藥。李時珍的回信寫得文辭纖巧,語意纏綿,傾吐了夫妻間純真深切的相思之情。
李時珍和夫人的兩封情書巧用了24味中藥名串聯成篇,毫不牽強,妙趣天成,讀來情趣無限。有趣的是,夫人信中以檳榔代指賓郎、郎君,李時珍以“紅娘子”這種中藥喻指“妻子”,信手拈來,都非常別致。李時珍對檳榔的醫療功能概括為“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饑能使之飽”。據《本草綱目》記載,檳榔性溫,味苦,可解油、驅蟲、除脹,還可治水腫腳氣等癥。適當嚼食,有利于面部神經的運動,可起到美容的功效。檳榔既是藥物又是一種果品,特別是在湘潭人的生活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湘潭人在待客時可以不用煙,不用茶,只要奉上一口檳榔,就足以表示主人的熱情和誠意了。
山楂治水腫
《山楂·發明》中講述了李時珍研究中藥羊朹(音球)子治水腫病的故事。
李時珍的鄰居,有個七八歲的小孩,平時面色黃腫,挺著一個大肚子,但能吃、能玩,大人也沒把孩子的病當回事。
一年秋天,李時珍發現孩子的氣色比原來好多了,大肚子也消失了,整天蹦蹦跳跳,活潑可愛。他很奇怪,便向孩子的母親詢問原因。孩子母親告訴他,前些時,孩子到他小姑家去玩,見后山有棵樹上長滿果子,就爬上去吃了個夠,回來后吐了好多痰水。從此以后,孩子的病就慢慢好了。
那是一棵什么樹,結的什么果?李時珍尋思著。第二天,他就找孩子帶他去看看。
孩子帶著李時珍來到他小姑家的后山,在山坡上有一棵一丈多高的樹。李時珍定睛一看:這不是山里人稱為茅楂或猴楂的山楂樹嗎?
他向山里打柴的樵夫打聽,才知道這種樹和矮小的茅楂,都是山楂的一種。茅楂結的果實,山里人叫棠朹子,酸甜可口,藥店里收購。而這種樹結的果實叫羊朹子,果實稍大,味道也差不多,而藥店里不收購。孩子在誤食大量羊朹子后,把食積水腫病治好了,這證明不被藥店收購的羊朹子與棠朹子有同樣的療效。
李時珍對這一發現非常高興。在《本草綱目》里,他對兩種山楂作了詳細的比較和解釋,得到結論說:“羊朹乃山楂同類,其功應相同矣。”
甘蔗方
中醫認為,甘蔗味甘性寒,入肺、胃經,有清熱潤燥,生津止渴,解毒透疹之功,適用于陰虛肺燥所致的咳嗽,胃陰不足所致的嘔吐,熱病傷陰所致的口渴、發熱,酒后煩渴及痘疹疹出不暢等。《本草綱目》言:“蔗,脾之果,其漿甘寒,能瀉火熱,消渴解酒。”
李時珍發現甘蔗的妙用,是從一部《野史》中看到的故事而悟出的。說古時有盧絳中其人,“病痁疾”,“忽夢白衣婦人云:食蔗可愈。及旦,買蔗數挺食之,翌日疾愈。”李時珍根據這一情節,從藥物學上加以研究,斷定:“蔗,脾之果也。其漿甘寒,能瀉火熱。”
李時珍沒有被這個故事的神秘外衣所迷惑,也沒有因其荒誕而一笑了之,忽視其合理內容。他用自己的藥物學知識和醫療實踐經驗,對其包含的合理內容予以了準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