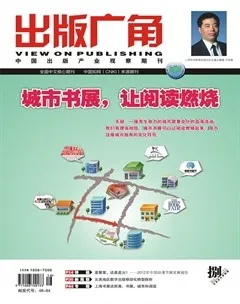上海書展近距離:書展、城市和閱讀
在泛娛樂化和信息爆炸的今天,一個人如果只是單純地希望消磨時光、獲取信息,有太多手段和方式可以滿足,而當一個讀者走進書展打開一本書、坐下來傾聽一場講座,無疑是懷著陶冶自我、提升自我的真誠愿望,再加上整個城市的文化環境和人文素養,最終促成這樣一場熱烈的文化盛典。
上海書展像極了上海這座城市。既海納百川,又堅持文化品格和品質;既一脈相承,又不斷突破自我,推陳出新;既名家薈萃、大雅齊集,又百姓節日、傾城同歡。每年八月,熱切的讀者冒著炎炎酷暑,在上海展覽中心門口排成長龍,購票入場,只為一年一度與心儀作者、作品重逢或相遇,這是多么讓人感動的畫面。在泛娛樂化和信息爆炸的今天,一個人如果只是單純地希望消磨時光、獲取信息,有太多手段和方式可以滿足,而當一個讀者走進書展打開一本書、坐下來傾聽一場講座,無疑是懷著陶冶自我、提升自我的真誠愿望,再加上整個城市的文化環境和人文素養,最終促成這樣一場熱烈的文化盛典。
2013上海書展十周年,參展出版社超過500家,各項文化活動超過600場,到場海內外知名嘉賓超過900人,多年打造的上海國際文學周、書香中國閱讀論壇、學術出版上海論壇等文化品牌獲得業界廣泛認可,“我愛讀書,我愛生活”日漸深入人心。書展十年,浸透著行業最優秀人才的智慧和心血,一路走來,邁過荊棘坎途,終見朗日榮光。雖然作為上海書展的親歷者,談起書展有太多話可說,但本文無意為上海書展作總結,而是希望從一個讀者的角度,淺談網絡化、信息化環境下為什么需要書展,需要什么樣的書展,以及幾點自己的思考,求教于前輩和同行。
一、今天為什么需要書展
書展究其形式,無非是物質產品的集中展示和銷售。當年上海書城籌建,口號就是“永不落幕的書展”。然而,隨著電商和網絡快速發展,規模已經無法為書展帶來稀缺性。上海書展受場地所限,能夠容納的品種數在15萬種左右,而當當的SKU(Stock Keeping Unit,最小庫存單位)超過百萬,其中紙質圖書約70萬種,電子書約5萬種;京東、亞馬遜的SKU還要多于這個數量。從價格角度比較,上海書展提供全場八折的優惠,不僅無法和電商瘋狂競賽的活動價、血拼價相提并論,也不及一般時段電商的平均折扣促銷力度。然而,上海書展卻并未門庭冷落,反而持續激發市民參與熱情。2013年書展期間全部開放夜場,周末更將開放時間延長到晚10點,展館內仍然人潮如織,價格較高的出版物如定價近千元的《新版十萬個為什么》日銷超過500套,書展結束前,大量單品種圖書售罄脫銷。那么,究竟是什么讓上海書展如此火暴,或者說,在高度信息化網絡化的今天,市民為什么還需要書展?
從讀者的角度看,上海書展的成功類似于iPhone——提供最佳用戶體驗。具體來說,儀式感、信息有效到達和精確投送、互動體驗和文化認同,構成了書展相對于電商的稀缺性,成為書展的競爭力核心。
首先是儀式感和現場感。較短的排隊購票時間和較低的票價設立了一個門檻,成功把真正關心閱讀、熱愛閱讀的人群篩選出來,讀者通過長長的、帶有清涼噴霧的遮陽篷,步入具有鮮明蘇聯建筑風格、巍峨雄壯的上海展覽中心,在高高的穹頂下置身漫漫書海和讀者潮中,所有書籍隨手可取、隨卷可閱,從視覺、感覺和心理上同時帶來強烈震動,自然觸發讀者正面情緒和感受。許多老讀者把到上海書展的感受描述為“過節”,這從購票到入場的一段路,正是節日特有的儀式感。
其次是信息的有效到達和精確投送。雖然電商網站SKU以百萬計,但受到屏幕分辨率和人類的視覺雙重制約。人類沒有昆蟲那樣精密的復眼,只能同時觀察有限事物;一個網頁的展示容量有限,通常一個屏幕內主要呈現的商品在12件左右,一個網頁能呈現的商品在100種以內,而一個0.75米書架的上架圖書品種數在48種左右,一個平方米展臺的展示圖書品種在26種左右,讀者在一個展位內停留兩三分鐘時間,數百種圖書涌入眼底,開本、紙張、色澤、質感一目了然,再花30秒鐘取下中意的圖書,看作者、看書前書后的推薦語、略翻一下內容,就能大致決定是否購買。行業內“報賣一個題,書賣一張皮”的俗語,準確描述了從信息投遞到作出購買的“快速通道”。這就形成了一種有趣的現象:由于購書是典型的或然購買行為,大多數讀者并不像逛超市一樣對要買的商品有清晰精確的預見,而是一個搜尋到發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書展反而對以網頁展示為主要銷售手段(移動設備展示方面局限性更大)的電商形成信息優勢。再輔以合適的信息傳導,比如作者簽名、編者講座,甚至只是工作人員的幾句推薦,都能讓讀者迅速得到有效指引。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有效指引對大多數專業并非文化行業的讀者來說尤為重要,根據《上海市民閱讀狀況調查(2013)》,有約21.5%的受訪者認為“缺少讀書氛圍”或“不知道該讀什么”是影響閱讀的主要原因,而書展上信息密集、有效、精確投送則完全解決了以上問題。
最后是作者、讀者直接互動帶來的愉快體驗,折射出深度文化認同的強烈需求。上海書展海內外名人、嘉賓超過900人,既有年輕人熱捧的演藝界明星,也有陳佳洱、歐陽自遠、周忠和這樣的兩院院士、大科學家,既有兒童文學新秀,也有賈平凹、蘇童、阿城這樣的文學大師。和自己所崇拜的作家見面、傾聽他們的講座、得到他們的簽名合影,無疑能讓“粉絲”興奮激動;當“韓粉”排在“一個”簽售會的長長隊伍中,當知青坐在梁曉聲講座的同齡人群里,談論共同的話題、尋找共同記憶,得到的顯然遠比一本書、一個故事要多得多,這是深度文化認同需求的滿足,是BBS、SNS等線上讀書小組所不能取代的。
二、明天書展會怎樣
上海書展物理空間有限、時間有限,在已經把“書”和“文化活動”做到近乎完美的基礎上,討論需要什么樣的書展,其實仍然無法繞開網絡化、信息化的時代背景。在《新聞周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這樣名報刊都放棄出版紙質版的今天,很難想象,書展會在未來繼續成為印刷品的盛宴和狂歡。我想,書展要繼續發展、繼續突破自我極限,應當突出“科技”“人”和“多元化”三個因素。
“科技”應當是今后書展乃至書業的首要關鍵詞。即使筆者這樣的深度紙質產品愛好者,也不得不承認數字閱讀的確優勢眾多。Amazon創始人貝佐斯(Jeffrey Bezos)2.5億美元買下《華盛頓郵報》以后,關于紙質報紙的命運又掀起新一輪口水。其實,報業將死已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專業媒體、專業出版的命運如何?互聯網普及和新媒體興起,挑戰的并非傳統新聞出版業如何轉型,也不是如何運用新技術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正常社會對專業新聞、優質內容有永恒的需求,不正常的社會更加如此。有需求就有市場,專業人士終將創造出商業可持續的內容生產模式。真正的挑戰來源于競爭圖景的改變,首先是區域壟斷被打破,書業開始全國競爭;然后是世界范圍的優質內容資源爭奪;互聯網興起,意味著專業人士以外的人也加入競爭,并且迅速成長為新的專業人士(比如已經成為文學新門類的網絡文學),網絡賦予了每一個人生產內容并傳播的權力。這帶來了最根本的挑戰,每一個出版人都應當反思并且重建出版專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全體專業人士競爭,和全體非專業人士競爭,只有第一流競爭者能夠生存,平庸就會消亡。作為書業的集中反映,書展理應體現數字閱讀、數字出版的發展,尤其是出版人重塑自身競爭力的探索和實踐。出版人尤其不能為紙質出版物的熱銷而陶醉,據說龐然大物如恐龍,踩到水桶那么大的東西,要幾個小時感覺才能傳導到大腦。我想,我們不應當作恐龍。
出版業并非關于書的行業,而是關于人的行業。書展要真正成為“百姓節日”,就應當更加重視“人”的因素,尤其是更加重視普通市民的因素。書展上人情味越濃、普通人的故事越多,就越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可。2012年起,上海書展全體工作人員送別最后一位讀者,并頒發榮譽證書和紀念品,就是一個很有創意的舉措;同樣2012年,譯文出版社一名工作人員在書展現場向女友求婚,獲得現場觀眾動情祝福,兩人五年前在書展相識、相戀,終成眷屬,成為當年書展的一大感人場景。出版人比較容易陷入單向傳播的思維,即我掌握知識,想辦法傳授給別人,而不太容易主動尋求雙向傳播的局面。書展要能夠真正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成為市民生活和記憶的一部分,就應當讓市民的聲音表達出來、讓市民的故事講述出來,要提供和創造一些這樣的渠道、措施、平臺,讓書展不只是文化的傳播授予,更是個人生活的坐標、成長的印記。
中國近代出版肇始于國家危亡、民族危難之際,出版人以啟蒙民眾、救國救民為己任,這種基于理想的出版理念和美國基于職業的出版理念形成鮮明對比。老一代出版人如張元濟、王云五、陳原,不但是大出版家,也是大學問家;而瑟夫、西蒙、舒斯特幾位美國出版家,則大多是富家公子。中國出版發展到現在,大部分出版人仍然秉持高尚的出版理想,對學術出版、專業出版更加看重,對一般大眾出版則相對不那么重視。易中天先生曾表示,“讀書無用”,即讀書是為了提升自我,不是學手藝、學掙錢,不是為了現學現用。這樣的觀點當然有道理,但一方面實用類圖書的的確確效用昭彰,對一個初為人父的讀者來說,《育兒指南》要比《資治通鑒》重要得多;對一個家有寵物的讀者來說,《寵物飼養》比任何其他書籍都緊要迫切;另一方面,能夠看得懂專業著作、學術著作不僅需要讀者有相當欣賞水平,更需要有較好的家庭和教育基礎——也就是需要一些好運氣。于是,一位讀者如果讀不了《四書章句集注》而讀于丹女士的《論語心得》,仍然不失為了解傳統文化的敲門磚。更何況,一些專業作品和學術作品粗制濫造,對社會的益處遠不及一本《電工手冊》。書展活動中,群眾活動、普及活動數量不少,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支持,出于多元化、提升市民素質的需要,應當更多安排、更加重視一般群眾活動和普及類的活動,眼光向上,姿態向下。
三、兩點其他的思考
本次上海書展創設實景版書店展區,曉風書屋、季風書園、鐘書閣、大眾書局等民營書店都實景展示了自己店面的情況。站在實景書店區域,讀者人潮洶洶,季風書園中幾無落腳處,這和筆者幾天前在季風華師大、上海圖書館兩個店看到的情景大相徑庭。季風華師大店由華東師大免費提供場地和水電費用,但由于門可羅雀,仍然虧損經營;新遷址后的上海圖書館店也不樂觀,除了下班客流高峰期,晚上8點后讀者也屈指可數。近年來,隨著物業價格上漲和人工、運費等成本上升,實體書店經營出現困難,上海率先出臺扶持實體書店配套政策,從資金、政策上對專精特、中小微實體書店進行扶持,但實體書店自身經營狀況如何,仍然是決定書店生死存亡的核心要素。書展推出WIFI覆蓋、導讀導購、快遞寄存、書香有禮、手機充電、餐飲便利等方便讀者的舉措,深受讀者好評和歡迎。比如前文提到的《新版十萬個為什么》,碼洋高達1000元,重量超過30斤,超過一般讀者體力所及。如果沒有免費快遞服務,很難想象其會成為熱銷品種。書展推出的種種服務舉措,有多少實體書店能夠借鑒,有多少能夠進一步深化,成為實體書店吸引讀者、改善經營的手段,值得認真思索。
另外,如何調動參展商積極性,也值得深入思考。上海書展展位免費提供,出版社無需支付場租費用,可謂已經十分優惠。但是,畢竟七天全夜場的高強度工作需要工作人員來維護、服務,一些工作人員因勞累而精神懈怠,甚至轉化為不滿。應該看到,書展倡導閱讀氛圍、引領閱讀風氣、培養閱讀習慣,對全行業、全社會而言都是好事,為什么還會有不滿意呢?那是因為,工作人員的工作不能直接體現為收益,參展商的努力沒有直接體現為業績。物不平則鳴。如何讓工作人員、參展商的工作體現出來呢?這涉及國有企業考核、績效評估和資產管理的問題。出版雖然是文化領域中改革最早、改革推進最快的領域,但和經濟領域改革相比,資產關系、人員關系仍顯僵化。通過改革和轉制,市場開始在一些領域的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生產力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解放;但是,舊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資產運作模式仍然大量存在,出版單位的經營自主權并未逐步放大,反而逆勢縮小,市場信號被嚴重扭曲。反映到工作中,工作人員對各項工作缺乏熱情和積極性,出版單位對轉型突破、創新發展缺乏勇氣和自主權,越來越成為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體制障礙。如何突破這些制度障礙、迎來新聞出版業生產力的更大解放,創造出更多、更優質的內容產品,值得全行業共同思索。
(作者單位:上海新聞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