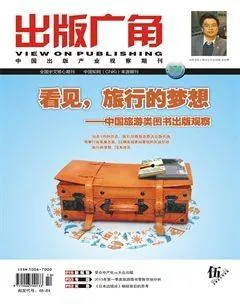一個大教授的小文章
有的人是為制造財富而活的,有的人是為了權力而活的,有的人是為了表現自己而活的。而我,活著就是為了寫這些字,通過這些字來表達我的想法。
我寫歷史文化隨筆,起于20世紀末。那時候剛落腳北京,一文不名,也百無聊賴。以前在黑龍江的時候,就喜歡《讀書》雜志,于是就試著給它投稿,沒想到居然被采用了。于是一發不可收拾,越寫越多。漸漸地,別的雜志也來約稿,稿費也逐漸高了起來。反正平時沒事總要看書,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喜歡把這段史料抄下來,再寫上幾句話。現在寫隨筆,無非是把過去的讀書筆記擴展開來,弄規整一點。
后來,有人建議我把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歸攏起來出書,還真有人要,于是出書。小時候讀魯迅全集,看到魯迅一本本的集子,無非平時的報刊文章歸堆,現在自己也可以這樣,心里很得意。這時候,有書商對我說,你小子有可炒作的潛質,我們炒炒你吧,大家掙錢。我說算了,你們一炒,是福是禍我心里沒底,反正書也能賣,就這樣湊合著吧。但是,輪到這本《歷史的壞脾氣》了,正好那年香港中文大學聘我去教半年的書,人不在北京,出書的人自作主張,就炒了起來。其實,這本隨筆集原來不叫這個名字,書名是書商的編輯起的,若干媒體一炒,就熱了。熱到一塌糊涂,我才知道,只好隨他去了。
打那以后,七八年過去了,我寫的東西越來越多,在許多地方開專欄,各大門戶網站都有我的博客(多數是人家復制的),微博也開了,有點大事小事,就會有媒體來采訪。原來立志做書齋學者的我,變成了一個非常熱鬧的人。我也才發現,原來我這么能寫,寫得這么快,有的時候,半個小時就可以出篇時評。
有的時候,也有點困惑,有點找不到北的感覺:我到底是干嗎的呢?當然,更多的時候,我還是在看書。凡事想不通的時候,就不想了,這是我避世的法門。我沒那么淵博,肚子里的貨有限,不看書,就寫不出來。這么多年寫下來,不寫已經沒法過日子了,不僅手癢,而且心癢。小時候的志向,就是賣文為生,現在已經實現了。即使沒有了學校教書的收入,我也能活。雖說現在的中國,知識產權大有問題,網絡到處都是你的文字,收入卻沒有。印成鉛字,剛賣出點名堂,盜版就上來了。而且國家對稿費征的稅又高得嚇人,稿費稍微高點,一刀砍下來,四分之一沒了。但是,只要你產量足夠高,換飯吃還是不成問題。
不過,這么些年寫下來,你說要是純粹為了稻粱謀,倒也未必。因為這期間,我也拒絕過一些報酬優厚的活兒。不想寫的東西,給多少錢也不寫。寫出來,無非是想借此表達我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想法。對與錯,是與非,無從論計,但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有的人是為制造財富而活的,有的人是為了權力而活的,有的人是為了表現自己而活的。而我,活著就是為了寫這些字,通過這些字來表達我的想法。這年頭,字寫多了肯定是會有名的,招人讀,也招人罵。熱鬧到這個份兒上,硬說自己淡泊名利,騙人也不是這個騙法。我當然要名,但我在乎自己的名,名就是我的羽毛,多光鮮談不上,但卻不想讓它們變得污濁。在網上,我有敢言之名,但有的事、有的時候,也不是什么話都敢說。但我不能說的時候就沉默,絕不說違心的話。做學問如此,寫隨筆如此,寫時評或者將來寫小說,都是如此。
我寫我思,實實在在。一旦違心,寫作也就沒有了意義。寫字可以賣錢,但不賣靈魂。陳寅恪先生說,人不能靠學問掙錢,要掙錢,可以做生意。我相信,如果老先生當年經商,也未必不能發財。但是,老先生一輩子養家糊口,還就是靠自己的學問。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命運,走到哪兒,人家都只認你的學問、你的文字。時運好的時候,你可以保持你的傲骨,同時也能拿到那份養家糊口的錢;時運不濟,如果還要保持你的傲骨,可能命也沒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一天,時運不濟,連今天這種艱難學文的機會也沒了。到了那個時候,我還能不能堅守自己的信念?會不會因為一口飯而放下自己高傲的身段?但愿中國不會回到那個風雨如磐的過去,真要是退回去了,我想,我肯定不會茍活于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