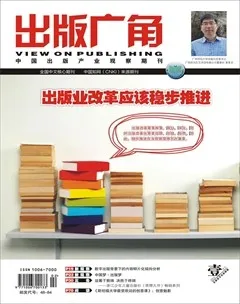出版業改革應該穩步推進
出版改革需要探索、前行、深化,同時出版改革也需要回顧、總結、反思,因此,穩步推進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出版業隨著改革的大潮已經走過30多個年頭,出版社啟動轉企改制也已經10年了,至今,形式上的轉企改制工作已經完成。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業的改革目標將如何設定,改革的思路將如何確定,改革的步子將如何制定,是擺在我們出版人和管理出版的人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發展的標準是什么,繁榮的標志是什么,這更是值得我們出版人去觀察、去思考、去探求的問題。筆者以為,中國出版業的改革應該穩步推進,我們應該去回顧、反思已經走過的歷程,去總結、去分析獲得的成功與不成功的經驗或教訓,去審視、去探求目前的現狀乃至于存在的問題。在13年前,筆者也是在《出版廣角》(2000年第四期)上這樣說過:“世紀之交,回眸已經逐漸遠去的20世紀,我們圖書出版界應該看到些什么,應該去想些什么,任何學科研討注重的只能是問題。津津樂道于過去的繁榮(且不談這種繁榮的程度如何)是沒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過去,問題卻關系著明天,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那么問題是什么?問題在哪里?首先,應根據對現狀的分析,歸納問題的所在,問題的實質,爾后才是追根求源去探究問題的根子所在。”在解釋我的專著《出版問道十五年》(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如此命名的緣由時,我這樣說過:“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對中國出版業問題的思考上,因為我以為能夠正視自己的問題才是充滿信心的表現,因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問題才有了解決問題的前提,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從提出和針砭的問題,可以看出我對中國出版業的某些癥結在進行著持續的思考探索,有的問題直至今天還是我們討論的話題,到今天還在影響著中國出版業的發展進程。因此,‘問道’,問中國出版業的‘道’是本集子也是筆者15年孜孜以求的。”由此,筆者還將繼續“問道”,問出版之“道”,或許這個音符有些不和諧,但是我仍然堅定地認為,這是必要的、必須的,尤其在當下!
回顧之一:集團化與不均衡戰略
由于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支配和影響下,我國出版業已形成了一種獨特模式,即布局上的分散性、分工上的雷同性、發展上的均衡性,從而影響了出版資源的優化配置,分割了圖書市場,分散了出版業的力量,制約了我國出版業的快速發展,直接削弱了我國出版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實力。所以,出版業改革初期就提出了“不均衡發展”戰略。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地方保護和區域利益的特征,在出版業改革逐步深入的過程中,各省市在組建集團、建立中盤、連鎖經營等一系列改革舉措面前使盡渾身解數,力保自己的地盤不失,于是這些改革舉措都在原來意義上被曲解了。當時理論界針對這樣的現象曾經進行過頗為深入的討論,筆者就曾在2002年對這樣的現象提出了明確的質疑和批評,認為這樣建設起來的集團基本上是以地區為界,以系統為界,以國有為唯一,形成一個封閉的圈子,對內是聯合加上保護,對外是競爭暗藏排斥,其最終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貿易壁壘,有悖組建集團的初衷。至2012年全國共組建37家出版集團,27家發行集團。目前雖已有集團開始跨地域的兼并重組,然而始終未能打破全國性的均衡發展態勢。
中國出版業在戰略布局上的當務之急就是組建幾個真正意義上的跨地域的“航空母艦”,它應該是幾個,而不是一批。同時,我們在組建集團、打造航空母艦的同時,也應該注意中小型出版社的發展,因為中國出版業的發展、圖書市場的繁榮離不開眾多的中小型出版社。出版業隊伍,需要“航空母艦”,同時,“小舢板”“沖鋒舟”同樣也需要,只有這樣組成的出版隊伍才是完整的。這是“不均衡發展”戰略在另一個層面上的意義詮釋。
回顧之二:上市熱與主業的發展
中國出版業在改革進程中又一條“風景線”就是上市熱,已有為數可觀的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用各種形式上市成功,還有相當的一部分出版企業正躍躍欲試,積極籌備上市。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49家新聞出版類企業上市成功。根據目前中國出版業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規律,資本市場的運作主要體現在兩大領域,一個是打造數字化平臺,延伸出版產業鏈,一個是企業兼并重組,這兩大領域都需要大量的資本。前者通過產業鏈的升級換代,把大量的內容資源整合在一起,從而實現數據庫出版,同時通過新的轉換方式和載體形式實現產業鏈的轉換。當然數字化平臺的投入從起步到盈利是需要時間的,對此,我們的決策者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心理準備。后者是出于企業擴張和本領域內多元化發展戰略,需要打造相關的產業鏈,因此通過兼并或者重組的形式,重制新的產業鏈(問題是在中國的行政區劃制背景下,大的未必能吃掉小的,強的未必能兼并弱的)。至于投資重大文化工程,在目前來看,一者是不需要那么大的投資,二者這個應該是政府層面上的職責,而且這樣的文化工程在資本市場的運作中也是不具有實際意義的。
問題的關鍵在于上市募集來的資金如何運作,如何投資,如何回報股民?而這一切均需建立在發展主業的基礎上,否則就失去了作為出版傳媒企業存在的意義。環顧已經上市的中國出版業,似乎還沒有發現哪一家上市以后運用募集來的資金投入主業的發展而且取得明顯實效的。倒是屢見用于投資政績工程,干起了房地產乃至于投資基金等副業的報道,這種違背當初上市發展主業初衷的現象是否應該值得我們反思?
回顧之三:轉企改制與市場主體
轉企改制,牌子更換,可這并不等于改制工作就大功告成了,后改制時代的改革道路還長,在出版改革為了什么,應該改什么,應該怎樣來改等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上我們還必須補課。我們必須讓全體出版人達成共識,那就是希望通過轉變體制,改革機制,增強活力,提升競爭力,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通過改革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創新之路,惟其如此,出版業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做大做強。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看到了轉企改制工作的真正實效。
然而同樣讓人有遺憾之感的是,改制后的出版企業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現代企業制度、產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還任重而道遠。而在新一輪意義上卻出現了“企業單位性質,事業化運作”的怪事,在行政級別、干部任命、企業分配制度、企業用人機制中無不繼續體現著行政權力的意志。因此,只有建立起由公司所有權、公司監理權、公司治理權和公司經營權四種權利要素構成的科學的權利體系,現代企業制度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得到完善。這正是在后改制時代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市場主體地位的問題在眾多的高校出版社表現得更為明顯,學術出版、學科建設與經濟效益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相當多的出版社眼下已經陷入了既非企業又非事業的尷尬境地,這又讓我不禁重提作為有著明確辦社宗旨的大學出版社是否有必要統統走企業化道路的話題。
回顧之四:精品出版與文化品位
在出版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似乎忽視了一個不應該忽視的問題,這就是出版人作為文化傳承的使者對文化品位的追求。對文化品位的忽視直接導致了我們出版物整體質量的下滑。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出版界的許多積弊產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擯棄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說是因為文化人本性丟失這個問題上?
出版實踐告訴我們,一本好書,一本符合人們生活、生產、工作、精神需求的圖書,無論是有社會效益,還是有經濟效益,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必須具有文化品位。沒有文化品位的弘揚主旋律的圖書一定是空洞的說教,一定是沒有新意、沒有創新的出版物;沒有文化品位的卻能獲得經濟效益的圖書,一定是庸俗的、低級的、嘩眾取寵的出版物。文化品位是出版物和出版業效益核心價值的體現,這應該是一個不爭的評判標準。
所謂“文化品位”,一定包括了內容的創新性、價值的積極性、形式的健康性三個方面,所謂文化品位的高低,一定就是在這三個方面的程度的高低。自主創新,是出版物的靈魂,原創是出版物文化品位衡量標準的重要內涵; 而社會價值的積極性,則是文化品位評判標準的基礎條件,那種低俗的文化垃圾、庸俗的迎合之作,是沒有“品位”之說的;形式的健康性是文化品位的外在標志,我們的出版物應該是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精神食糧,而不是跟風出版、機械模仿的應景之作,不是嘩眾取寵、庸俗作秀的低俗之作,也不是空洞說教、重復出版的文化垃圾。
出精品,出傳世之作,是我們出版人的責任,是我們的追求。我們應該記住,出版社是靠書立社的,靠名編輯立社的;編輯是以書立身的;我們的出版業是以書來傳世的。我們的前輩已經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張元濟、葉紹鈞、鄒韜奮……他們無一不是這樣去做的。 我們每個出版人都應該為之作出努力。
回顧之五:數字出版與實事求是
我們應該重視新技術給我們出版業帶來的深遠影響。在許多領域,數字出版正在蠶食我們傳統出版的份額,這是不爭的事實,在出版的許多領域,數字出版或許將成為主導地位,也許會是一種顛覆性的革命,這也是完全可能的。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從甲骨文到竹簡書帛,從刻印到造紙印刷術的發明,每一種新技術的發明都給人類文明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伴隨新技術新媒介而來的數字化出版同樣將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里程碑式的意義。但是,即便這樣,在今天,我們也沒有必要任意夸大數字出版將對我們產生的影響。
2011年公布的數字出版份額達到1377.88億元。可多事的我,馬上發現數據里的奧秘,其中手機“出版”為367.34億元(手機音樂282億、手機閱讀45.74億——注意:相當大部分的是給移動的網絡費、手機游戲39.60億);網絡游戲428.5億元;數字期刊9.34億元;電子書16.50億元(注意:賣的載體應該占絕大部分);數字報紙(網絡版)12億元;網絡廣告512.9億元;網絡動漫3.5億元;在線音樂3.8億元;博客24億元。真正的出版又占幾何?2012 的數字應該會更加好看,但是真正的“出版”估計又幾乎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數字。
對于數字出版,我們應該以正確務實的態度去對待,以一種正確的心態去看待、分析數字出版將對我國出版業帶來的深遠影響,任何漠視和夸大數字出版的影響都是沒有意義的。傳統出版會完全被數字出版所取代嗎?那只是數字技術商們制造的童話。新技術確實給我們出版業帶來了深遠影響,筆者這個年齡的人也感受到了新技術的來勢洶洶,也感受到了新技術運用的愉悅,電腦寫作的便利、存儲信息的海量、博客微博的迅捷、iPad與微信的便利。但是,即便這樣,在今天,我們也沒有必要任意夸大數字出版對我們產生的影響。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也認為“新的出版業態還缺少足夠強大的內容提供能力”,“傳統出版依然是出版的主流”,“仍然有發展的空間”,“可以進一步發展壯大”。更何況,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或者說是摸索出一個完整有效、系統可行的數字出版的贏利模式,這需要時日,需要我們全行業的共同努力,需要我們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去探索創新,人云亦云、一窩蜂地創造政績的心態是無濟于事的,因為這是科學,是高科技。實事求是應該是我們目前面對數字出版必須具備的正確心態。
出版改革需要探索、前行、深化,同時出版改革也需要回顧、總結、反思,因此,穩步推進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