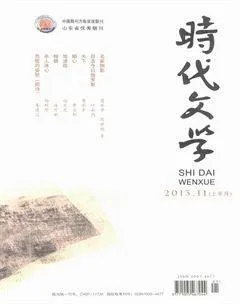美女盲流·神仙裸泳
春末的時候,去上海。葛水平說她從北京過去,在上海機場等我的廈門航班。我出了機場,就看到機場通道的外鐵護欄上,倚靠著一個女人,她一腳搭在護欄底線上,手提一個雜志大小的塑料袋,悠閑得像剛得了手的盲流。好像有點打眼,再一看,天!這美女盲流就是等我的葛水平!我說,行李呢?她晃了晃塑料袋。全部在這?她說是。她就這樣從北京飛到上海,就這樣,提著小塑料袋等我的飛機下來,去完成一個三天的聚會。
超然物外如此,魏晉風度都不及她率性天成,一個女人啊。塑料袋里面就是幾件換洗衣物,好像還有甜角之類的零嘴。她特別能吃,根本不在乎身材什么的,這個,有空再表揚。我們就這樣入住那個五星賓館。沒有十八般武藝的衣服,也沒有繽紛炫目的化妝品,一支小破口紅,在她想鄭重一點的時刻,就抹兩把以示不輕慢。葛水平美麗,天然、淡定、溫潤的美麗,因此她對外面的修飾粉刷幾乎不留心。這份骨灰級的超然,和老天的偏愛有關。她也有很不超然的時候,這個,我們基本上是當笑話,一有機會就熱情幫她溫習一遍。
那是冬天的故事。那個冬天,我們去了九寨溝。冰天雪地的,除了我們這一撥,基本沒有游客。吃喝玩樂之余,店家推舉他們山上的露天游泳池,說是可以加溫。冰天雪地呀,在九寨溝露天冬泳!想一想我們都覺得自己是神仙。為了讓我們自己完全進入神仙角色,一車人就開始討論裸泳。不知是哪個起意的,大家都興致高漲,熱烈附議。在九寨溝冰天雪地里裸泳,不是神仙是什么?一車人飛流直下三千尺胡扯九萬里。誰也沒有注意到葛水平沒有聲音。游泳活動的安排不在當日,但一車人遐想胡扯完,照吃照玩照睡,沒有人知道,葛水平憂慮重重得幾乎整夜失眠,次日眼看臨近游泳項目了,葛水平小心翼翼地問一個面善的,低聲說,喂,真的要裸泳啊。那人一看葛水平凝重的表情,噴飯。葛水平很不自在,頑強地說,那我不去。那面善的笑得不行,說,嗐,嗐!你以為真的呀!葛水平點頭,說,怎么不真啊,那山某、彌某、童某,宇某、瓜某,一看就是裸泳的人嘛。后來,那冰天雪地之夜,一車人按游泳界的常規,著裝整齊地下了水,包括葛水平。見我們個個人模狗樣,葛水平這才徹底釋然。我們沒有裸泳,她不懂,所有人都心有靈犀,知道游泳要穿泳衣,只有像神仙的葛水平,以為大家會赤誠相見。回想起來,我們大約真辜負了那個千山鳥飛盡、萬徑人蹤滅的神仙時空,那個本該最有神仙氣的葛水平,估計一下水,她天賦的魏晉風度就會被再度喚醒。
葛水平是端莊美麗的,而且正氣沛然。那天有個著名評論家,在為一個濫性男作家辯護。葛水平勃然動了真氣,呸,那個流氓!小丑!換是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她的詩意氤氳的小說,字縫間升騰起來的就是這種英武之氣。這也是葛水平迷人之處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