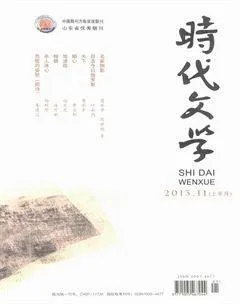我游臺灣(組詩)
夜降桃園
BR761航班 從濟南起飛
選一條夜的航線
貼著大陸 沿著夢的邊境
午夜 平平穩穩地
飛臨臺灣上空
空姐提醒 桃園到了
將要結束黑暗的航程
我從舷窗俯瞰地面
地面燈火通明
我懸著的心 反倒更加忐忑
說不清是急盼著陸
還是想久留空中
五十年前 我曾在邊防線上
是名空軍雷達兵
臺灣一個叫桃園的地方
格外繃緊我的神經
桃園呀 桃園
我看不見你的三月桃花
只有熒光屏上的幾個陰影……
這次我乘坐BR761
海峽兩岸的雷達 都用
一雙關愛的眼睛
你送我迎
飛機慢慢地降落
我這脫了軍裝的游人
也卸下了往昔的沉重
機場跑道 幾番整修
桃園空域 清朗明凈
而停機坪上的飛機
也早已換了機型
嚼檳榔
臺灣 在地圖上
頗像一枚檳榔
但不知其味 總想品嘗
踏上寶島 從專賣店
買一袋檳榔
檳榔是臺灣的意象
我用一口殘缺不全的牙齒
嚼呀 嚼檳榔
誰知 難言的酸澀
刺激我的味蕾
麻痹我的口腔
——這就是臺灣嗎?
一個難咽的問號
卻勾住胃腸
嚼呀 嚼檳榔
折磨我的耐性
磨損裸露的牙床
檳榔汁混著口水
不斷地從嘴角流淌
嚼呀 嚼檳榔
漸漸地感覺一絲微甜
還有一縷余香
嚼呀 嚼檳榔
渣子舍不得吐掉
欲將全部滋味 盡收皮囊……
臺灣的檳榔林漫山遍野
不生椏枝 筆直向上
扎根山坡 是綠色的植被
站立路邊 是歡迎的儀仗
乘坐的旅游大巴
圍著臺島 在檳榔林里穿行
滿目盡是檳榔風光
再看輪下轍印
從北到南 從南到北
不經意間 竟然圈起
一個碩大的檳榔
返大陸時 本想
帶回一籃熟透的檳榔
讓親友分享
可水果禁止攜帶
——要知檳榔的滋味
只能親臨臺灣 自己張口
嚼呀 嚼檳榔
臺北故宮
本應只有一個故宮
卻一分為二
一在臺北 一在北京
臺北的是仿古建筑
北京的是古老原型
北京故宮 我多次觀瞻
可每次都悵然若失 神色凝重
此番登上臺島
欲補心中缺憾 以求完整
走進臺北故宮大門
登著臺階 數著樓層
將稀世珍寶一一過目
驚嘆中 又幾度噤聲
當年 這些國寶
被偷偷地運出京城
輾轉萬里 歷經戰亂
未能流失
可謂民族大幸
只是臺北故宮太小
中外游人擠爆了展廳
有的藏品難得一見
至今仍被歲月塵封
我這大陸游客
臉上掛滿了愁容
本是一國之寶
何必分存兩地 難成一統
忽想起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我才稍稍得以撫慰
不再憂心忡忡
身首分離的傳世名畫
最終在臺“山水合璧”
補你闕如 圓我殘夢
那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
也定會分久必合
海峽兩岸 共集大成
9btX+x2Od//jQpGvweTiWptAarFUUX0o6VW1q2bg034=我走出臺北故宮
看著剪過的舊門票
我想 說不定哪一天
到北京 還可再用
士林官邸的教堂
士林官邸的深處
一座紅色的基督教堂
風雨中的十字架
讀出了宋美齡的信仰
當年在此潛心修行
雙手合十 虔誠至上
做了一個禮拜 又一禮拜
祈禱救世主
救贖一個東方女子
驅逐眼里的憂傷
熟讀圣經 篤信教義
欲想走出大半生的迷茫
可依然為世詬病
只因 貼身服侍著
千夫所指的老蔣
想想二姐宋慶齡吧
受國人愛戴 為宋門爭光
而宋美齡的名字之美
卻未贏得褒揚
風燭殘年的蔣介石
孤獨而又絕望
也許陡生一絲懺悔之意
也許有種贖罪之感
也像個基督信徒
隨夫人走進教堂
——雖經洗禮
上帝也不會饒恕你的
那放下的屠刀 未洗凈血腥
和善的面孔 經過化妝
如今 教堂的主人早已離去
清冷的十字架
平添幾分蒼涼
我是個無神論者
(《國際歌》詞: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此時 正隔著鐵的護欄
在一旁觀光
紅檜林
一片原始的紅檜林
提升了阿里山的風景
一個天然的氧吧
任我吸納 免費提供
真正是樹的大家族
一代又一代
枝葉牽手 根須溝通
長者已兩千三百多歲
子孫也七八百的高齡
六十米的偉岸身高
十幾人圍攏的闊大心胸
一個臺灣特有的樹種
參天而立 樹色褐紅
那來自原始的基因
至今未曾變異 未改屬性
臺風時常過境
樹大自然招風
尤其在這高高的山頂
卻未見大樹連根拔起
只是折其枝杈 為之整形
難怪稱為阿里山的神木
真是入木三分 古樹有靈
實在是過于古老
有的樹心已經腐朽
給年輪造成空洞
——那是常年挖空心思
留下無法愈合的后遺癥
忽然一陣山雨襲來
我急忙躲進樹洞
幸好沒遭雷擊
否則就要喪命
無意中 我把樹心充實
古樹不再虛空
我與大樹渾然一體
分不出哪是人 哪是樹
哪有血肉 哪有魂靈
看我頭頂之冠
白發不見 變成一蓬青蔥
而千年紅檜 也因我
縮減了原始的樹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