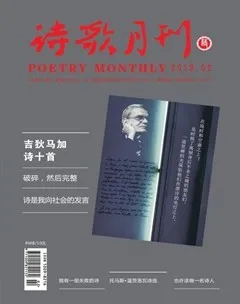俞昌雄的詩
這就是二十一世紀
棉花糖包著少女的心
地標性建筑是新長出來的指甲
狗和很多人握手
從不見主人的表情
深夜里總有人在地圖上散步
我緊跟其后,遇見
政治家、野獸和睜著瞳孔的植物
地球在顫抖,人類卻一無所知
這就是二十一世紀
天空被搬到地面,烏鴉在裂隙中
飛行。我用羽毛包裹自己
宛如一件歷史的遺物
對一只石獅子說話
我對一只石獅子說話,而另一個人
正在故鄉的另一頭揣摩它的樣子
那個比我年長的人,他打算用剩下來的
時間,協助我從花崗巖的紋路里
取出鑿子的力量。我的故鄉
天還是亮的
月亮升起來
天卻黑了
我怎么知道
那些人從山那邊回來
說山那邊還有山
太陽一直往下落
月亮一直往上升
昨晚出現過星星的地方
今晚空著
壓力測試
一列火車怎么搖擺才像一列火車而非棺材
一列火車行駛在夜里
而夜浸泡在水中,一列火車
有棺材的外形,也有死者的表情
那是在曠野,小站臺的路燈下
白色的石牌上寫著黑色的站名
我撩開窗紗一角看見一張臉一晃而過
我聽見車輪擦拭著軌道發出膠卷底片的呻吟
石獅子在夜里都是醒著的
它們不奔跑,但那含在嘴里的圓珠
總能發出奇異的響聲。有時
我站在月光下,不小心摸到自己的骨骼
它們比想象中來得光滑,堅硬
這讓我想起石匠的角磨機
想起那個年長的人,他用魔法
從石獅子的尾巴里掏出時間暗藏的火
我為此感到驚訝!在我的故鄉
很多人對石頭都充滿敬意,很多人
對靜夜里的石獅子束手無策
只有我,還有那個比我年長的人
聽得見它的呼吸,聽得見
一把閃光的鑿子在石塊中劃過的聲音
也許,來世的人們并不這么陳述
他們習慣于在文字里標記:
有一個夜晚,城里的石獅子睜眼了
在那搖擺的石座上,一高一低的
兩副身影認真比劃著,月光是那么的亮
高的說,是時候了,你來完成吧
矮一點的說,再等上一桿煙的功夫
那么圓珠會滾動,石獅子自然會說話
讀關晶晶的作品《無題09-01》
很多人明白了,我還不明白
很多人喜歡巨幅畫像,我只喜歡剪影
譬如關晶晶的《無題09-01》
陰暗的不是人生,光明的又太像人生
線條往畫布里跑,成色塊,藏著一口氣
代替時間,尋找旅程中的批判者
多出來的與悄悄少掉的,大的與小的
黑與白,死去的肉體與復活的魂靈
它們相互交叉,疑似一個正被涂抹的時代
尺寸都是虛設的,唯有光斑在移動
早晨到黃昏,悲劇到喜劇
留白越來越空,命運從那兒發出了聲音
很多人明白了,我還不明白
為何人世的軀體都要摸到自己的支架
而后懸空,徒留死去的一片片色彩
它們獲得呼吸,軀體卻落滿塵埃
侏儒
天空再高,與他們無關。那些侏儒
時常被打發,他們在夢中
不得不與傳說中的草木偷偷對話
年輕的要光亮,年老的將卸除偽裝
原來,時間在他們那兒丟失了刻度
身體壓得矮矮的,心卻攀升
那些侏儒,祈求從人群中獲得替身
說響亮的話,做不可預見的事
這樣的時刻,天是藍的,地很寬
擦肩而過的人驀然就想起一句古訓
“每一座埋著獵人的森林,定有草木
佯裝珍禽,在幽徑里獨自生長”
一些叫不出名的植物
一些叫不出名的植物總是比我們
更快來到人世。我們活十年
它只在自己的光線里閃爍一回
在山崗的投影里,在泉水尚未走遠的
時刻,它生長,和時間無關,和
那正被偷換走的身體有關
我們有時聽到說話,摸到一些氣息
那叫不出名的植物如此謹慎
它躡手躡腳的樣子,不動聲色的樣子
并非針對我們。它要去的地方
也許在云端,也許在夢里
我們當中的某個人,在某天某個時刻
被它領走,藏在細小的陰影里
這時,山崗是看不見的,而泉水已枯
竭
我們依舊在這個世界等待,等待
時間來追趕,我們未曾收留的一切
那叫不出名的植物,到底是誰
它有白天卻沒有黑夜,它有血脈
卻沒有行蹤。我們猜測,并在文字里
恢復那早早被抹掉的光亮
而我們當中那個早已消逝的人
他已脫胎換骨,他時刻站在我們背后
以另一種寂靜的儀式,要求我們
脫掉老舊的軀殼,從晨曦中
喊回那曾被大地深深愛過的樣子
悲傷
整座城市埋在雨水里
夜店的燈亮著,妓女們
從一條小巷跑向另一條小巷
誰都不知道這是不是生命當中的
最后一夜。我悲傷。世界
在此刻,有一顆黑漆漆的心臟
妓女們躲在自己的身體里
跳舞,她們不愿出來
她們有淚,哪能和雨水一樣喧嘩
昆蟲是無罪的
一個殺死人的罪犯在監獄的墻壁上畫了
無數只昆蟲。提審時,法官問:
你為什么去殺人?罪犯說,因為我是一只昆
蟲
我已經在地上爬了,為什么還有人來踩我
法官說:殺人終究是要償命的
罪犯閉上了眼睛,輕聲問了一句:
“在上帝眼里,昆蟲難道不是無罪的么?”
讀拿單·扎赫
我不認為以色列是個小國
那個詩人,拿單·扎赫也這么看
在特拉維夫的劇院里
他取走了舞臺上每一塊被虛擬的土地
但帶不走角色。在黑暗的廊道里O11b0Ivxuc7k09QoNA64zUHm7mXEQRzcxbuF6FTMaAQ=
他喊了一聲,這才掉下一滴淚
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在弧形的遺骨和廢舊的木樁上
在那片失落的大陸
拿單·扎赫用楔形文字把自己
標注在太陽底下。而太陽
多么簡單,它掠過以色列時也幾乎
照亮了流血拼命的戰場
我看見拿單·扎赫持燭的手上
刻著一個深夜,舊事物開始
深陷,歷史也是,好比那些窟窿
即將要埋葬細碎的火星
拿單·扎赫挪動著笨拙的身體
他知道很多東西都擋住了
光明,但詩歌沒有
他在那些文字中被一次次保留下來
以至于今天,我能在危險的
旅途中和其相遇。我想攙扶著他
去認領半個世紀前的那個傍晚
以色列被狠狠壓在地上
他卻站著,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那片土地的一部分
每當日落時,大地就多出一份重量
我能深深地感到,在今天
那股力量時刻都將涌出地表
尋找托身之人,在每一個角落
以迎接黑暗,那深不可測的空茫
傳感器
五官已不夠用了,每個人都緊張
躲在角落里的那個人,很多零件被毀壞
他還不能停下來。他是祖國的一臺
機器,即便回到家里,在停電的晚上
身體里的燈還亮著,那是傳感器
每一根血脈都連著神秘的按鈕
有些人裝在額頭,有些人被埋入腳掌心
他的,安在心臟的最前方
他摸了無數遍,但取不出來
祖國說,看哪!山河是如此明亮
每一寸土地,都要得到相同的指令
草木繼續蔥蘢,鳥獸回到巢穴
至于躲在角落里的那個人
給他未來的投影,再給他舊時光
他就是完整的——完整如一滴失散的
水銀。幾十年一晃就過去了
躲在角落里的那個人并不知道
身體里的那個部件,它是多余的
或者必不可少?每一天都能聽到響聲
每一個晚上,他一旦放開手腳
那個被稱為傳感器的東西就一直亮著
在胸口,在黑暗遮蔽不了的地方
祖國從身體里走了出來,輕輕地說
“鬧鐘已調好,你得看到明日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