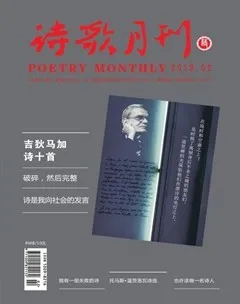破碎,然后完整(選章)
黃昏,還是黃昏
最終,你無法釋懷的還是黃昏。
“為什么不是黎明,不是夜晚?多么誘人的午后,正在呈現她的慵懶與明媚。”
而風疲于應答,仿佛它被糾纏過很久,或有不可名狀的苦衷。
追問往往窮盡余生。
“為什么非要抱緊這樣一段未知的山水,選擇這樣一個出場的愿景?”
“關乎輾轉的流年,今生的遇見”,一個遲到者的喃喃自語。
這或許是此生最蹩腳的注解了,卻安頓著一顆就要落定塵埃的心靈。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間的節點?你搬空了日子的兩頭,只為拉長這一小段夕光下的流水?
那么,你潛心揀選的黃昏該作如是描述:除了寂靜與遼闊,其它都不是你的落落清歡。
夕陽的余暉并沒有鍍向你,低徊的只是一個人歸鴻般的形單影只。
遠山的風并沒有吹送你,它已在黎明推開了白鳥之翼。
至于鳶尾花,它只能在一首詩中沉默,盡管藍是你與生俱來的清朗。
那么,只剩下這谷底的空曠了,也覆蓋不住你半生的寂靜。
“而美是需要認領和執守的。”
正如逝水念念有詞般地唱誦“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幾千年的曲水流觴漫過了萬千的光陰,或明媚,或頹敗,煙嵐深處,余音猶響……
但這聲音還是忽略了你,越過了你——
仿佛從某一天起,你省略了晨曦與夜色,搬運的只是黃昏的空曠,等待的只是一記沒有回聲的——空響。
一首詩的禮遇
她一直深信,
過去,現在乃至將來——
于所有現實的山水與虛無的明月中,除了時光這臺機器,沒有什么能潰敗她中年的肉體;除了時間這朵玫瑰,沒有什么花能刺痛她安靜的指尖。
而最輕淺的或許是最重磅的?這個假設的突然成立,就像無意間一首詩給予她的特殊禮遇。破譯一首詩的隱晦,她得以撥開眼中的重山與霧靄,一切珠絲有跡可循,淵藪被層層打開,止水不小心溢了出來。
之于她,悲情的不是窺視到字里行間的種種暗示與巧合,而是她自己藤蔓般糾纏的內心。這里有不為人知的籽實完整,被胡桃般精巧而縝密的外殼所包裹。這么多年的生活瑣碎,并沒有支離一顆糖果的內心。
或許1分鐘,甚至更短,她聽到了冰凌的破碎聲,就要遷徙進春天的飛鳥被結冰的詞語所投擲,白色的雪擁著黑色的羽毛紛紛而落,她被滯于二月的歧途。以至接下來的春天、夏天,夢境重疊而凌亂,瓦礫、碎石、雪線或者是另一些搬也搬不走的詞語。
受阻于一首詩,淪陷于這白紙上的隱喻,沉湎于文字間泛起的波瀾,那些與她本無瓜葛的盛開與頹敗,白晝與夜晚相互牽纏的浮光與暗影,那些熟稔的意象像密集的子彈將她一次次擊穿……
這些秘而不宣的禮遇只屬于一個人的跌宕,而不知不覺就秋了!
除了繼續沉默,小心按住那些涌自肺腑的潮汐,或者顧左右而言它地寫下:“要在秋天葉落之前,
逃離或者抵達。”
——是了,秋天遼闊,盡可以湮沒YTe9/N26bRsWgT6h1fxYOQ==所有的悲欣。
二月的墨水
漫長的冬季之后,水仙終于向我投以幽暗之香。
但除了這香氣,我還能備忘些什么?
外面始終是喧嘩的,形形色色的玫瑰在形形色色的手掌中傳遞,空氣的罅隙有了局促或者曖昧的暗
示。無可否認的此刻,我正躲在時光的柵欄里覬覦這玫瑰的花瓣,這有形有色的浪漫……倘若多棱
而銹色的目光可以忽略那些尖銳的時間之刺。
一定有什么是草芥無法逾越的高度和圍欄。
所以,關上門吧,所有敞開的門。
與其讓嗅覺被二月遞送的花香所迷醉,不如讓欲望的呼吸屈從于內心,讓內心屈從于一株水仙的安
靜。讓孤獨的喘息回到一首孤獨的詩,回到一個詩人寫下的第一句,“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
哭。”
但如果,二月的文字是被用于涂鴉情緒波動的雙曲線,那么哭泣一定是一個隱忍不發的漸近詞。但
是二月,這一年中最短的月份,僅僅29個晨昏,卻耗盡一個人積攢了一冬的墨水。
置身于二月的幽香,我已沒有多余的墨水豢養這香氣,只有深深地、深深地呼吸。
所以關于二月,我選擇遺忘一次,空白一次。
四月的荒原
我再一次認出了你。
認出荒原之上,穿過的是風,還是風。
喏,四月!借我以平曠千里之眼吧,或者干脆讓我淪為一只風暴之耳。
聽,這風之咆哮,無限地指向四面八方的虛構。未來的箭簇一定指向東,而往事的弓弦只有向西按
下夕陽的快門。過去,現在和未來啊,這一段段被風拂過或者即將拂過的浩繁塵世,——被吹近,
然后再吹遠。
所以主宰的風呵,它必定握有遼闊與豐盈,也同時抱緊命運的貧瘠與富庶。它只身享有喧嘩與呼
嘯,也獨自消磨由此而來的深淵般的孤寂。
而我再一次認出了你——
認出了這是四月的荒原啊,我愛!
當陳舊的死亡一面露出惶恐的訕笑,一面向我投擲風的匕首。荒蕪像附著于白紙的言辭,誰能為一
首舊詩步半闋新詞?
顫抖的鳥鳴,凜然的辭令,隱晦的氣息……此時的荒原就是個巨大的喻體。看吧!虛幻或者真實即
將被打開各自的淵藪。草芥低矮的身姿讓它得以比枝頭、比花朵獲得與春天更早的和解。此刻只有
風,一次次穿過蟄伏的蟲豸,穿過我形同虛設的本體,而你多像一枚喻詞,在春天己等候多時。
每一個荒原背后都是一個期待。
如果你說,“荒原何其盛大,春日就何其盛大。”
而我正如草葉靜默,只等一聲裂帛穿身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