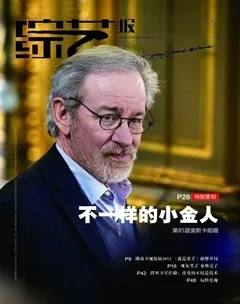“下一部作品”是最大動力
1997年,格斯·范·桑特導演的《心靈捕手》不僅捧紅了名不見經傳的本·阿弗萊克和馬特·達蒙,更是把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劇本獎收入囊中。15年后,40歲的本·阿弗萊克帶著自己的導演作品《逃離德黑蘭》來到《好萊塢報道》頒獎季圓桌會議。與他一起分享導演經歷的還有:《悲慘世界》導演湯姆·霍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導演李安、《烏云背后的幸福線》導演大衛·歐·拉塞爾、《被解放的姜戈》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談話中,演員出身的阿弗萊克連連打趣,說自己是“在座惟一一個可能被其他人雇用的人”。
問:作為導演,你們經歷的最艱難時刻是何時?
湯姆·霍珀:我14歲的時候和哥哥一起拍攝我的第二部電影《飛行夾克》,我任導演兼攝像,他主演。當時我準備了100英尺的膠片,按1秒16幀算,成片率大概在1.2比1。結果哥哥突然發現他有機會凌駕于我之上——如果他在拍攝中故意出錯,我的膠片就全部白費了。那次,他把我弄哭了。
昆汀·塔倫蒂諾:可是,本·阿弗萊克還是讓他哥哥(卡西·阿弗萊克)出演了他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失蹤寶貝》。
本·阿弗萊克:我哥哥常說:“你這是占我便宜。”
昆汀·塔倫蒂諾:講故事也好,和演員、劇組打交道也好,對我都不是難事,在我看來都是分內的工作。承擔整個制作任務,正確引導團隊,每天想方設法鼓舞大家才是最難的。有時我很想發飆,想撂挑子大喊“我受夠了”,但我不能,因為整個劇組都指望著我。
李安:主創人員發生更替會讓我很難過。有一次我不得不換掉配樂師,具體是哪部電影就不提了,那滋味很不好受。賣座和不賣座的電影我都拍過,我真心為劇組所有人的工作自豪,但有時不得不把個人感情放到一邊,選擇相對熱門的人選。每到那種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很失敗。
問:預算高于以往的作品會不會讓你感到壓力倍增?
李安:預算數字確實會讓人抓狂,不過一旦開工后,冷靜下來,狀態就不一樣了。從影以來,“想做的下一部作品”是我的永恒驅動力,那是一種讓你不得不集中精力的危機感,甚至是恐懼感。這些內心深處的情緒讓我保持清醒。
問:你們都可謂功成名就,會擔心頭上的光環在某一天消失嗎?
昆汀·塔倫蒂諾:完全不擔心。我可沒打算一輩子都當導演。
大衛·歐·拉塞爾:真的嗎?這可是個晴天霹靂。
昆汀·塔倫蒂諾:我也許會去做編劇,或者寫小說,或者寫寫電影文學、電影論著、評論文章之類的。讓我產生這個打算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忍受那些數字化的玩意兒,我當導演不是為了拍這些。如果還要做和銀幕相關的事,我寧愿把劇本拍成HBO的迷你劇——沒有有時間上的壓力,可以從容地忠于劇本精髓。我的劇本內容總是比實際拍攝出來的多,惟一能完整呈現我整個劇本的電影是《殺死比爾》,因為我把它拍成了兩部曲,那個本子我足足寫了一年。
問:是不是得“瘋魔”到一定程度才能當導演?
大衛·歐·拉塞爾:需要極大的熱忱和極強韌的神經。
湯姆·霍珀:拍《悲慘世界》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我讓演員現場真唱是瘋了,他們勸我放棄現場真唱,但最后我還是遵從了自己的直覺,。
本·阿弗萊克:作為導演,必須夠瘋狂才能承擔如此多的責任。當然演員里的“神經病”也不少,我就碰到某人把測量輻射指數的計數器帶到片場測量戲服的放射性,夠神經質吧。
問:你們遇到的最古怪或者最好玩的影迷是什么樣的?
李安:我最近接受過一個女記者的采訪,采訪快結束時她說:“我希望你能執導《愛與痛的邊緣》(編者注:美國暢銷情色小說)。
昆汀·塔倫蒂諾:有個14歲的小女孩寫了一個《殺死比爾3》的故事大綱給我,并說她想出演長大后的“黑蛇”的女兒。我認真讀了她的來信,并給她打了電話感謝。我很感動這樣的小女孩能如此喜歡這部電影,并希望這個故事繼續下去。
大衛·歐·拉塞爾:其實我很希望昆汀能夠繼續拍電影,我喜愛你的作品。還記得10年前我跟戴安·基頓聊起導演伍迪·艾倫,我們有些擔心他的創作狀態,但事實上他至今仍保持著幾乎一年一部的創作速度。我贊賞這種生活方式,也非常喜歡他去年的作品《午夜巴黎》。
昆汀·塔倫蒂諾:巧了,那也是2011年我最喜歡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