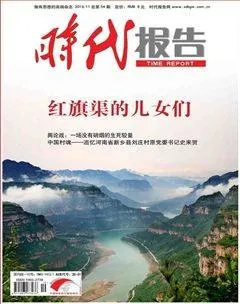向遺產征稅仍需時日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將我國經濟推上了快車道,也讓貧富差距漸次拉大,用遺產稅優化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呼聲日漸高漲。
遺產稅的運作機理就是通過削弱財富在代際間的傳承能力達到縮小貧富差距之效。在西方許多發達國家,遺產稅已在抑制貧富差距所引發的社會負面效應、平衡納稅人心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年前巴菲特與蓋茨來華高調舉行慈善晚宴,讓國人看到了國外頂級富豪的“慷慨大義”;去年曝光的蘋果CEO庫克天價年薪,不僅未遭致美國輿論界質疑,反倒多有褒獎之聲。諸如此類的現象表明,貧富差距并未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引發各階層間尖銳的對立情緒,公平的創富機制甚至讓富人成為了勵志標桿和學習楷模。以遺產稅為代表的制度設計引導了富人群體更多地關注社會慈善事業、強化了個人憑借奮斗成功的社會理念和自強不息的創業精神。
相形之下,我國基尼系數也已經越過了貧富差距的警戒線,2012年該系數達到了0.474,明顯高于印度、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的水平。在“隱形富豪”大量存在、致富模式復制難度較大的背景下,貧富差距已影響到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恰因此,我國亟待通過制度創新促進財富在各階層間的合理流動,以此化解階層相對固化的現象,而遺產稅就成為其中較為有效的備選工具之一。
今年3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發布報告認為,開征遺產稅的時機已經成熟,起征點應定為500萬元。有機構據此測算,1億資產繳納遺產稅之后所剩可能不足千萬。在國人養兒防老、光耀門楣的傳統理念中,個人財產最終是要留給子孫后輩的。若遺產稅開征后億元家產在身后將會化為烏有,許多人恐怕在情理上難以接受。今年年初深圳開征遺產稅試點傳聞就立刻觸動了高收入者的神經,向保險公司咨詢“保險避稅”的企業主絡繹不絕。而此前為了預先規避遺產稅,許多人也主動以孩子的名義購置房產,以至于“小鬼當家”現象在各大城市紛紛上演。可見,富人群體對遺產稅動向頗為敏感,如果稅負偏高就會導致資本財富外流風險。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富人移民潮已然攪動了財富轉移的一池春水,業界擔憂遺產稅出爐將會加劇這一現象蔓延,進而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和財稅收入的穩定。更何況在房價飆長的情境下,一線城市一套房產就可輕松突破500萬元的“紅線”,遺產稅極有可能淪為平民稅種,與“削峰填谷”的稅收機理產生背離。
以此觀之,遺產稅開征需以完備的信息統計及資產管理措施為重要前提,否則不僅征收標的難以厘清,還有可能反向加重財富分配不公現象。遺憾的是,信息系統滯后恰恰是當前國內的一項軟肋,我國尚未實行統一的個人財產登記制度,稅務機關主要掌握的僅僅是公民工資收入信息。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住房信息聯網工程已在住建部的努力下推行了近十年,至今仍未真正成形。住房信息聯網工作尚且舉步維艱,我們更難奢望有關部門能在短期內精準掌控珠寶首飾、股票等個人其他財產的統計數據。這意味著,擁有更多資產配置形式的富人群體,可以通過多種途徑進行財產轉移與避稅,這無疑給遺產稅的公平征收形成了羈絆。另一方面,海外遺產稅征收運作較為平穩的國家,大都有完備的社會福利體系“兜底”。因為只有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百姓生活需求均獲得完備保障之后,遺產稅開征所面對的現實阻力才會減小。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正處于積極構建當中,包括財政資金撥付、市場化補充渠道暢通等工作均需得到進一步夯實。而在居家養老模式尚未大規模向社區、機構養老過渡之前,遺產稅開征環境也難言成熟。
遺產稅之名在國內盛傳已久,但起真正被納入稅收體系,或許仍需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