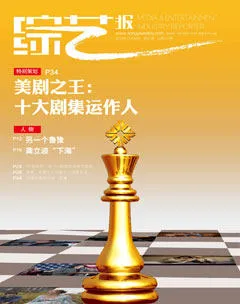《甜心巧克力》“純色”愛情

放在日本,《甜心巧克力》也許是一部尋常的愛情電影,但在中國就顯得有些另類——大銀幕上盛行的是一種由重口味笑料和極致煽情配方而成的“麻辣燙愛情電影”,該片則是一部舒緩甚至散淡的“純愛”電影。
今年以來,小妞電影大爆發。從年初的《北京遇上西雅圖》到年中的《被偷走的那五年》等,女主人公環肥燕瘦,花色多樣,但均離不開嬉皮笑臉的毒舌,情色暗示的金句,以及可憐巴巴的女主人公。前兩項是逗人笑的,后一項是招人哭的,不讓觀眾哭哭笑笑,似乎就不是一部合格的“浪漫愛情喜劇片”。
筱原哲雄導演的《甜心巧克力》反其道而行。兩個日本小伙子和中國女留學生的故事,在北海道的小城夕張和繁華大都市上海之間交替進行。夕張人煙稀少,就是三兩人游動在蒼茫天地間。上海的地標建筑倒經常出現,但都是空鏡,劇中人并沒有和熙熙攘攘的外部發生實質性交流。外部空間是疏離的,他們一直在努力打理內心世界。時空也是靜止的,他們現在做的事一直是十年前《北海道往事》的續篇。100分鐘看下來,沒有急管繁弦,只有淺斟低唱;沒有撕心裂肺,只有黯然神傷;沒有大吵大鬧,只有相對無言;沒有拿時事和性開玩笑,只有尋常的邂逅和無聲的會意。
中國正處在一個集體尋求致富的狂熱年代,即使電影中的愛情,也總被房子、車子、票子、孩子等現實問題所纏繞。這既是時代精神格局所限,也是商業電影對觀眾的刻意擺布。雖然純真的愛情總會戰勝物質侵蝕,但回頭看看就能發現,影片的主體部分一直為身外之物糾結,為之哭,為之笑,為之惱,為之鬧,那個閃亮的結尾太像靈魂出竅的不真實旅行。所以,面對《甜心巧克力》這樣一部壓根兒不涉生計,也不急吼吼敘事的電影,就如同在暑氣逼人的七月喝了一杯冰鎮汽水。久石讓泉流般的音樂,為影片更增清冽。
風格上的小清新,對中國火急火燎的影市是有益的補充,但就沖擊力和感染力來說,《甜心巧克力》還不能令人滿意。首先,情節的鋪設不夠精妙,導演精心布置的底牌,在30分鐘后就能隱約猜到—— 一個意外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其次,因為散淡和留白,愛情的起承轉合有些“怪咖”。面對木場和星野再明顯不過的好感,林月選擇了后者,但木場和林月隨后“不偶不友,亦偶亦友”的十年相處,太讓人費解。這種基于日本情愛文化的設計到了中國,出現了明顯的“懸浮”感。雖然感情世界的第一定律是“測不準原理”,但愛情電影尤其重視同感、通感和痛感,這三方面都不能有所作為,必然會影響影片的到達率。其三,就表演而言,池內博之扮演的木場深情穩重,福地釣介扮演的星野陽光活力,但林志玲到了需要情緒反應時往往木然以對,不能不說是種遺憾。
這部影片讓人想起巖井俊二的《情書》,以及旅日導演蔣欽民的《初到東京》——為什么日本的愛情電影都滲透著純凈的氣息,都能超然于物質之上而專一關注心靈,而我們的愛情電影卻總是扎在煙熏火燎的世俗中不能自拔?答案暫時還沒有,這需要我們一起慢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