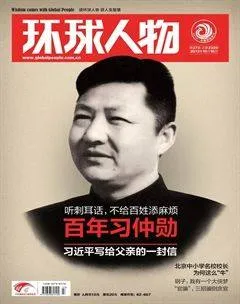“周文”的興起是中國的興起
中國和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國家與文明相比較,形成自己相當特殊的國家與文明的道路,大致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我以為大致是從三千多年前的周朝開始。在此之前,中國也建立了國家和王朝,其信史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從夏朝開始的三代(夏、商、周)。但夏商兩代的文獻較少,我們對商代稍微知道得多些,但也多是知道它的晚期,即因為商被周取代,我們從周興的歷史得知商末的沒落。
但從這即便較少的文獻,我們也大致可以看到商朝和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國,尤其古國中的大國多有相似之處:比如集權甚至專制的君主;虔誠地相信一種超越的存在(上帝);朝野之風似都有些豪放但也有點欠缺文采;不是那么重視嫡親BTNK3AHm02kzlCkLNjDdqw==的直系血統,君位也可兄終弟及;君主相當自信甚至太自信——相信天命始終在身,等等。
但周代的興起比較徹底地改變了這一切。幸運的是,大致也是從周代開始,我們開始有了比較詳盡和連貫的歷史記錄,尤其是周朝歷經文王、武王、周公“三圣”的興起,有了相當詳細的記述。我們看到,周代君主不再那樣相信天命而是更重視人事了,他們相信天命更多地系于自己的德行和治理,對超越的存在雖然敬畏但也不是那樣虔信了,而且將政治權力相當程度地分散到各地,當然首先是分封自己的親屬,但也照顧到功臣、公認的德者、賢人,乃至被戰勝的前朝君主的后人。君主比較小心謹慎甚至有點“戰戰兢兢”,朝野之風漸漸從奢靡、野性和尚武轉向比較節制、文明和守禮。
我們或可用“周文”來概括周代興起的這一政治和文化的傳統,說“周文”并不只是指周代的狹義“文化”,而不如說是點明周代的政治文化傳統所具有的一種“文質彬彬”的特征,說“周禮”也有接近的意思。這一“周文”大致可以用王國維所說的“尊尊、親親、賢賢”來概括。這一政治的大轉型應當說還是相當成功的,僅舉一例,在五六百年間,上百個諸侯小國在中華大地能基本相安無事地和平共處,不互相野蠻地征服吞并,這也是世界文明史上難得一睹的政治奇觀。
而更重要的是,“周文”的傳統并沒有隨著周代的結束而結束。在春秋時代,雖然開始“禮崩樂壞”,但像孔子和儒家等學派還是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周文”的命脈。而在秦朝建立了強大的統一國家但卻“二世而亡”之后,代秦的漢朝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之后,在漢武時期終于吸納了儒家所承續且有獨創發展的“周文”,從而找到了一條傳統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此后兩千多年,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基本類型可以說是將支配思想的“周文”與統一國家的“秦制”結合起來的“漢制”,而并不是單純強力的“秦制”。
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說,正是從周代開始,中國開始走了自己的路;正是從周代開始,中國才成為世界文明體系中一個特殊的中國。沒有周之更商,或許也會有其他強大和統一的王朝國家,但一定不會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