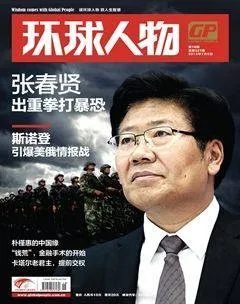鄭一鳴,開美國航母的中國人

“小時候,我膽小是出了名的,甚至從來不敢主動開口說話。”鄭一鳴說道。然而,就是這個小時候膽小到連滑梯、木馬都不敢玩的人,后來居然當了8年美國大兵,跟著航母出海,打過兩次仗,還成了唯一一位開美國航母的中國人。
“以前認識我的人都說怎么也想不到,我說我也沒有想到。”他笑著說。更讓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書《我在美軍航母上的8年》近期在中國面世了。
其實早在出版前,書中內容就已經在國內網站廣泛流傳。6月27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聯系到了遠在美國的鄭一鳴。他非常謙虛,雖然在部隊屢次獲獎,但除了家人外,誰都不知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之后,我會把它們當成歷史,這些事都已經過去了。”
方向盤比汽車的還小
看起來憨憨的鄭一鳴是個“80后”,15歲時,他從甘肅蘭州前往美國特拉華州和做訪問學者的媽媽團聚。“在學校里,我成績不好,總受人欺負,很自卑。”雖然讀書墊底,但鄭一鳴的動手能力很強,高中畢業后,他進入一所社區大學學機械原理。
一次偶然的機會,鄭一鳴走上了參軍之路。他的好朋友查理與海軍簽訂合同,高中一畢業就入了伍。這讓鄭一鳴萌生了參軍的想法,“我一直有個愿望,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加入海軍正好能實現。而且,我參軍回來,政府會給我錢、供我讀書,就可以不花父母的錢了。”2003年3月,就在鄭一鳴報完名等待去新兵訓練營期間,美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想過可能會犧牲嗎?”記者問。“當然想過。可當兵就是要打仗的,咬著牙沖上去就是了。”
2004年春天,鄭一鳴登上了“卡爾·文森”號航母。盡管他在報紙上多次看到航母,但第一次真正見到時,還是不由驚呼:“光甲板就有3個足球場那么大。”在航母上,鄭一鳴當了一名飛機維護長,負責打手勢、接發飛機,以及檢查、維修飛機。
“我有點像阿甘,不懂偷奸耍滑,只知道埋頭苦干。”鄭一鳴的踏實負責讓他成了飛機維護長中的“佼佼者”,得獎無數,名字也被印到了飛機上,成了名人。而最讓鄭一鳴驕傲的是,他獲得了“年度最佳水兵”,這是航母上的最高榮譽,獎勵是親手駕駛航母。“一艘航母上有5000多名海軍,每個月選出兩個人,出海半年,總共只有12個人能夠被選中親手駕駛航母。誰能被選上,都足夠驕傲一輩子的。”
在航母的指揮室,讓鄭一鳴大吃一驚的是航母的方向盤。“我總覺得,航母的方向盤應該是很大的,可事實上,它比汽車方向盤還要小。方向盤旁邊,還有一個操作桿,用來調節航母速度,輕輕往上一撥,停住,航母就能自動以這個速度行駛。”鄭一鳴把手放在方向盤上,聽著駕駛員的指導,邊看電子顯示屏上的海圖,邊跟著轉方向盤,就這樣開了15分鐘航母。因為當時鄭一鳴只是持有美國綠卡,未加入美國籍,他便成了唯一一個親手駕駛過美國航母的中國人。“當時有點嚇傻了,人家叫干啥我就干啥,后來回憶起來,卻所有細節都歷歷在目。”
要是幾星期沒聽到喊“有人跳海”,我們都會覺得奇怪
航母上的生活是枯燥、單調的,尤其是頭幾個月,干不完的活,吃飯、洗澡、睡覺也成問題。鄭一鳴睡覺的地方,正好在甲板下面,炸彈艙上面,可謂飛機當“被子”,炸彈當“褥子”,睡覺時總能聽到飛機降落時“哐、吱……”的聲音。“到了第三個月,都不想活了,非常壓抑。”慢慢地,鄭一鳴也找到了自己的解壓方式。“看看錄像、翻翻書、打打游戲,時間很快也就過去了。我也算是個工作狂,只要有活要干,我就去幫忙,所以剩下的自由時間并不多。”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很好地舒緩這種情緒。跳海自殺的事,鄭一鳴就碰上了。半夜三四點鐘,廣播里喊:“有人跳海啦!”所有的人立即起身去報到,檢查是誰不見了,全船5000多人必須15分鐘內統計完畢,5分鐘內直升機就飛出去救人。“在艦上不管是白天、晚上,我們必須穿救生衣。只要一見水,救生衣就能自動充氣,上面還有一盞燈,只要晃一晃,就亮了。”當然,有不少惡作劇的人把這種燈裝在垃圾袋上扔到海里。黑夜里,站崗的人根本分辨不出,只好一次次把所有人叫出來集合。“要是有那么幾個星期沒聽到喊‘有人跳海’,我們都會覺得奇怪。”
有一次,鄭一鳴犯了個大錯——在甲板上把手電筒丟了。當時正是夜里,飛機起降非常頻繁。飛行甲板控制室得到消息后,立馬把航母的飛行線都關掉了,該起飛的飛機不讓起飛,先在甲板上等著;該降落的不準降落,都在空中繞圈子。同時,船上的人組織起來,到甲板上去找那個手電筒。一個手電筒,為什么要如此大的陣仗?“飛機發動機如果把手電筒吸進去,不但會造成發動機損壞,還可能機毀人亡”。
航母上,除了男兵,還有不少女兵,“大概六七個士兵里面就有一個女兵”。“除了生理期可以不做重活外,其他方面不享受任何特權,跟我一起干活的女兵都像爺們兒一樣。不這樣就體現不出男女平等了,反而會引來批評。”但鄭一鳴也上演過英雄救美的一幕。一天晚上,他和兩個女兵一起上夜班,那天正好下雷陣雨,天氣很差。上司讓女兵們去檢查甲板上的飛機,可45分鐘過去了,她們還沒有回來,鄭一鳴自告奮勇上去看看。狂風巨浪,人站在甲板上就像坐過山車,隨時可能掉到海里。他只能抓住拴飛機的鐵鏈子,一點一點地往前挪,從這頭找到那頭,把每架飛機都找了一遍。終于,他找到了這兩個女兵,她們正抓著身邊的鐵鏈子,嚇得一動不動。
想當汽車修理工
“美軍的一大理念就是極為提倡團隊精神,所以才有‘仗不是一個人打贏的’這類口號。”鄭一鳴告訴記者,“但業余時間則是另一回事,在不影響秩序的情況下,不會控制太嚴。上班時像技術工人,兢兢業業地干好自己的活,下班后就像平民,愛干啥就干啥。”
“美國海軍的傳統就是煙、酒、嫖、賭”,而鄭一鳴被稱為“軍中圣人”,這些惡習通通不沾,每次靠岸休假,他喜歡到處走走,見識當地民風。在迪拜,他遇到了阿富汗人,他們從充滿戰亂的故鄉逃亡到迪拜當司機,窮得連鞋都買不起,只能光著腳開車。其中有個人,為了能回家看一眼,翻山越嶺要走很多天。“他們沒有任何東西,不停地干活,可總是很快樂的樣子。而我有時還會抱怨生活,覺得很慚愧。”鄭一鳴由衷地說。
鄭一鳴還是個“吃貨”。逛街時,他會背著軍隊發的綠色大背包,到當地的超市買各式各樣的食品,每次都塞滿一大包。他還因此成了航母上的零食供應商,連上司都時不時跑去問他要零食。
2011年7月,鄭一鳴離開了海軍,繼續在社區學校學汽車修理,準備將來去修理廠工作。“以后有錢了,我就自己開家修車店。只要有手藝,一輩子吃喝不愁。”言語間,他依然像個單純的大男孩。
現在他還是一名后備役軍人,一個月訓練兩天,一年要去基地正規訓練14天。“如果軍隊召喚,必須轉入現役參加戰爭。我還有兩年合同期,到期后我就不打算再續簽了。”
“這8年在航母上的生活,給你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么?”聽到記者的提問,鄭一鳴坦言,最大改變就是獲得了獨立和自信。我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可以養我一輩子,但我還是當兵去了。我不聰明,也沒什么過人的地方,我就是不想當啃老族。你最初說要采訪我,我很猶豫,因為我實在太一般了。不過我又想,也許可以通過我的經歷讓一些人去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成功?我相信不管你干任何事,如果能夠盡到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到最好,這就是一個人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