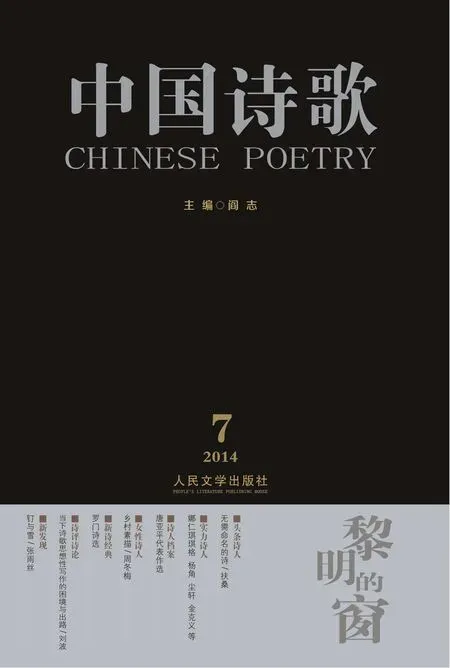2013年第52屆斯特魯加詩歌節詩作點評
□北塔
2013年第52屆斯特魯加詩歌節詩作點評
□北塔
詩人之戀
〔墨西哥〕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北塔/譯
詩只有一個現實:受難
波德萊爾證明過這一點。奧維德也會同意我這個說法。
另一方面,這一現實也保障了一個事實:
詩歌是一門臨危幸存的藝術
讀的人少,厭惡的人
卻很多
如同良知生了病,如同遙遠年代的遺跡
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宣稱
享有對魔術無止境的壟斷
《詩人之戀》的作者是來自墨西哥的大詩人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JoseEmilioPacheco,1939—)。2013年第52屆斯特魯加詩歌節頒發了5個詩歌獎項,其中最重要的是年度詩人獎,稱為“金環獎”或“金花環獎”,今年摘取桂冠的就是帕切科。他還是小說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曾獲西班牙格林納達國際詩歌獎和分量很重的塞萬提斯獎。
這首詩的正文是西班牙文,但題目作者用的卻是德文(Dichterliebe)。這至少有兩層深意。
1.典故意義上的。《詩人之戀》本是“音樂詩人”舒曼在1840年(舒曼音樂生涯中的所謂“歌曲之年”)譜寫的聯篇歌曲集。歌詞是海涅的詩集《歌集》(BuchderLieder)中的《抒情間奏曲》(LyrischesIntermezzo)20首中的16首。海涅是浪漫主義文學家的代表之一,但他又不失批評德國浪漫主義的精神,對同時代作家作品進行冷嘲熱諷是他作品的特點。德彪西等人常議論舒曼究竟用音樂表現了幾分海涅的諷刺。
帕切科這首帶有極簡主義特點的詩意蘊極為豐富,那么它的主要情調到底是抒情還是諷刺還是兩者兼有?答案是:諷刺。詩的第一行說:“詩只有一個現實:受難”。帕切科認為,恰恰是這一現實,保障了詩能在危險的處境中幸存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讀詩的人少之又少,因為很多人認為,詩不僅沒有用,而且有危險,不啻是帶病的良知(sickconscience),或者說詩人是有良知的病人。帶病的良知也許是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的最集中顯示。良知屬于詩人,但可能不屬于我們這個時代。主導我們這個時代的是“知”(science,所謂“科學”是也)。科學貌似普遍,實質是局限于時代條件的,但科學極為自負地認為,它是永恒的,與天地共生的,它甚至能壟斷魔法。而帕切科堅信,良知為各個不同的時代所共有。比科學古老的是“良知”,真正能掌控魔法的是詩歌。這首詩嘲諷了在所謂的“科學時代”里人們對科學的迷信,對“知”與“良知”的混淆。這首詩的前半首寫詩的受難品質,后半首寫科學的自以為是;從邏輯的演進上來說,科學自認為是能把詩歌從受難境地拯救出來的救世主,它以詩歌的救命恩人自居,從而想達到控制詩歌的目的。但帕切科想說的是:詩歌雖然處于受難境地,但無需拯救,因為受難是它與生俱來、不可消除的品質,是它的病,但也是它的命,除掉了這“病”,“命”也就沒了。況且,縱然詩歌是需要拯救的,那拯救的手也未必來自科學,因為“良知”與“知”迥乎不同,具有更加恒久的價值。這種對詩歌價值的肯定和稱頌則暗藏于“嘲諷”的后面。
2.修辭效果意義上的。上半首和下半首之間的邏輯推理表面上順理成章,實質上牽強附會,那是科學的自作主張、自我加冕。兩者之間這種似續實斷的關系產生了某種反諷效果。這種效果還體現在題目Dichterliebe和內容之間的乖張關系。Dichterliebe屬于舒曼,屬于浪漫主義,至少表面如此,因為那是舒曼命名的,打上了深刻的舒曼的音樂烙印,人們剛開始接觸了解這個詞時,馬上會聯想到這組舒曼寫給妻子克拉拉的纏綿之作。但事實上,這是被舒曼的音樂改寫了的海涅的詩。通過這首詩的寫作,帕切科顛覆了、剝除了舒曼音樂的外殼,還原了海涅詩歌的真面目。題目是那么抒情,而正文毫無抒情,只有諷刺和批判。正是在這抒情表面和諷刺內里之間,反諷的張力效果顯得更加強大。
被謀殺的詩人的土地
〔保加利亞〕柳波密和·雷夫切夫北塔/譯
在癌癥多發的熱帶地區
和北極圈之間
(在激情
和理性之間)
遠離
天宇
有一片繁榮的土地
——美麗
而富裕——
這是被謀殺的詩人的土地……
不過呢,詩會涌現,在暗地里
壓迫我,把我撕成
碎片。在那里,遵循著
傳統,收割者揮舞著
陽光的鐮刀。“你
還活著!”——而鷹受傷了,狼
搜尋著
傷口。
這是我的土地!
這是在我深處的土地!
在我的無眠的夜晚
地球在尖叫。
我的血液之河騷動著
沖走了
我心靈的堤岸
而我
學會了
在這片被謀殺的詩人的土地上
如何寫詩。
保加利亞大詩人柳波密和·雷夫切夫(LyubomirLevchev)對詩歌抱有某種古典主義的觀念和情懷,他賜予詩人的土地處于北極圈和熱帶之間,也就是說冷和熱之間,理性與激情之間。溫帶地區具有最好的氣候,因此那片土地是美麗富饒的。如果說那片土地不屬于詩人,或者,本來屬于詩人,后來又被剝奪了,詩人之被殺顯得更加符合日常邏輯。但問題是:這片土地既然屬于詩人,而且又那么好,詩人何故被殺害呢?那殺害詩人的到底是誰呢?“收割者揮舞著/陽光的鐮刀”。陽光,一般被認為是美好的事物,是跟雨露一起化育生命的。但在詩人手里,它成了鐮刀,成了戕害生命的東西。或許,在熱帶地區,由于陽光太暴烈,的確有害。但作者在這里沒有明說這是熱帶的陽光,而是泛指,它可能屬于寒帶,也可能屬于溫帶。那么好,我們應該得出這樣的推論:美好的東西同時也可能會傷害我們。對詩人來說,最美好的東西莫過于詩歌了吧?但雷夫切夫認為,詩人可能或者必須死于詩,詩人被置之死地而后詩生,詩人被害而詩涌現,詩“在暗地里壓迫我,把我撕成碎片”。詩和詩人之間的關系是相生相克。詩是神,也是鬼,是吸血鬼,一直在吸詩人的血,吃詩人的肉,詩人被吃剩下一副骨架,就要被“詩鬼”拋棄。
我曾經寫文章闡述過類似的看法,對清初大詩人、史學家趙翼提出來的“國家不幸詩人幸”這個話題進行糾正和發揮。我的觀點是:國家幸時——以美麗富饒的土地為象征,詩人未必幸;國家不幸時,詩人未必幸,更可能是不幸;國家不幸時,真正幸的不是詩人,而是詩!吊詭的是,詩人對于自己如此慘死于詩的命運,并沒有怨天尤人,呼天搶地,而是主動接受,勇于承擔,去做殉詩者。為了詩歌,他們寧愿把鬼當作神,頂禮膜拜,肝腦涂地,在所不辭。“鷹受傷了,狼搜尋著傷口”。鷹和狼一般都被認為是加害者,那么,它們之所以受傷,是因為它們自己愿意受傷,自討苦吃,自作自受。這首詩也隱含著《詩人之戀》一開篇就提出來的苦難主題。在雷夫切夫看來,苦難有時并不是外在強加的,而是自我開拓和自我探索過程中的產物:“我的血液之河騷動著/沖走了/我心靈的堤岸”。浪漫主義詩人雨果說,世界上比大海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心靈。但事實上,人的心靈沒有那么大,所以我們需要不斷拓展我們心靈的邊界,去容納更多的事物;我們要容納的是更多外在的事物,但卻不能依賴那些外在的事物來幫我們拓展,而要靠我們自己內在的能量和力量,不惜去消耗這些能量和力量。寫詩是拓展心靈空間的一個獨特而有效的手段,必然要消耗我們自己的生命。
關于密碼,由紀伯倫
〔馬其頓〕妮可莉娜·安多娃北塔/譯
互聯網上有篇文章,說
許多夫婦都知道
對方的電子郵箱密碼
是相互主動告知的
作為信任和安全的標志
我不像紀伯倫那么
睿智
我要加上這樣幾句:
互發郵件
但不要泄露密碼
人與地相依為命
但各自保守初始的秘密
妮可莉娜·安多娃(NikolinaAndova)是馬其頓生于1970年代的女詩人,獲得了第52屆斯特魯加詩歌節的另一個獎項——“斯特魯加之橋獎”。她的這首詩題目有點怪。紀伯倫就是黎巴嫩藝術家、詩人、作家、哲學家卡里·紀伯倫(KhalilGibran),問題是:他從未曾使用過“密碼”這個詞。那么,安多娃為何要在密碼后面加上紀伯倫?
這是一首日常生活敘述的詩。從1990年代以來,中外很多詩人都注重日常生活,從日常生活擷取素材,抓取靈感,甚至獲取語言資源。但安多娃的寫法還是有點新意。這首詩開始于一個日常生活的細節:許多夫婦在網上注冊郵箱時都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密碼,說白了,就是:夫妻共享密碼。密碼成了夫妻關系中信任和安全的象征。作者在敘述了這一關于電子郵箱密碼的普遍現象之后,不是自己直接發表看法,而是通過仿寫紀伯倫的詩句說出來。她很老實,在自己的文本之前,先引用了紀伯倫《先知》一書中關于婚姻的詩的一部分,那首詩非常著名,她引用的是中間的部分(她分成了八行):
彼此斟滿了杯,
卻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飲。
彼此遞贈著面包,
卻不要在同一塊上取食。
快樂地在一處舞唱,
卻仍讓彼此靜獨,
連琴上的那些弦子也是單獨的,
雖然它們在同一的音調中顫動。
安多娃的最后四句就是對這八行的仿寫。她認為,密碼畢竟屬于秘密的一種,不應該告訴任何別人,包括自己親密的愛人。這首詩的用意其實很簡單,就是她反對夫妻間共享密碼。但她的靈感來源,或者說她組織詩歌結構的方式,值得我們一說。前半首是“關于密碼”的日常敘述,平淡無奇;后面緊接著,如果是談她個人的想法,完全用她自己的語言,那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后半首是對前半首的一個形而上的提升,本詩可貴之處就在這里。前半首說事,后半首說理。她之所以能說理,而且這理還不是簡單的批判和否定,而具有更加普世的價值,是因為得益于她聯想到了紀伯倫的那首名作,尤其是那首名作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架構。是紀伯倫給了她理論化的支撐。
題目中逗號前后的兩半內容正好對應于這首詩整個內容的前后兩半。密碼和紀伯倫之間的關系就是由作者對紀伯倫詩句的學習構建起來的,甚至我們可以推測,她的靈感的一部分就是來自紀伯倫。我曾經想把題目改譯成《關于密碼,仿紀伯倫》,但后來還是決定保持《關于密碼,由紀伯倫》這樣似非而是的樣子。作者把自己的詩和紀伯倫的原作放在同一個空間,使兩者之間產生明顯的互文作用。
預先警告
〔馬其頓〕米洛斯·林德羅北塔/譯
世人啜飲的器皿
會發出沉郁的回響
先是雷聲大作
然后是無情的回聲
時日的刀刃
將削下高端
切開樹皮
劃裂大地。
隨后圣靈將流下
沉重的淚滴
圣父將派來
他的兒子——詞語——
藍色的詞語。
這將是一個預先警告
是人們很久前就預料到的可怕的警告:
最終你會看到,那筆債啊,
算到最后,事實上,
哪怕不按時,
早晚都得
由我們
徹底——還清!
馬其頓詩人米洛斯·林德羅(MilosLindro)的《預先警告》是一首具有宗教情懷的詩,其思想源頭應該是人類因為原罪而必須經過自己的補償行為得到救贖。有意思的是,林德羅把“罪”置換成了“債”,詩的最后一部分說:“那筆債啊,/算到最后,事實上,/哪怕不按時,/早晚都得/由我們/徹底——還清!”人類對上帝犯下原罪,就像是欠了他一筆債,很難還清,但遲早得還清,哪怕是到了生命終點的時候才能還清,否則,死后也不能升入天堂,見不了上帝,到死也得不到解脫和輕松。這是對宗教原罪觀念的一個改寫。這種改寫后面是否隱含著這一疑問:將罪置換為債,是把罪現實化甚至貨幣化,似乎更容易償還了,但即便償還了,我們是否真的就無罪了,是否真的能得到拯救?世俗意義上的罪可以分為刑事和民事兩部分,民事部分可以置換為債,通過賠償得到解決,但刑事部分如果也被錢買了,那么,法律就成了金錢的奴隸。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或者整個的罪都置換成債。
這首詩的另一處改寫更有意思。基督教有所謂三位一體的概念,即圣靈、圣父和圣子。這首詩中間幾行說:“隨后圣靈將流下/沉重的淚滴/圣父將派來/他的兒子——詞語——/藍色的詞語。”此間有兩個問題:1.為何“圣子”被置換成了“詞語”?2.為何這個詞語是藍色的?
圣子者上帝之子也,但不像上帝那么抽象,因為他的母親瑪利亞是普通的人間女子,其原型耶穌也就隨母親道成肉身,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再后來,人們用象征手法,把他的形象“去生命化”,說紅酒是他的血,面包是他的肉。不過,紅酒和面包雖然不是生物,但畢竟還是具象的。再后來,人們進一步把圣子形象抽象化、符號化,變成了一個詞語——一個詞語而已。在林德羅看來,圣子形象的演變史無疑是漸行漸下的。
在詩的原文中,那個“詞語”是大寫的,但較之耶穌原本該有的形象,無疑是被矮化了甚至抽空了。因此,作者用“藍色”來修飾那個詞語——作為圣子形象的替代物。大家都知道,在西方語境中,“藍色”代表的是“憂郁”、“沮喪”甚至是“下流”。話題一下子就沉重起來。其實,詩的一開頭,就奠定了這一沉重的基調,作者用了“bluishly”(沉郁)一詞:“世人啜飲的器皿/會發出沉郁的回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欠的債不僅屬于圣父,也屬于圣子,是我們在不斷地弱化甚至丑化圣子的形象,我們必須要對此付出代價。作者所要預先警告的,就是這點。
矮鹿
〔科索沃〕娜伊姆·貝奇拉耶北塔/譯
在適合于
盜獵者的森林
你是我的一頭
小小的矮鹿
你甚至還不知道如何祈禱,好讓
盜獵者改變主意
你也不知道如何拐向容易逃跑的一邊
你可以再流浪
幾個星期
逃生
就是
為生而逃嘛
你會生我的氣
如果我稱呼你
愚蠢的矮鹿
那是因為你相信:
獵槍是溫柔的
森林在春天總會生長
你正在變成珍稀動物
不要猶豫了啊,我的小可愛,
你得改變槍筒的念頭
像狐貍那樣地活一天
只要你忘記這世上還有許多惡行
那些打在你身上的主意就不會消失
在動物地圖集里
我將看到一個例證:
曾經一度有過一種美麗的動物
叫做矮鹿
女詩人娜伊姆·貝奇拉耶(NaimeBeqiraj)的這首詩探討的是生態問題。作品通篇以第二人稱抒寫,直接稱矮鹿為你,而不是它,沒有冷冰冰地把動物視為他者,“你是我的一頭/小小的矮鹿”,如果中間沒有加“我的”,是非常平淡的敘述語氣,加了“我的”一詞,顯得溫情脈脈。“我”和“你”之間的距離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可以說是親密無間。但文本的形式又不是對話,而是“我”對“你”的談話。因為關系親密,所以“我”和“你”無話不談,甚至“我”對“你”哀其不幸,怒其不智。矮鹿又稱“狍子”,在中國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在動物權利保護觀念更強的歐洲,肯定被認為是更珍貴的動物。對這種動物的獵殺是非法的。但獵殺者并不缺乏,在他們的槍口下,矮鹿要死里逃生。但是,作者又認為,矮鹿是呆笨的,因為它們居然認為獵槍是溫柔的。她希望矮鹿能學得聰明點,像狐貍,哪怕只是一天。不過,總的來說,作者是非常喜歡矮鹿的,無論是哀其不幸,還是怒其不智,都是因為愛。這份愛不會因為矮鹿的生或死而有所變化。從詩的最后,我們得知,矮鹿被獵殺了,或者說,作為一個物種滅絕了。事實上,這個物種當然沒有被獵殺殆盡,現在還有不少存活的野生矮鹿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問題是,在這里,作者沒有用虛擬語氣,而是直接說:“曾經一度有過一種美麗的動物/叫做矮鹿”。因此,整首詩就像是一篇悼念文字。在生態主題下,也許會有很多詩人憐憫矮鹿,也有很多詩人譴責盜獵,但在愛護的大前提下,對“矮鹿”這一受害者形象稍有微詞,是比較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