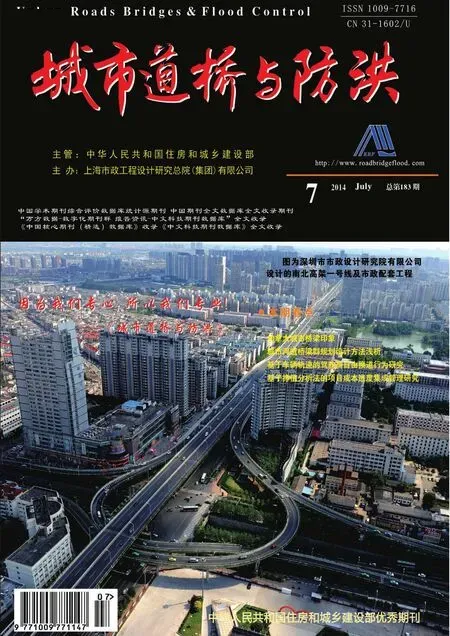兩種濕地植物枯落物還田分解速率對典型氣候環境因子變化的響應
張 寧,張艷楠
(1.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 200092;2.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上海市 200092)
0 前言
土壤碳庫是地球表層系統中最大的碳儲庫,其中土壤有機碳儲量的變化對全球碳循環具有重要的意義[1]。植被通過光合作用固定大氣中的CO2,其植物枯落物是土壤有機碳庫的主要碳輸入途徑,而枯落物的分解過程則是土壤釋放CO2的主要方式,所以植物枯落物的降解是全球碳循環的一個關鍵過程[2]。深入研究枯落物還土的降解性質,以及環境因素對枯落物分解的影響對于人們更好地保護土壤碳庫及其生態功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濕地生態系統一方面具有較高的初級生產力,另一方面,由于長期處于水淹狀態,所以導致其中微生物活性相對較弱,來自土壤呼吸的CO2釋放量較少,因此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碳匯”[3]。唐玉姝的研究發現,長江口地區蘆葦和互花米草具有較高的生物量,但是蘆葦濕地的土壤呼吸較互花米草更低,這可能是由于在原位蘆葦秸稈比米草秸稈更難降解[4]。但是由于氣候環境的日益變化,其對濕地生態系統也會帶來不可忽略的影響。大氣CO2濃度增加將引起溫室效應,影響地球表面其它環境因子如溫度升高等;同時,城市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海中,使營養物質在水體中富集,導致沿海水域富營養化加劇[5]。這些氣候/環境因素的變化將導致濕地水土環境質量問題,并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植物枯落物的分解速率。所以有必要分析濕地植物枯落物分解對于氣候環境變化的響應,確定未來氣候環境變化下的高碳匯植物類型,優化濕地系統的“碳匯”功能。
因此,在研究中,采用人工氣候室調控氣候環境變化因子,包括溫度升高、大氣中CO2濃度增加、海水富營養化等,選取了九段沙濕地生態系統的兩種典型植物蘆葦和互花米草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溫度升高、大氣中CO2濃度增加、海水富營養化等因子單獨作用和共同作用下對植物枯落物還田后分解過程的影響,以期預測未來氣候環境變化背景下九段沙濕地生態系統中典型植被的分解特性,為提高土壤有機碳保留能力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設計
因溫度升高與CO2濃度增加引起的溫室效用往往相互關聯,因此將兩者作為一因素,加上海水富營養化帶來的N、P濃度增加因素,設計2因素2水平試驗如表1所列。

表1 試驗設計一覽表
根據該設計,在室內控制條件下進行模擬九段沙生態系統植物枯落物還田后的分解試驗,設置施氮、磷營養元素和增溫、CO2倍增2種單因素處理。其中,增施氮、磷模擬九段沙濕地系統中水體富營養化加劇因子,增溫、CO2倍增模擬全球氣候變化因子。同時,設置對照CK及兩因素共同作用處理。
采用2臺寧波海曙賽福儀器廠生產CO2人工培養箱PRX-1000C對溫度、濕度、CO2濃度、光照、晝夜時間等環境條件進行控制。且根據實驗需要,將人工氣候室內分成2個小格,在每個小格中放入一個48 cm×48 cm×30 cm的 P VC箱,其隔板上有滲水孔25個(直徑2 cm),側面有通氣孔和排水孔各1個(直徑3 cm)。每個箱中分別裝入近100 kg混合均勻的土壤,箱底隔板上層鋪有砂石混合物1 cm。圖1為PVC箱示意圖。

圖1 PVC箱示意圖
于2010年11月,在九段沙濕地各植被為優勢群落的樣點,分別采集蘆葦和互花米草兩種枯落物,經清洗、70℃烘干至恒量,剪切成20 cm左右,分裝等量于分解袋中。并于2011年11月,將預處理后的分解袋埋入各PVC箱內,每個PVC箱內兩種植物各兩袋共4袋,具體布置見圖2所示。
圖中N代表無機氮;P代表無機磷;T代表溫度;+代表因素高水平處理;-代表因素低水平處理。
1.2 運行設置
按照上海市近十年來的氣象資料,核算每季度的平均氣溫,晝夜溫差設定為5℃,溫度增高組設定增高幅度為4℃(見表2);CO2低水平設定為350 ppm,高水平設定為倍增的700 ppm。
各PVC箱內每天加入人工配置海水模擬九段沙濕地系統中的潮汐海水沖刷,其中低N、P水平按照九段沙附近海域中海水中的數據為參考,測得其各項指標分別為:pH為7.78,含鹽量為3.40 g/L,無機氮的含量為0.401 mg/L,速效磷的含量為0.048 mg/L。人工配置海水為65 g海水鹽加入15L自來水中,經測定pH為7.61,含鹽量為3.03 g/L,無機氮含量為0.404 mg/L,速效磷的含量為0.054 mg/L。經方差檢驗LSD多重比較,兩者并無顯著性差異(P>0.05)。為模擬海水富營養化,向配置的人工海水中加入無機氮、無機磷,按照海水水質標準中四類水水質,往16 L人工配置海水中(無機氮污染低水平)分別加入硝酸鈉0.91 g,氯化銨0.57 g和磷酸二氫鉀0.1 g作污染源,經測定此時海水中無機氮的含量為1.309 mg/L,速效磷的含量為0.236 mg/L,遠超過了海洋四類水標準,海水富營養化標準[6]。
人工氣候室于2011年4月開始,進行條件控制與調整,待穩定后,11月正式運行,并將兩種植物枯落物分解袋埋入土壤。記錄人工氣候室條件,調控各參數;每天向各PVC箱內加入人工配置海水和富營養化海水,并定時放水,保持各箱內滯水時間一致。此外,按照季節變化調控各時間段的人工氣候室運行參數(見表2)。

表2 人工氣候室運行參數一覽表
1.3 樣品采集與分析
于2011年11月將植物枯落物分解袋埋入土壤,并保留部分初始枯落物作為背景值分析,在分解30 d,90 d,180 d,270 d后,取出各植物枯落物分解袋,平行樣品兩袋。用自來水清洗,再用蒸餾水洗凈,置于70℃烘箱內24 h后,稱重并粉碎、過60目篩。
植物枯落物C、N元素含量采用德國Elementar公司Vario EL III元素分析測定。稱取5-10 mg過60目篩植物顆粒進行包樣后直接上樣檢測。碳的分析精度為±2%,氮的為±8%。
1.4 數據分析
采用SPSS 16.0統計軟件對所測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Pearson相關性分析,確定不同因子之間的相關性。Ducan多重比較(P=0.05或0.01)分析不同植物枯落物分解過程中相關指標的顯著差異。
采用NAI值來表示枯落物分解過程中各主要元素的積累或釋放,計算方法如下式[7]:

式中,Mt為枯落物在t時刻的干物質重量,g;Xt為t時刻枯落物中元素的濃度;M0為枯落物的初始干物質重量,g;X0為枯落物中元素的初始濃度。NAI<100%,說明枯落物分解過程中元素發生了凈釋放;NAI>100%,說明枯落物分解過程中元素發生了凈積累。此方法較為直觀地描述了枯落物分解過程中營養元素的變化動態。
2 結果與討論
2.1 CO2濃度增加(溫度升高)和海水富營養化單獨作用下對兩種濕地植物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
CO2濃度增加往往引起溫室效應,導致氣候變暖,因此將兩者合并,作為氣候影響因子,加上海水水體富營養化,分析兩個單因子升高對植物枯落物還土后分解過程的影響(見圖3)。由圖3可以看出,兩種植物枯落物的分解過程均受到了單因子變化的影響,總體而言,溫度和CO2濃度升高單因子作用和海水富營養化單因子作用均促進了枯落物的分解,在分解前期(0~180d)海水富營養化的促進效應更為明顯,但是在180 d后,溫度和CO2濃度升高因子對枯落物分解過程的促進效應更為強烈。尤其是對于互花米草的分解過程,單因子升高在分解后期(180d后)更為顯著,明顯地促進了它們的分解,經過270d的分解后,較對照組(CK)質量損失率提高了27.02%~40.62%。

圖3 單因素變化對濕地植物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曲線圖
多數研究結果表明,溫度升高促進了枯落物的分解過程,因為枯落物的分解是一系列物理、化學和生物作用過程的綜合結果,溫度升高一般促進了這些過程的進行。Jenny等分析不同溫帶和熱帶地區,因緯度不同帶來的溫度差異,對于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發現熱帶地區植物枯落物分解速率明顯快于溫帶地區[8]。溫度升高促進了營養元素的礦化,提高了土壤養分有效性及微生物的活性,又促進了枯落物的分解,但是溫度對于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各種直接和間接作用并不都表現為正效應,溫度升高改變了系統的水熱條件,使得地面蒸散作用增加,土壤含水率減少,過于干燥的環境反而抑制了枯落物的分解。因此,溫度升高對于枯落物的分解過程影響,因氣候環境、枯落物基質的不同,作用效應也會存在差異性,而這必將會引起植物群落格局的變化。
海水的潮汐作用,不僅對于濱海濕地地貌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海水中的營養元素也是濕地系統主要的外源營養元素來源。富營養化的海水中,N、P元素濃度普遍較高,營養元素的輸入一般促進了枯落物的分解,這可能是因為營養元素增加,一方面改變了分解生物有機體的組成,促進了蔗糖酶、淀粉酶等和有機質分解利用有關的各種酶活活性[9];另一方面,提高土壤輕組分有機碳的輸入比例,從而間接調控微生物群落組成,影響枯落物分解[10]。Szumigalski and Bayley通過對加拿大泥炭地的研究發現分解速率與水中銨態氮濃度和可溶性磷含量有關,增加氮磷輸入可以增加枯落物分解速率[11],其結果與本文所介紹的研究結果一致。
植物枯落物中的碳元素動態變化與系統中的碳循環過程有關,氮元素是枯落物分解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子,因此分析枯落物分解過程中這兩元素的動態變化(見圖4)。由圖4可知,環境因子的變化,對于濕地植物枯落物還土后分解過程中C、N元素的動態變化過程存在影響。不同的環境因素對于植物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隨著枯落物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對于蘆葦植物枯落物,溫度升高和N、P元素濃度增加均促進了其中C元素的流失,且影響效果基本一致,溫度升高和N、P元素濃度增加作用下的枯落物經過270 d的分解后,C的NAI值分別為10.7%和10.8%,而顯著低于CK組中植物枯落物中C的NAI值30.2%。對于米草植物枯落物,N、P元素濃度增加因素的作用加速了其中C元素的釋放,但是溫度和CO2濃度升高作用卻減緩了其中C元素的釋放,這是否會影響未來氣候環境下其成為高碳匯植物的潛力,有待進一步驗證。

圖4 單因素變化對濕地植物枯落物中C、N元素含量的影響曲線圖
雖然無論何種環境條件下,兩種植物枯落物中N元素均呈現前期釋放,中期積累之后又釋放的趨勢,但是不同的環境因子作用下,枯落物中N元素的變化幅度存在差異。N、P元素濃度增加作用對于N元素動態變化趨勢影響更為顯著,溫度升高對于植物枯落物分解前期作用并不顯著,后期(180 d后)N元素的變化作用較為明顯。對于不同植物枯落物,影響效應也有差異,溫度升高和N、P元素濃度增加作用促進了蘆葦枯落物分解后期的N元素釋放,但是卻促進了米草分解后期的N元素積累。根據前期研究結果,枯落物中N元素含量與其分解速率存在正相關性[12],所以米草后期枯落物中N元素的積累可能會促進枯落物的進一步分解。
2.2 雙因子共同作用對九段沙濕地植物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
實際環境中,環境因子的變化并不是獨立作用于枯落物分解,而是表現為綜合作用,因此研究溫度及CO2濃度升高氣候因子和海水富營養化因子共同作用,對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見圖5)。由圖5得出,溫度及CO2濃度升高和海水富營養化,對于植物枯落物的分解存在交互作用,與對照組比較,兩因子復合作用促進了還土植物枯落物的分解,但是與單因子作用結果比較,經過270 d的處理后,雖然對分解的中間過程有明顯的增強效果,但最終復合作用的促進效果小于單因子作用結果。這說明了各因子綜合作用對于枯落物分解過程影響的復雜性。不同植物枯落物對于雙因子的反饋效應不同,互花米草最為明顯,經過270 d的分解后,剩余質量顯著少于對照樣,僅為對照樣剩余量的75.9%。

圖5 雙因素對濕地植物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影響曲線圖
在大氣中CO2濃度升高的背景下,有必要了解在未來氣候環境變化作用下四種植物枯落還土后,釋放的C元素動態,以期確定各植物在“碳匯”能力中的排序。有研究表明,枯落物中的N元素變化對于其分解過程有重要影響[13],因此需要分析蘆葦和互花米草中碳、氮元素動態變化對于雙因子作用的響應。研究結果發現與單因素作用結果基本類似,溫度及CO2濃度升高和海水富營養化兩因子升高的交互作用,對于植物枯落物中C、N元素的動態變化過程存在影響(見表3)。兩因子升高的交互作用,促進了還土后蘆葦枯落物中C元素的釋放,經過270 d分解后,蘆葦中C元素剩余量僅為對照組中剩余量的48.5%,但是卻減緩了互花米草后期C元素的釋放,使得經過270 d分解后,雙因子升高作用下互花米草枯落物中C元素含量超過了對照組。雙因子升高共同作用對枯落物中N元素的變化過程影響較為復雜,整體而言,雙因子交互作用促進了蘆葦秸稈中N元素的釋放,雖促進了互花米草分解前期的N元素釋放,卻促進了后期N元素的積累。N元素在枯落物的分解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14],N含量的積累可能會使得互花米草后期的分解過程加快。

表3 雙因素變化對濕地植物枯落物中C、N元素含量的影響一覽表
因此,溫度及CO2濃度升高和海水富營養化等單因子作用均不同程度地促進了濕地植物枯落物的分解,加快了枯落物中C元素的流失。雙因子共同作用效應小于單因子作用結果,這說明了枯落物分解過程的復雜性。互花米草相較蘆葦對于氣候變化的響應更為明顯,雖然質量損失在溫度及CO2濃度升高單因子作用下顯著加快,其中的C元素損失速率卻有所減緩,可是另一方面,互花米草枯落物中N元素后期出現積累,這又有可能會促進其之后的分解。所以不同植物類型枯落物在氣候環境變化的影響下,其分解過程有無顯著變化,是否會影響未來高碳匯植物的類型,有待更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3 結論
通過人工氣候室調控氣候環境變化因子,包括溫度及大氣中CO2濃度升高、海水富營養化等,分析氣候與環境單因子作用及雙因子共同作用對植物枯落物還田后分解過程的影響,結果發現:
(1)在溫度及CO2濃度升高單因子和海水富營養化單因子作用下,均不同程度地促進了兩種植物枯落物的分解,加快了枯落物中C元素的流失;在分解前期(0~180 d)海水富營養化的促進效應更為明顯,但是在180 d后,溫度和CO2濃度升高因子對枯落物分解過程的促進效應更為強烈。
(2)與單因子作用結果比較,經過270 d的處理后,復合作用效果小于單因子作用結果,這說明了各因子綜合作用對于枯落物分解過程影響的復雜性。
(3)不同濕地植物類型枯落物在氣候環境變化的影響下,其質量損失率有所升高,其中碳元素損失率也有加快,但是互花米草枯落物中的碳后期損失速率有所降低,N含量有所升高,這是否會影響高碳匯植物的類型,有待更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Lal R,2004.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mpact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Science,304(5677):1623-1627.
[2] Davidson E A,Janssens I A,2006.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soil carbon decomposition and feedbacks to climate change.Nature,440(7081):165-173.
[3] Hu,Y,Wang,L,Tang,Y S,et al,2014.Variability i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and activity between coastal and riparian wetland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Potential impacts on carbon sequestration.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70,221-228.
[4] 唐玉姝.九段沙濕地土壤/水體系統碳匯聚能力的空間異質性及其影響因素[D].上海:同濟大學,2011.
[5] 席雪飛.環境變化對九段沙濕地土壤微生物呼吸影響的模擬研究[D].上海:同濟大學,2011.
[6] 劉成,王兆印,何耘,等.上海污水排放口水域水質和底質分析[J].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學報,2003,1(4):275-280.
[7] 楊繼松,劉景雙,于君寶,等.三江平原沼澤濕地枯落物分解及其營養動態[J].生態學報,2006,26(5):1297-1302.
[8] Jenny,H,Gessel,S P,Bingham,F T,1949.Comparative study of decomposition rates of organic matter in temperate and tropical regions.Soil Sciences 68,419-432.
[9] 萬忠梅,宋長春,劉德燕.氮輸入對沼澤濕地小葉章枯落物分解過程中酶活性的影響[J].環境科學學報,2009,29(9):1830-1835.
[10] Mack M C,Schuur E A G,Bret-Harte,M S,et al.Ecosystem carbon storage in arctic tundra reduced by long-term nutrient fertilization.Nature,2004,431(7007):440-443.
[11] Szumigalski A R,Bayley S E.Decomposition along a moderate-rich fen-marsh peatland gradient in boreal Alberta,Canada.Wetlands,1997,17:123-137.
[12] 張艷楠.不同植物枯落物在土壤中的分解特性及其對氣候環境變化的響應[D].上海:同濟大學,2013.
[13] Torreta N K,Takeda H.Carbon and nitrogen dynamics of decomposing leaf litter in a tropical hill evergreen forest.Eur.J.Soil Biol.,1999,35:57-63.
[14] Corteaux M M,Bottner P,Berg B.Litter decomposition,climate and litter quality.Tree,1995,10: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