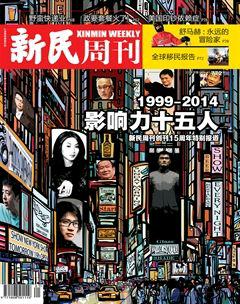洋畫登陸百年風
李超
在上海開埠的語境中,回顧一下西洋畫在上海的登陸,確實也是一件頗有意思的事。20世紀中國油畫的初始,與近代中國西學東漸之風密切相關。其一是新學風氣影響下的師范學堂的圖畫教育和傳播。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以審美書館為中心的活動,倡導“新畫法”,其中的核心是關于西洋畫“臨畫法”向“寫生法”的轉化。二是作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的土山灣畫館出身的西畫人才,運用學得的西畫技藝依附于商業,進行水彩畫、布景畫及廣告畫等新生態繪畫的制作,同時也兼職從事早期的西畫教育。周湘、徐詠清、張聿光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三是清末首批中國留學生,如李叔同等人歸國,在中國城東女學任教,并通過“文美會”等藝術活動,進行西洋畫的教育和傳播。
洋畫運動的開端,始于上世紀10年代初。國內先后出現私立和國立的美術學校,使得初期西畫教育中的臨摹范本的師范化教學模式發生突破。其引進和借鑒國外的教育體系,成為中國早期美術教育的模式之一。20世紀20年代,國立美術教育再次掀起一個高潮,一批留洋的藝術家的努力,融合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使得美術院校成為中國油畫的重要學術基地。美術教育有如“飛鳥”,社團和展覽又似其“兩翼”。其間,以上海為中心,波及北京、廣州、杭州和蘇州等地,先后出現多個西畫團體。20世紀20至30年代,隨著大批在歐洲和日本留學的中國油畫家回國并匯集中國,著名的“洋畫運動”拉開序幕,他們自覺地將西方美術作為文化引進的對象,其以現代美術教育為核心,并通過社團、展覽、美術刊物等一系列藝術活動,大面積地將西方油畫的寫實主義、印象主義和現代主義進行移植和借鑒,并分別制定出相應的融合本土文化,振興中國美術的方案。
從文化意義上看,“洋畫運動”的出現,標志著源于西方的油畫,正式以完整文化形態引進和滲透于中國文化生活之中,而在當時已趨國際化都市的上海,更使油畫的活動和影響具有正規的國際意義。“唯我國畫界之開始洋畫運動,……必端于上海,而無形中上海一向成為洋畫運動的中心”。
晚清學者顧祿《桐橋倚棹錄》中所記的“洋畫”詩,“世間只說佛來西,何物眼云障眼低?畢竟人情皆厭故,又從紙上判華夷。”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晚清中國學界對西洋的認識注入更為復雜豐富的內涵,對于多種舶來品冠以某某“洋”貨之謂,并且產生了“西洋”和“東洋”之說。——這并非僅僅是打開門戶后的地理發現的概念,更主要的是伴隨著洋務思想的興起而形成的文化比較概念,其背后蘊藏著的是民族意識反省自強的精神波動。其中,“洋畫”之說逐漸以較大的比例,出現在晚清以來的出版物及其相關評說之中。當“國畫”和“洋畫”的詞語,在近代中國畫壇出現之時,實際已經表明中國繪畫的內涵突破了傳統的格局,而這種觀念相對應的是,中國傳統繪畫的“重鎮”和西畫東漸“中心”,奇跡般地共存于晚清上海之地。畫家隊伍發生轉化和派生,繪畫的運作機制發生變化,在傳統繪畫以外,出現了多種新生的視覺文化形態和現象,而“洋畫”之謂,即是其中較為通行的概括之一。
上海近代出現的新生態的畫報插圖和月份牌廣告畫,又正是這種“共同體”文化土壤中漸次出現的花果。其中西融合的畫法,又轉而影響已經舶來于滬上的畫種,包括水彩、油畫和石印版畫等。畫法交融的背后,發生著更為繁雜而鮮見的商業文化內容。如果說繁盛的市場是新生型視覺文化的溫床,那么新起的石印技術,則是其中的催化劑,成為畫報插圖和月份牌廣告畫物質技術的前提和保證。洋畫通過大眾傳媒的廣為流通,在中國本土實現了空前的變格。“洋畫紛紜筆墨擬”,由此成為其新生型視覺文化的現象寫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