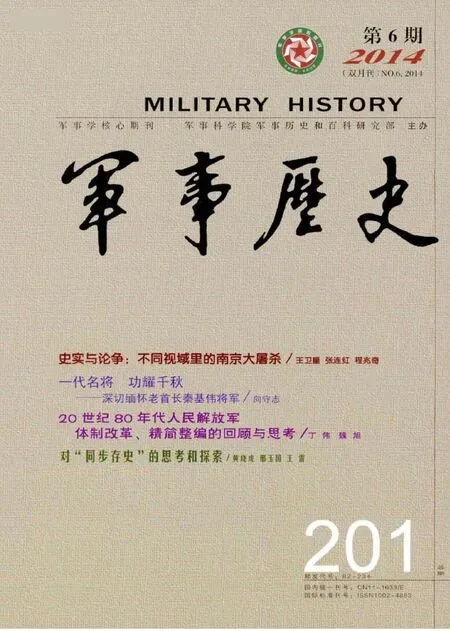史實與論爭:不同視域里的南京大屠殺
□ 王衛星 張連紅 程兆奇
一、日軍在南京的集體、零散屠殺:無可辯駁的歷史證明
【王衛星】日軍在南京的集體和零散屠殺持續了約6個星期,直到1938年1月末才有所緩解。然而,日本總有一些人找出種種“理由”和所謂證據,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不斷深入,中方、日方及第三方的史料陸續被發現,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日本“虛構派”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謬論不攻自破。
(一)攻城戰中的俘虜“處置”
1937年12月10日,日軍向南京發起總攻擊。在進攻南京的過程中,日軍俘獲了大批中國軍人。對于中國戰俘,日軍并沒有按照相關國際法人道地對待,而是“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以實現其圍殲中國軍隊于南京城下的軍事目的。
日軍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一千三百人。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處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個大壕,但很難找到。預定將其分成一兩百人的小隊,領到適當的地方加以處理。”
12月13日,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占領了南京太平門。該聯隊士兵池端正巳回憶:“俘虜很多,繳獲的物品也很多,所以如何處置這些敗殘兵就成了問題。我們部隊人數很少,不足百人,而俘虜那么多,有一千幾百人,無法供他們飯吃。……我們部隊自己吃飯也成問題,就去請示作為上司的師團,師團命令說‘處置掉’。”
日軍第10軍第114師團步兵第127旅團第66聯隊第1大隊,于12月12日在南京中華門外“掃蕩”時俘獲了1500余名俘虜。據該大隊《戰斗詳報》記載,12月13日下午,第1大隊接到聯隊命令:“根據旅團命令,俘虜應全部殺死。”第1大隊“最后決定各中隊(第一、第三、第四中隊)平均分擔處理,即每次從監禁室帶出50人,第一中隊將俘虜帶至露營地南方谷地,第三中隊帶至露營地西南方凹地,第四中隊帶至露營地東南谷地附近,全部用刀刺死。”
日軍對中國戰俘最大規模的屠殺發生在南京北郊幕府山附近的長江邊。12月13日,由日軍第13師團第103旅團長山田栴二率領的山田支隊,攻占了南京烏龍山炮臺和幕府山炮臺等地,捕獲了大批俘虜。15日,山田栴二派人去南京聯系處理俘虜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說全部殺掉。12月16日至18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附近的長江邊屠殺了約2萬名俘虜。
山田支隊步兵第65聯隊第4中隊的宮本省吾少尉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傍晚攻打烏龍山。陣地上并沒有敵軍,俘虜了許多敵殘兵并殺掉了一部分。”在14日的日記中他又記述:“凌晨5時出發,掃蕩敵人殘兵。……傍晚把俘虜押往南京的一個兵營,不料竟有一萬多人。立刻實施了警備。”16日,日軍開始實施大屠殺,將約3000名俘虜押到揚子江邊槍殺。17日,宮本省吾在日記中記述:“傍晚回來,立刻出發加入了對俘虜兵的處決。由于已殺了兩萬多人,士兵殺紅了眼,結果,竟向友軍發難,殺死殺傷友軍多人。我中隊也造成了一死兩傷的損失。”該聯隊第8中隊的遠藤高明少尉在日記中也詳細記錄了屠殺俘虜的經過:12月16日,“俘虜總數有17025人。傍晚,按照軍部命令,把俘虜的三分之一拉到江邊,由第一大隊實施槍殺。正如下達的命令中所說的,即便是一日兩餐的糧食供應,也要一百袋(糧食)。而如今我們士兵都得靠征繳提供給養。因此提供糧食是不可能的。軍部必須采取適當的處置。”17日,“晚上,為了處決剩下的一萬多名俘虜,派出了五名士兵。”
盡管上述記載對俘虜的人數表述不一,但山田支隊在進攻南京的過程中俘獲了大批俘虜并加以屠殺是不爭的事實。從上述日軍屠殺戰俘的史實中可以得出結論,即這些屠殺是根據軍、師團或旅團的命令實施,而不是個別部隊的個別行動。
(二)南京陷落后的搜捕與屠殺
南京陷落時,許多守城中國官兵未及撤離,不得不丟棄武器,換上便衣,進入由留在南京的西方人設立的安全區等地避難。為此,日軍在包括安全區在內的城內各處反復進行搜捕,并采取體貌辨別、親人相認、“良民”登記等多種方式,“甄別”和捕殺中國軍人及疑似軍人的普通平民。凡是手上有老繭、肩上有磨痕的青壯年男子,日軍均認定是“敗殘兵”而遭到捕殺。
日軍搜捕到中國軍人和疑似軍人的青壯年平民后,除就近屠殺外,更多的是押往下關江邊、漢中門、水西門、江東門、玄武湖、古林寺等地進行集體屠殺。其中,下關江邊是日軍集體屠殺最為集中的地區。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士兵高島市良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述:“第一小隊抓到了兩百多名殘兵。他們是不知道南京已經陷落而逃來的吧。我去問大島副官如何處置這些俘虜。大島副官說:‘不管是200還是500,隨便拖到什么地方都殺了!’于是將他們裝入了車站的空置車廂。決定由小隊協助重機槍隊在揚子江邊處理俘虜,……俘虜排成四隊,兩手舉起。我們拉著50人來到江邊。……把人從貨車和倉庫拉出來,共1200人,讓他們面朝江水坐在沒膝蓋的泥土中。命令一下,躲在后面戰壕里的重機槍就一齊開火。他們便像骨牌一樣倒下去,血肉橫飛。跳進河里的數十人被等在棧橋上的輕機槍全部打死,鮮血染紅了泥水。”
南京陷落之初,日軍第9師團步兵第7聯隊是“掃蕩”安全區的部隊之一,該聯隊上等兵井家又一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上午10時出去掃蕩殘敵,繳獲了一門高射炮。下午又出去抓來335名年輕的家伙。抓走了難民中像是敗兵的人。這些人中間也可能確實有軍屬……335名敗兵被帶到揚子江邊,讓其他士兵把他們全槍斃了。”根據該聯隊《戰斗詳報》記載,搜捕期間,該聯隊共“(刺)殺殘敵6670名”。
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斯蒂爾和《紐約時報》記者蒂爾曼·德丁,是僅有的兩位目睹日軍在長江邊屠殺的西方人士。12月15日,經過交涉,斯蒂爾等少數西方記者在日軍當局的允許下離開南京,在下關登上了美國炮艦“瓦胡”號。斯蒂爾通過“瓦胡”號上的報務員,向芝加哥每日新聞社拍發了親眼所見日軍在江邊屠殺的新聞稿。當天,《芝加哥每日新聞》就在頭版以“日軍殺人盈萬——目擊者敘述剛剛陷落的南京城‘地獄般的四天’,馬路上‘積尸高達五英尺’”為題,刊登了斯蒂爾的電訊報道:“我們撤離這座城市時所看到的最后一個景象,是在南京下關江邊,沿著城墻,有一群約300個中國人,正在被集體槍決,而江邊早已‘積尸過膝’。這種瘋狂的場面,在南京陷落后的這幾天,已成為這個城市特有的景象。”
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第3機關槍中隊士兵北山與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記述了漢中門屠殺的情形:“出了漢中門,去征繳菜葉、水牛。我們到的地方死人堆積如山,總數有500多,被堆在一起殺害了。其中主要是軍人,也有穿著如一般百姓的死尸。”日軍步兵第20聯隊上等兵增田六助在其手記中記述:“第二天(14日),要去國際委員會設立的難民區掃蕩。數萬殘兵一直誓死抵抗到昨日,但被四面八方包圍后,他們一個也沒跑掉,結果全部逃進了這個難民區。今天我們即使撥開草叢,也非要把他們搜出來不可,為陣亡戰友報仇。我們分成小隊,各自挨家挨戶搜索。每家的男人都受到我們的盤問。”
1938年任華中派遣軍第11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在戰時寫下的陣中感想錄中記述說:“派遣軍前線部隊一直以給養困難為借口,大批處死俘虜,已成惡習。南京戰役時,大屠殺的人數多達四五萬之多,對市民進行掠奪、強奸的也大有其人。”從岡村寧次的“感想”中不難看出,屠殺俘虜并不是日軍部隊的個別現象,而是一線部隊普遍存在的“惡習”。
(三)隨意的零散屠殺
除了大規模集體屠殺外,日軍還放任士兵三五成群在城內外四處游蕩,濫殺無辜,零散屠殺時有發生。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述:“今天中午高山劍士來訪,當時恰有七名俘虜,遂令其試斬。還令其用我的軍刀試斬,他竟出色地砍下兩顆頭顱。”日軍步兵第33聯隊士兵松田五郎也回憶說:12月11日,“一個士兵抓住了一個俘虜,說:‘誰來殺他?’說著就在我邊上舉起長刀朝脖子砍去,結果因為砍在了骨頭上,所以沒有砍下來,于是他就把人往死里打,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人給殺了。”
南京陷落時,許多市民進入國際安全區避難,但在安全區外,仍有一些市民因各種原因在家中居住。日軍占領南京后,對城區進行反復“掃蕩”,并隨意屠殺平民。
抗戰勝利后,南京市民紛紛呈文國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痛陳日軍在南京的屠殺暴行。張施氏1945年9月26日在致南京市長馬超俊的呈文中稱:“竊民人張施氏,江蘇人,年四十歲,居住馬臺坊拾貳號門牌,于民國二十六年,因民夫張萬義,年四十四歲,彼時日軍進城事變緊急之時,隨同妻女連家五口往山西路美國保護難民區避難,走至半途忽有日兵拖夫,民夫那時即被他拖去至中央門,因慢行一步被日兵一槍打死。”
夏淑琴一家的遭遇是日軍零散屠殺的典型案例。夏淑琴證實說:“12月13日上午,一隊日本兵(約有30人)來到我家門前敲門。剛剛打開門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槍殺。我父親看到這個情況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懇求他們不要殺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槍打死。母親嚇得抱起1歲的小妹妹躲到一張桌子下面,被日本兵從桌子下面拖出來,日本兵從母親手中奪過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著他們扒光了母親的衣服,幾個日本兵對母親進行了輪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殺死,并在她下身里塞進一只瓶子。后來,幾個日本兵闖進隔壁房間,那里還有外祖父、外祖母及兩個姐姐。日本兵要強奸兩個姐姐,外祖母拼命護著她們,也慘遭槍殺。”
時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的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在致妻子的信中寫道:“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只有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堪與比擬。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屠殺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尸體。”
面對日軍的屠殺暴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西方人士不斷致信日本大使館官員,抗議日軍的暴行,要求日軍停止屠殺。但是,這些西方人士的抗議,并未能制止日軍的暴行。
二、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日軍“慰安婦”制度:西方傳教士的記錄與批判
【張連紅】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不僅肆無忌憚地強奸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女,而且為了防止性病蔓延開始在軍中大規模推行“慰安婦”制度。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有20余人,他們耳聞目睹了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歷史事實,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書信日記,揭示了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歷史真相。
(一)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方式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西方傳教士人身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盡管他們無法了解日軍占領南京所發生暴行特別是推行“慰安婦”制度的全貌,但僅就他們所留傳下來的書信日記,我們大概可以發現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幾種方式:
一是日軍通過大肆搶掠強迫中國婦女充當臨時慰安所中的“慰安婦”。收容婦女難民的金陵女子大學難民所的負責人明妮·魏特琳女士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載:“昨天,30名女學生在語言學校被抓走,今天,我聽到了數十起有關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慘遭遇,其中一位女孩僅12歲。”第二天,魏特琳的難民所也不幸遭到日軍對年輕婦女的掠奪。當晚,日軍以搜查便衣兵為借口,將魏特琳等外國人控制在前門口,讓數名士兵入校園里挑選婦女,然后從后門偷偷帶走。這一次日本人共搶走12名年輕姑娘。
當時南京安全區所報告的日軍暴行幾乎天天都有大量的案例。例如:“12月15日,日本兵闖入漢口路某宅,強奸一個少婦,并綁去三個女人。”“12月16日,日本兵架去陸軍大學內的七個姑娘,從十六歲到二十一歲,五個釋放回家。據十八日所接報告,她們每人每天被奸污六七次之多。”“12月17日,日本兵從陸軍大學架去南京青年會總干事某君家內的三個姑娘,她們本來是住在陰陽營七號的,為安全起見,才遷往陸軍大學,日本兵把她們綁到國府路,加以奸污,于半夜間釋回。”“12月23日下午8時15分,七個日本兵綁去四個姑娘。”
實際上,到了南京大屠殺后期,日軍到處搜捕婦女的暴行一直沒有停止。約翰·馬吉在1938年1月30日致夫人的信中說:“就在今天(也許是昨天),那位不愿為日本人做事而被抓走殺害的學生的年輕妻子以為現在安全了,到安全區外的明德中學買些東西,這時一輛卡車在她身旁停下,把她抓上去,車上還有其他20多名婦女,她們被帶到城南的一所房子里,那兒有日本軍官,她們將供他們‘使用’。”
為了能夠挑選年輕貌美的女性充當“慰安婦”,日軍還借婦女難民登記之機進行強行搜捕。時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日本人命令每一個難民都必須登記,登記必須在今后的10天內完成。……有一大批年輕姑娘也被挑選了出來,為的是建一個大規模的士兵妓院。”
二是有組織地到各大難民所強行征召。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軍專程到金陵女子大學難民所,向魏特琳提出要挑選100名妓女到慰安所去。魏特琳詳細記錄了當天的經過:“10點,我被叫到我的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出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后,我們允許他們挑選,在這期間,這位顧問坐在我的辦公室里。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于找到了21人。”
同時,日軍還強迫“南京自治委員會”設立為日軍服務的“慰安所”,到各難民所招募“妓女”,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史邁士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自治政府委員會’的第一職責,在日本人12月22日召集之時,就是為日本軍隊建立三家妓院。”24日,史邁士記載道:“紅卍字會正著手和日本人一起建慰安所,以滿足日本士兵和軍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戶!上周六貝德士就暗示過此事,當時林查理吃驚不淺。許先生(按:指許傳音)說他們準備建兩個分部:一個在鼓樓火車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一個在新街口以南供軍官使用,全是營業性的。”
三是日軍通過招募洗衣工等謊言,欺騙中國婦女而被迫淪為“慰安婦”。如鼓樓醫院外科的威爾遜醫生記載,在1937年12月31日,有6名中國婦女“被從難民營里帶出去,詭稱讓她們為幾名軍官洗衣服。……在白天她們洗衣服,到了晚上她們就被強奸了。她們中的五個每晚要接受10到20次的凌辱,而那第六個因為年輕漂亮要接受40次左右的蹂躪。”
(二)“慰安婦”的悲慘生活
在日軍占領南京初期,“慰安婦”遭受非人待遇,為了不讓她們逃跑,不給她們衣服穿,每人每天要遭到十數次乃至數十次的輪奸。威爾遜醫生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記中說:“兩天前我接待了一名病人,她22歲,結婚4年了。她和其丈夫在日本人進城那天進了安全區。她的丈夫當晚就被抓走了,再也沒看見。她那天晚上也被抓走,帶到了城南的某個營房,在那兒她每天要被強奸十幾次,一共呆了38天。到此時,她已經身患兩邊化膿性腹股溝腺炎、列性淋病和大面積陰道腫大性潰瘍,因此她就被送出來了,因為沒用了。”
約翰·馬吉曾拍攝到一名15歲被強迫充當“慰安婦”的女孩子的悲慘遭遇,該影片是馬吉所拍影片中的7號片,其內容如下:“一名15歲的姑娘站在教會醫院的汽車旁邊,她乘這輛車剛到醫院。她的父親Yu Wen-hua在蕪湖有一家店鋪。一些日本兵闖入他家翻找值錢的物品。他們把住宅和店鋪都搶劫了。姑娘的哥哥在一邊幫助他的父親,他和當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受過軍訓并有一套軍裝。日本兵發現了這些就說他是個士兵。據姑娘講,日本兵想砍掉他的腦袋,要他跪下,但他拒絕了,因此被殺害。她父母跪在日本兵跟前,乞求他們饒了孩子們的性命。然后這群日本兵試圖強奸姑娘的嫂子,她是一名受過訓練的護士,她堅決不從,他們就把她殺了。他們又要強奸她大姐,她也不從。然后,在她父母跪下乞求時,日本兵把他們也殺了。全都是用刺刀刺死。父母臨死之前告訴她女兒,日本兵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這位姑娘已昏了過去,日本兵把她捆起來帶走。到了另一個地方,她蘇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地板上,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已被強奸。她發現她是在一棟樓房的二樓,這座房子現在是座兵營,有200~300名士兵。樓里有許多妓女,她們很自由,待遇也不錯。也有許多像她這樣的良家婦女,有的來自南京,有的來自蕪湖或其他地方;她不知道這樣的人究竟有多少,因為她們都像她一樣被鎖在房間里,而且她們的衣服也都被拿走。她認識的一個和她同時從蕪湖抓來的女孩子自殺了,她還聽說其他人也有自殺的。日本兵想強奸她,她拒絕了,因此挨了耳光。她每天要被強奸兩到三次,這樣一直持續了一個半月。當她病得很厲害時,日本兵就不靠近她了。她病了一個月,這期間她經常哭泣。一天,一位會講中文的軍官進了她房間問她為什么哭。她把她的遭遇告訴這位軍官后,軍官用汽車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門釋放了她,并在一張紙上給她寫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幾個字,這是一所著名的美國教會辦的女子學院,在最危險時期曾保護了1萬名婦女。這個女孩子病得太厲害,第一天連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都去不了,途中在一家中國人的房子歇腳。第二天,她終于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然后被帶到了教會醫院。”
上述馬吉所拍攝到的這位姑娘最后得了十分嚴重的性病,事實上,在日軍慰安所中慰安婦的性病比例很高。“自從日本人進城后,性病的比例從15%上升到80%。軍隊要大量妓女,不斷有人從周邊農村搶走婦女,把她們送進城以滿足需要。而且因為她們對性病毫無防御力,很快就會染上重病。在這種行當里不再有使用價值,所以就不斷地要求新的婦女來補充。”
除了性病,日軍慰安所也是交易和吸食毒品的場所。據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調查研究,到了1938年11月,“在過去幾天,一家日本和韓國的慰安婦機構,就買進80箱鴉片。”“有時日本士兵用鴉片來支付妓女和在軍需物資供應站干活的勞工。”
(三)西方傳教士對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批判
西方傳教士對日軍在南京違背人類良知、公然四處設立“慰安所”、強征“慰安婦”的惡劣行徑給予了猛烈的批判。日軍擔心性病傳染,影響士兵戰斗力,成立了統一管理的“慰安所”,但他們卻聲稱設立專門的“慰安所”是為了保護良家婦女。日軍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令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深感吃驚與憤慨。馬吉對此從日本文化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在寫給夫人的信中說:“日本人似乎是一個沒有性道德的民族,在這個國家,一個女子為了經濟方面幫助父母而當幾年妓女被認為是孝順的行為,然后再結婚。當然在這方面他們有自己的道德規范,我們與之打交道,這些日本人根本不認為強奸是什么罪行。”
貝德士針對在南京大街上出現的“慰安所”廣告,諷刺說這是“代表裝點南京街道之一種象征模式”,成為日本“東亞新秩序的政治工具”。
他寫道:“南京居民常常回想,在國民政府治理下這里是不允許有有傷風化的淫穢展示的,市政當局嚴禁各種惡行。現在他們正在了解日本首相宣言的意義,他的國家‘必須盡最大努力把中國提升到日本的文化水準’。
甚至連海報的語言都是中日淫穢的混合物,令每個有教養的中國人作嘔,同時又是對于受過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軍隊促進的這種‘友好關系’,最好別印出來。
淪陷區居民知道,日軍離開邪惡即無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們希望應該多少考慮一下對于年輕一代心靈的影響,以及一個過去習慣于禮儀的社會的市容。”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針對日軍所推行的“慰安婦”制度,盡管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根本不可能深入調查,但僅從他們所留下的所見所聞,我們從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判斷:一是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慰安婦”來源完全是強制掠奪的,根本不是所謂自愿的商業行為。二是在慰安所的婦女過著非人般的生活,隨時有生命危險。三是日軍在南京推行的“慰安婦”制度極大地傷害了南京逐漸建立起來的現代道德文明。
三、誰在編造謊言:日本國內論爭的此消彼長
【程兆奇】1971年6~7月,《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獲中國政府特許,訪問了還處在“文革”中的中國廣州、長沙、北京、沈陽、撫順、鞍山、唐山、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幸存的受害人,這些記錄成了自當年8月起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的《中國之旅》的主要內容。由于本多勝一的嚴厲批判,加上《朝日新聞》的特別影響力,“南京大屠殺”成了日本大眾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引起的是反省還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輕斷。但它的影響本身使持反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者不能自安,由此為推動力形成了一波強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洶涌浪潮。另一方面,在左右兩方的爭持中也推動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展開。
其實,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還早在本多勝一報道發表之前。日本學者洞富雄在“文革”之前就曾赴南京,調查有關日軍在南京的暴行。1968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文,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文。1972年洞富雄出版了第一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專著《南京事件》;次年,兩卷本的《南京大屠殺資料集》出版。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問題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探討,從他的代表作《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看,他提出的問題和對日本“虛構派”的辯駁基本構建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框架,確立了回應“虛構派”挑戰的方向。雖然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推進,洞富雄的一些具體結論已被超越或修正,但從總體上說,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并未動搖。
在《中國之旅》發表的次年,第一個站出來“批駁”本多勝一的是鈴木明。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刊物的重鎮《諸君!》發表了《“南京大屠殺”之謎》(“謎”的原字為假名“まぼろし”,以往多譯為“虛構”,作者后來澄清說應為“謎”)。次年鈴木明的論集也以此為題名。此文發表后,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一派即被稱為“まぼろし派”,或“虛構派”。《“南京大屠殺”之謎》涉及第16師團諸如尸體橋等等的疑問,但主要是對“百人斬”的質疑。在20世紀70年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爭論點。雙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勝一,一方是鈴木明和《我心中的日本兵》的作者山本七平。
進入80年代,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當時教科書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成了激化爭論的外部觸機。1984年“屠殺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除了洞富雄和本多勝一,成員還有前輩學者藤原彰,中生代學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等20人。這一時期是“屠殺派”取得最大成績、也是在和“虛構派”爭論中最占上風的時期。當時“屠殺派”的重要著作還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殺》、吉田裕的《天皇的軍隊和南京事件》、本多勝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審判的南京大屠殺》以及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編輯的《思考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現場》等。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推進和“虛構派”的挑戰密不可分,同樣“虛構派”的愈演愈烈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屠殺派”的刺激所致。80年代“屠殺派”的最主要論敵是戰時在大東亞協會跟隨過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他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殺”的虛構》和《南京事件的總括》兩部書中。兩書從所謂南京人口、戰后難民的急速增加、進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見尸體、國際委員會報告的虛與實、難民區的安泰和感謝信、大量屠殺俘虜的虛構、崇善堂埋尸的不實、斯邁思調查可證沒有大規模暴行、事發時中國軍事會議未提及、中共沒有記錄、國聯沒有成為議題、美英法等國沒有抗議、美英媒體幾乎沒有報道、沒有鉗口令、沒有目擊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謂“傳聞材料”、照片出自偽造等等廣泛方面,否定日軍有過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如果問田中正明與之前的虛構論者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點就是從對南京大屠殺的某一點的質疑到對整體的徹底否定。田中正明不僅和“屠殺派”辯難不已,和“中間派”也勢同水火,有激烈交鋒。雖然從“虛構派”那里看到的永遠是勝利宣言,但在這一輪的攻防中至少在聲勢上“虛構派”是被壓了下去。除了上引著作,這一時期“屠殺派”的更重要貢獻是通過廣泛搜求,全面建立了支撐以屠殺為代表的日軍暴行為實有的史料基礎。90年代初出版的《南京事件資料集》最重要的上卷“美國關系資料編”也成之于這一時期。
日本“中間派”是認為屠殺人數在數萬到1萬的寬泛表述,近年又有人將其中主張被殺1萬左右的稱為“小屠殺派”,被殺4萬的稱為“中屠殺派”。“中間派”只是對屠殺數的認定介于兩者之間,其“政治”立場則遠為復雜多樣,不像“虛構”、“屠殺”兩派那樣單一明了。如在日本有大名的櫻井よしこ在被殺人數的認定上屬于“小屠殺派”,但長期以來一直是一面反中的旗幟,和“虛構派”沒有分別;而“中屠殺派”的秦郁彥的基本看法則接近于“屠殺派”。“中間派”長期以來與“虛構派”、“屠殺派”兩線作戰,總的來說,在80年代“中間派”對“虛構派”的批駁力度還是更大一些。比如田中正明編輯的《松井石根大將陣中日志》出版后,“小屠殺派”的板倉由明經過逐一核對指出田中“改篡”松井原文達900處。80年代“中間派”在資料上也有建樹,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舊軍人團體偕行社編輯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和90年代初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Ⅱ》。盡管戰時文獻多已被焚,但殘存的日本軍方文獻仍可證明日軍曾大規模屠殺俘虜。《南京戰史資料集》所收日軍官兵日記的特點是包括最高長官以下的各個層級,與“屠殺派”所編資料集悉為士兵和下級軍官不同。進入90年代后,“中間派”中雖然仍有偏重“技術”的傾向,如防衛研究所研究員原剛通過重新研究幕府山屠殺俘虜等個案,將屠殺數從1萬提高到2~3萬。但大體上說90年代后“中間派”整體是在右轉。如“小屠殺派”的畝本正己自稱他著作的目的就是“洗刷”日軍的“冤罪”,80年代曾批駁田中正明“改篡”史料的板倉由明的遺著《真相是這樣的南京事件》所附追思篇題名即稱板倉為“屠殺派”的“天敵”,即使秦郁彥也多次說“正確的數字只有上帝才知道”。在“虛構派”甚囂塵上的今天,“中間派”的“中間”意義已十分弱化。
90年代以后特別是近年“虛構派”聲勢日益煊赫和冷戰結束后日本保守勢力卷土重來的大背景有很大關系。這一時期“虛構派”有這樣幾方面的變化。一是右翼“學者”成為主流。90年代中期前,除了曾從事媒體、出版工作的鈴木明、阿羅健一(畠中秀夫),“虛構派”主要是戰時的一輩人,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意識形態”味濃厚的東中野修道、藤岡信勝,還是基本算是專業型學者的北村稔,都是長期在大學執教的大學教授。二是“組織”化。和“屠殺派”80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不同,“虛構派”90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則頻有聚合,2000年還成立了“南京學會”。三是和政界互通聲息。90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對歷史問題的“失言”,但并未直接介入“虛構派”的活動,近年自民黨“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思考會”的“南京問題小委員會”及參眾兩院超黨派“檢證南京事件的真實之會”都與“虛構派”時相過從,互動密切。四是主流電視臺的推波助瀾。長期以來日本主流電視臺間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議論,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主持的東京電視臺(十二頻道)的談話節目,但從未以南京大屠殺作為專題,以南京大屠殺為專門節目近年始見。這些節目因“屠殺派”從不參與(在電視中“拋頭露面”揭日本傷疤的壓力可以想見),而“虛構派”總是有備而來,這樣的不對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兩方的相爭總是“虛構派”以“證據”獲勝。因此,對“虛構派”來說,這種節目其實比單方面宣傳更有效果。五是虛構觀點的全面深化。“虛構派”在鈴木明時期還只是提出幾點疑問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盤否定始具規模,這一時期“虛構派”上窮下索,對以往的主張全面強化。如田中正明在《南京事件的總括》的結尾說到照片“偽造”,東中野修道等人接過衣缽號稱檢查了全部照片:“對‘證據照片’143張首次進行總括的檢證”,證明“作為證據的照片一張也沒有”。鈴木明“發現”田伯烈是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誤書為“情報部”)“顧問”,北村稔以此為線索寫了一本在“虛構派”中備受推崇、號稱從源頭上抓到了所謂“南京事件”與“國民黨的國際宣傳和對外戰略”有“密切關系”的“把柄”的專著。六是新著連篇累牘的問世。七是第一次拍攝電影《南京的真實》(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開始向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輸出。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虛構觀點的影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大。
面對“虛構派”的全面進攻,“屠殺派”仍在頑強抗爭。與80年代“屠殺派”給人的“眾志成城”的印象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13個謊言》,“屠殺派”基本上是單槍匹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為戰。這一時期在實證研究上成績最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成員中石田勇治編譯的《德國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資料的第一次結集。小野賢二編輯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的最大意義在于證明了戰時報道的“兩角部隊”在幕府山俘虜的1.4萬名中國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槍殺。“調查會”之外,松岡環編輯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采訪第16師團為主的老兵達102名,為迄今搶救當事者記憶的人數之最。這一時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殺派”著作中,我覺得有一本書應該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此書的中譯本在兩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書,之所以說“應該一提”,是因為此書在日本連“屠殺派”也“視而不見”。被無視的原因當是由于此書以南京大屠殺“實有”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諸派所爭本在史實,但我覺得之所以被無視多少也和此書尖銳批判的對象是日本民眾的責任有關。日本各派“黨同伐異”由來已久,80年代“屠殺派”占據上風和90年代“虛構派”甚囂塵上可以說都是拜同派之間聲應氣求“一致對外”之賜,“屠殺派”在這一時期的影響力下降不能說沒有整個風氣右轉的大環境原因,但和“屠殺派”“各自為政”過于孤高也不能說全然無關。
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爭論的歷史,可以說諸派論爭是推動研究的最主要原動力。目前“虛構派”雖然氣盛一時,但沒有也不可能籠罩一切。由于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窮盡,所以各派影響力雖會有消長起伏,在看得到的將來,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壓倒性勝利則當無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