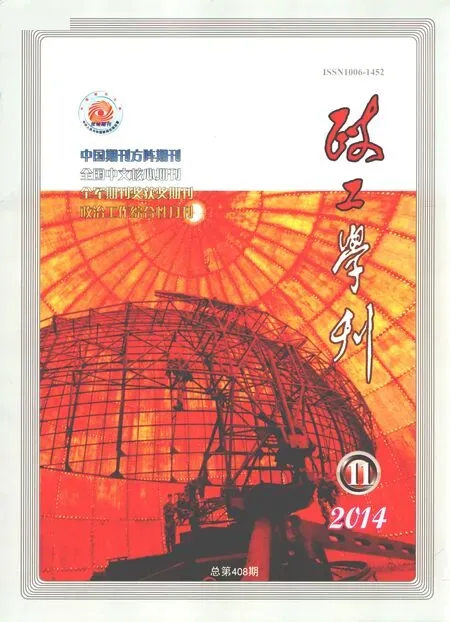弘揚中華傳統武德 培育我軍戰斗精神
●衛 琦
弘揚中華傳統武德 培育我軍戰斗精神
●衛 琦
中華傳統武德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軍戰斗力生成的民族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和弘揚其優秀內涵,對于培育我軍官兵戰斗精神、推動強軍目標實現具有積極意義。
一、弘揚“精忠報國、捍族衛民”的武德傳統,培育官兵聽黨指揮、報效國家的忠誠品格
忠誠作為武德的基本規范源遠流長,《左傳》中說“臨患不忘國,忠也”。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孫武,就把“與上同意”之“忠”,放在戰勝敵人的五大要素之首,并要求將帥“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是“效忠貞之節”的典范,強調“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兇。故良將守之,志立而名揚”,因此對兵卒要“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明將戚繼光強調軍人要“倡忠義之理”。歷代兵學圣典中都明確把“忠”作為軍人的基本品格之一,表現了古代軍人對國家、對國君忠心不二,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以致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境界。雖然古代軍人的忠誠有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但就一般意義而言,為捍衛本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忠誠品格,自古以來都被歷史所謳歌。在新的歷史時期,習主席提出必須把聽黨指揮作為強軍目標之魂,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絕對忠誠,是人民軍隊最重要的政治品格,是堅決聽黨指揮的價值支撐,是戰斗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礎和不竭力量的源泉。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尖銳復雜、軍隊使命任務不斷拓展的新形勢下,只有對黨、國家和人民絕對忠誠,才能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落到實處。
二、弘揚“尚武足兵、務戰備兵”的武德傳統,培育官兵和不忘戰、安不忘危的打仗意識
軍隊是為打仗而存在的,《孫子兵法》有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國家的安危存亡,人民的禍福生死,是與國防、軍隊和戰爭緊緊連在一起的。作為國家,不可一日無軍;作為軍人,不可一日忘戰。孔子基于對戰爭的不可避免性認識,提出了“足兵”的思想,強調要有充足的武備,使之足以維護政權,保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左傳·襄公十一年》曾載:“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吳起曰:“備者,出門如見敵”。墨子雖主張“非攻”,但也強調:“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回顧中華武德文化發展史,也常有“重文輕武”的深刻教訓,不少軍隊在和平環境下,在歌舞升平、文恬武嬉的氛圍中,滋生享樂腐敗之風,淹沒尚武精神,淡化打仗意識,導致敗軍亡國。歷史證明,只有安不忘危,和不忘戰,長存憂患意識,軍隊才能永葆戰斗力,民族才能生存發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站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高度,強調軍隊要強化戰斗隊思想,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的思想,加強戰斗精神培育,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國不可一日忘兵,兵不可一日忘戰,越是和平時期,越是勝利之師,越要增強和不忘戰、安不忘危的打仗意識,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堅持不懈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始終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發的戰備狀態。
三、弘揚“習武精藝、智勇兼備”的武德傳統,培育官兵英勇善戰、敢打必勝的勇敢品質
兩軍相逢勇者勝。一切軍隊要奪取戰爭的勝利,都離不開一個“勇”字,這是最基本的戰斗精神。勇敢作為軍人必備的素質,歷來為兵家所重視。孔子把美德概括為“智、仁、勇”,“勇”被后人稱為“三達德”之一;《孫子兵法》中講軍人有五種美德,即“智、信、仁、勇、嚴”,強調欲求兵勝,必須“齊勇若一”地與敵軍拼搏。所謂“兵之勝負,全在勇怯”“有勇,能摧堅破銳”等兵家名言,之所以被后人視為經典,就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勇”的價值,蘊含著豐富的軍事哲理。何為“勇”呢?孔子及其眾兵家認為符合于“義”“智”“仁”的“勇”,才是武德之勇,否則就是“蠻勇”“魯勇”“匹夫之勇”。勇武之氣如何來呢?古代兵家強調通過尚武精藝,練就英勇膽氣。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軍事變革的潮起潮落,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正在悄然發生改變,人們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信息化戰爭是否還需要刺刀見紅、貼身肉搏之勇?“夫戰,勇氣也”。戰斗力從來都是以敢于亮劍、勇于犧牲的勇敢精神為支撐的,我軍也正是這樣一步步走向勝利的。信息化戰場的真正英雄應該是“信息精英+鋼鐵硬漢”,官兵必須具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往無前、英勇無畏的軍人血性,科學運籌、從容應變的智慧謀略,堅毅果敢、攻堅克難的意志品質。朱德元帥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預見說:今后戰爭的勝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他又認為,不能只靠勇敢,還必須使軍隊各種成員精通軍事技術,“使勇敢與技術相結合”,勇敢加技術,就戰無不勝。“藝高”與“膽大”是辯證統一的。在信息化戰爭條件下,勇敢無畏的膽略,可以使手中武器的效能發揮到最優狀態。習主席多次強調指出:和平時期,決不能把兵帶嬌氣了,威武之師還得威武,軍人還得有血性。因此,在加強官兵練勇氣、強血性的戰斗精神培育中,必須教育引導廣大官兵大力發揚我軍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保持旺盛革命熱情和高昂戰斗意志。
四、弘揚“師出以律、賞信罰必”的武德傳統,培育官兵依法治軍、軍紀如鐵的守紀觀念
歷代軍事家都把嚴格的紀律作為治軍統兵的第一要義,《周易》講到:“師出以律,失律兇也”。《孫臏兵法》強調:“令不行,眾不一,可敗也”。歷史上曹操削發代首,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等等,都是嚴肅軍紀、從嚴治軍的佳話。而推行軍紀軍律、激勵士氣的重要手段就是做到“賞信罰必”,其包含豐富的內涵:一是賞不逾時、罰不遷列,強調賞罰的及時性;二是賞不虛施、罰不妄加,強調賞罰的適當性;三是賞無私功、刑無私罪,強調賞罰的公正性,也就是該賞就賞,該罰就罰,賞罰分明,兌現及時。嚴守紀律是軍人必備的武德,也是形成和鞏固強大戰斗力的重要因素。我軍歷來非常重視紀律建設,正是因為軍紀嚴明,我們才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和擁戴,以劣勝優,以弱勝強,奪取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同時“嚴守紀律”也是新時期的軍人道德規范,更是實現強軍目標的保證。未來作戰是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其聯合性、精確性、協調性等要求不斷提高,這就要求各個環節、各個要素必須絲絲相扣、精確無誤,依法從嚴治軍必然是未來體系作戰的要求。同時,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愈加艱巨,給國家和軍隊的安全和穩定增加了新的威脅。習主席正是基于對國內外復雜局勢,以及軍隊發展規律的歷史性把握,鮮明提出:“要牢記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必須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這就要求全體官兵在戰斗精神培育中,不斷加強組織紀律性,保持政治本色;牢固確立法治理念,尊重法紀權威,嚴格按照法紀制度履職盡責;注重條令條例和規章制度的貫徹落實,著力增強法規制度執行力,始終保持部隊正規的戰備、訓練、工作和生活秩序。
五、弘揚“和軍一心、上誠下信”的武德傳統,培育官兵尊干愛兵、同甘共苦的團結精神
“用兵之道在于人和”是歷代兵家和其他思想家的共識。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吳子云: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說:宋時人稱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只因為岳家軍“軍士萬人一心,一個百斤力,萬個百萬力矣,如何撼得動。”“和軍”貴在“愛卒”,只有“愛卒”才能“和軍”。孫武率先提出視卒如愛子,視卒為嬰兒。因此中華武德史上,有吳起為士卒吮疽,與士卒同衣食,士卒勇于為國盡忠;岳飛親自為有疾之卒調藥,派妻子慰問部將的家室,撫養犧牲部卒的子女等故事流傳至今。“團結出戰斗力”這一定律,同樣在我們人民軍隊的斗爭和建設實踐中得到了充分證明。我軍官兵情同手足、親如兄弟,同寒暑、共安危,患難與共、生死相依……這是我軍擁有排除萬難、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強大戰斗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習主席指出:要大力發揚尊干愛兵、官兵一致的優良傳統,堅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團結友愛和諧純潔的內部關系。未來信息化戰爭是陸、海、空、天、電“五位一體”的諸軍兵種合作作戰,對團結協作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對官兵團結協作精神的考驗更加艱巨。這就要求全體官兵繼承“和軍一心”的武德傳統,站在實現強軍目標的高度,深刻認識和對待團結問題,做到時時、處處、事事、人人都顧大局、講團結。
【作者系第二軍醫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