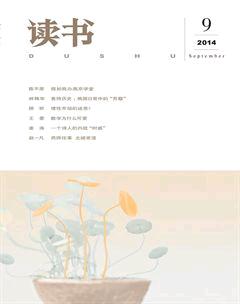讀《閻宗臨傳》
丁東
此書傳主和作者是父子,又是史學同行。兒子寫父親,容易產生子為父隱的偏向,偏離學術的中立性。作者對此有所警惕,力求以事實說話,依托豐富的文獻,議論不多,分寸得當,雖帶著體溫和親情,但并無溢美之詞。在當今的學人傳記中,當屬難得之作。
閻宗臨一九零四年生于山西五臺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朝陽大學,因經濟困難而退學,同年參加狂飚社,由高長虹介紹認識魯迅。一九二五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九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學哲學文學院,學習歐洲古代文化及歷史。開始與羅曼·羅蘭的交往。當時羅曼·羅蘭有了解魯迅的愿望,正巧遇上了這個認識魯迅的中國青年。這就使閻宗臨成為羅曼·羅蘭的忘年交和中文譯介者。他一九三三年獲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回國任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次年再赴瑞士,到弗里堡大學任教,同時攻讀博士。一九三六年獲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為赴國難,他與新婚妻子梁佩云辭別瑞士,啟程回國。
從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閻宗臨先后在山西大學、廣西大學、桂林師范學院、無錫國專、中山大學任教,進入一生學術的高峰期。“二戰”激烈進行的年代,他所擅長的歐洲歷史文化,正是觀察戰爭深層原因的重要視角。他逐一論述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俄國和中國文化的不同,從中尋找戰爭的動因,分析戰爭的趨勢,闡發中國抗戰必勝和日本必敗的理由,其學術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他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略懂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直接閱讀了大量歐洲文獻,兼有歐洲生活和實地考察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對歐洲歷史文化的體系認識,反映在他的專著《歐洲文化史論要》、講稿《歐洲史要義》、《希臘羅馬史稿》中,這些論著處于當時中國人認識歐洲歷史文化的最前沿。他不但見地獨特,而且文筆精彩。不妨體會一下他的行文風格:
我是愛讀羅馬史的,為此我曾去過羅馬七次,看地孛河疲倦緩慢的水勢,深感到他的回憶太多。在羅馬,無處不表現這種豐富,使人感到迷離。豐富是生的別名,每塊石頭上,都有他不朽的生命,容十萬人的斗獸場;二十二萬四千平方公尺的澡堂,破瓦頹垣的政議場,無處不表現他的容量,為此,他成了歐洲一切的根源,而今歐洲的形勢,也許從羅馬史中發現他們的缺陷。羅馬史在告訴我一個真理:奮斗者生。但是奮斗必須以正義為目的,以群眾的福利為皈依,倘使一切的行為完全以自己為主,恃強凌弱,必然要淘汰的。羅馬的偉大,不在他的武力,而在他的法律。
然而,進入五十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的歷史觀定于一尊,唯物史觀成為不二法門。閻宗臨原先熟悉的是伏爾泰、布克哈特一脈的文化史觀,這時已經被判定為唯心論,只好從頭學習唯物史觀。研究對象也從遙遠的歐洲,回歸本鄉本土的古籍整理。他學術成果的數量,以《閻宗臨作品》三卷為據:“從一九三六年開始至一九四九年的十三年間,有六十四萬字,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九年間有二十六萬字。”
抗戰時期,饒宗頤與閻宗臨在桂林無錫國專曾是同事,又一起在桂東逃難。饒宗頤對他的學識贊揚備至,說“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西方傳教士與華交往之事,國人治學循此途轍者殆如鳳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重”。后饒宗頤去了香港中文大學,成為一代學術宗師,成就堪稱輝煌。而閻宗臨“回山西故里,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當然,這不是閻宗臨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中國大陸史學界共同的命運。五十年代以后,只有陳寅恪、顧準等極少數的史學家、思想家在另辟蹊徑,留下卓爾不群之音。
閻宗臨晚年對史學已經傷透了心。他有六個兒女,都上了大學,但只有閻守誠最終進入歷史系,成為子承父業的唯一傳人。
我和閻宗臨教授有一層師生關系。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我報考了山西大學歷史系,一九七八年春入校,作為系主任的閻宗臨身體已經很衰弱,我雖然去他家和他見過面,但僅僅寒暄而已,學術上未得親授。那年秋天,他與世長辭。二零零七年,《閻宗臨作品》三種—《歐洲文化史論》、《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出版,我才恍然醒悟,一位曾經近在眼前的學者,早就耕耘出一片博大精深、生趣盎然的史學天地,一個大師在我的求學之旅上遺憾地擦身而過。這是我有眼無珠,還是時代的宿命使然?
(《閻宗臨傳》,閻守誠著,三晉出版社二零一四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