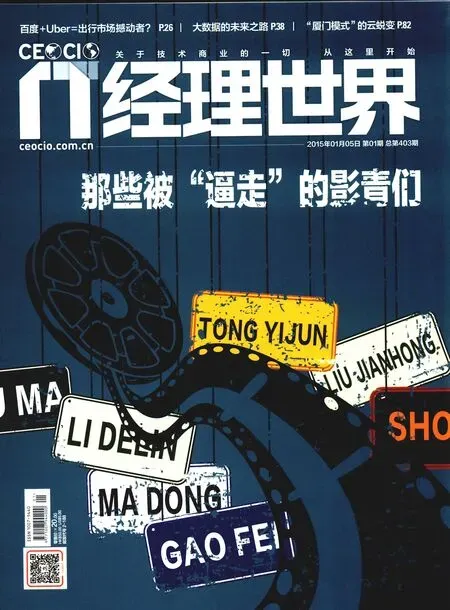底特律式衰敗與救贖
劉曉芳


李書福給自己布了一個局。他原本是來宣示成果的,沒想到卻被卷入與幾位互聯網精英的舌戰中。當然,場上的刀光劍影,好像并沒有影響到李書福幾天來的好心情。
就在這場論戰的三天前,沃爾沃在國家會議中心召開了盛大的新品發布會。那天,嘉賓云集,媒體難得興奮忙碌,李書福是當晚最笑容滿面的資深明星。李書福有理由高興,沃爾沃S60L是他醞釀了很久打出的一記重拳,終于可以與“德系三強”在單個戰場上正面作戰。
自從被吉利收購后,沃爾沃一直被拿來與當年出自同一個老東家福特的另一大品牌——捷豹路虎相比,后者給塔塔集團帶來的收益遠遠超出沃爾沃對吉利集團的貢獻。過去的三年,李書福承受運營,成本及政策多重壓力,然而,當晚發布會上,他在臺上未發一言,也沒有接受任何采訪,只是微笑,偶爾豎起大拇指讓人拍照。
底特律式焦慮
與在發布會上展現的自信姿態相比,幾天后,當李書福走出一個國際汽車安全論壇的會場時,臉上卻多了幾分凝重。
這場論壇,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李書福遭遇了來自搜狗王小川、易到用車周航,以及麥肯錫資深合伙人高旭的聯合狙擊,或者用他們的行話說“倒逼”。沃爾沃是這場論壇的贊助商,李書福應該沒想到,做了一個局,結果把自己做進去了。也是,誰叫他太大牌了呢!
雙方交火,場面火爆,場上場下高潮迭起,不過,有點詭異的是,你很難聚焦找到雙方論戰的核心,因為自始至終雙方各用兩套話語體系,各說各話,各表各態,好像雙方來自兩個逆世界。終了也沒有形成共識。如果說互聯網正在改變汽車,這也算共識的話,好吧這算一個。
真實的情形是這樣的,有兩撥人,一撥來自汽車業,一撥來自互聯網和IT業,要共赴一場盛宴。可是大家都站在門口,誰也不想先進去。因為誰先進去就意味他要先給自己找座坐下,怎么坐呢?這個座位的排位向來是有大學問的。
汽車企業肚里的一張牌是,這是我們的地盤,汽車再怎么改變,汽車的基因還在,汽車是主人,互聯網是客人,宴賓請客,基本客套是必須的。
“互聯網及應用是為汽車和車主服務的,而不應該由它們來主導汽車行業。就像如果沒有蘋果手機,任何應用都無用武之地。沒有汽車,談何應用。”李書福開門見山亮出觀點之余,也沒忘展現要變的誠意,“原來汽車業相互比的是發動機效率,這種思維已經老了。現在大家比的是誰的排氣量小,氣缸數少,扭矩小,要做到這些難度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高。而這一切背后的驅動力就是來自于電腦和電池技術的變革。”
而來自互聯網行業的新晉精英們卻另有打算,互聯網已經橫掃各個行業,汽車是最后一公里上要打通的一個鐵殼子,新的游戲規則不可能由一家說了算,誰占主導還不一定。
“互聯網產品的更新換代以月或周為周期,汽車以年為周期。這使我對汽車產生畏懼,以前見到汽車企業都是繞著走,能不打交道就不打交道。這兩年發現,互聯網正在對汽車產生倒逼的效果,汽車業主動找上門來了。可是,它們做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所有汽車企業都要求定制,要以廠商為主,把B2C變成了B2B,互聯網以用戶為中心的精髓被打破了。這是思維方式的不同,一定要用互聯網的思維改造甚至消弭汽車思維。”王小川大有一錘定音的魄力。
這場論戰基本從一開始就被定了論調,它既是當下汽車與互聯網交鋒的主流思潮,又不是太主流。它是一次行業集體焦慮的發泄,離實質性操作層面的對話還很遠。不過,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汽車與互聯網各自的一線戰區交戰,隨著相互滲透的深入,一場縱深的遭遇戰已不可避免。
追溯這場交火的源頭,各種線索其實早有暗示,而這些線索往回延伸一個最大的交匯區,就是底特律的破產。很多人,把底特律城市消亡當作一個獨立事件,或者只當成美國經濟危機下的獨特個案,只能說您也被誤導得有些偏視了。
誠然,底特律走向今天離不開美國政府對汽車工業的袒護有加,不惜多年借債維持底特律的運轉;同時,美國汽車工業協會的強健,使得其堅若磐石的薪酬福利制度,成為了當年通用等巨頭企業破產的直接導火索;當然,你還可能會說金融危機席卷了汽車業。真正的原因果真僅僅是這樣的嗎,如果不是因為汽車業維持了近百年的高利潤增長,如果不是因為股民包括華爾街都對汽車業抱有習慣性的高預期,會有這些結果嗎?
事實是,這個汽車業多年的高利潤池早已經開始出現大幅萎縮現象。最近十幾年以來,各大汽車企業旗下擁有的多品牌之間,不同企業同價位品牌之間的質量和性能越來越趨同質化,邊際利潤不斷被攤薄。更為關鍵的是,汽車業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現令消費者驚喜的創新了。
汽車業高附加值的這塊利潤池已經被挖掘殆盡,企業的增長率與員工的薪酬增長相比,動力不足,難以為繼。“底特律的破產象征著美國標簽和創新精神的喪失。”比爾·弗拉斯科在《底特律往事》中的筆觸沉痛,驚心動魄。
汽車業腐朽指數高
“底特律破敗不堪,街道上百業凋零,人煙稀少。……這一幕場景寧靜而灰暗,顯得那樣令人傷感。宜人的天氣反而凸顯出這里水泥地的黑灰色以及塵土的棕黃色,就像上古時代的石塊,已經無法擦洗光亮了。(摘自《底特律往事》)”
這是2005年的底特律。近100年前,福特在這里建立了第一座工廠。隨后,在汽車歷史上三次重大變革中,一次就是福特建立標準汽車流水線,一次來自豐田的精益生產模式,第三次也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互聯網汽車變革。
2005年,底特律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最后掙扎階段。“美國汽車工業一直在以極度狂熱的速度進行著生產。…然而,銷售業績卻沒有隨之增長。”《底特律往事》這樣記錄道,約克是美國最負盛名的財務專家,他像科研工作者一樣將通用汽車的資產負債表細細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以圖尋找一種治療流行病的藥。在他看來,通用過于自大,一系列價值連城的資產都湮沒在了堆積如山的債務、海量品牌以及龐大的業務團隊、高管和員工隊伍中。盡管如此,通用也沒有把有限的現金用于重組和產品創新上,而是花在了銷售推廣中。
決策失誤,變革的抱負和決心不足,創新乏力,同時,官僚主義和龐大的體系阻礙了它快速的改革計劃,最終使得通用一步一步走向破產。福特和克萊斯勒的情形也大體不出這個范疇。
那時候,比爾·福特會在凌晨3點,輾轉反側,難以入眠。而通用的時任總裁里克·瓦格納眼看著企業一天天沉下去變得越來越狂躁。他們都一腔熱情,聰明絕頂,都是企業的忠實守護者。可是,他們能做的是在一個毫無生氣的舊體制下,拿一幅舊牌玩出新花樣來。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嘛。
而期間互聯網和IT技術正在逐步潛入到各行各業中,從每個流程的細節到創新的思維層面,從形而下到形而上,全面改造一個企業的運維體系。至少到2008年前,汽車業與互聯網業二者仍還處在相互隔岸看熱鬧的情形。2009年以后才有少數的先行者,國內的如榮威350iVoka,國際的有寶馬的iDrive,開始被融入互聯網因素應用到汽車上。但是,這些都還只是局部的改造和探索,直到谷歌的無人駕駛汽車開始駛入街面,特斯拉按照硅谷思路打造出一臺體系化呈現互聯網精神的電動車,汽車業的大佬們才突然有所覺悟。原來他們真有可能是落伍了。
然而,覺悟歸覺悟,覺悟離動手做,能做多徹底,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汽車業太慢,腐朽指數高。”周航一語點出了汽車業的癥結,“汽車還沒有高度的體系化,它們慣有的做法是,先有局部,然后去分步處理,結果系統越做越復雜,組織結構越來越龐大。”
王旭做了多年的汽車咨詢,他知道,汽車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它的所有軟件編程程序超過1億條,比波音787航電系統的870萬條還要多。汽車已經成為一個最復雜的日常消費品。”
“為什么汽車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操作系統,一個統一的架構?汽車從來就沒有一體化的計算能力,也不是一體化的架構。大家都是關起門來做自己封閉的體系,這是汽車被高度復雜化的根本原因。”周航向來是敢仗義執言的人。
汽車為什么要做得那么復雜,有必要嗎?面對直接的質疑,李書福的回應有些百轉千回,“汽車本來就復雜,但是IT更復雜。跟電腦和網絡相比,汽車已經很簡單。面對IT和互聯網,汽車廠商需要自我意識到變革,然后實現自我超越,自我變革。互聯網要來搶汽車的飯碗,是不容易搶的。”
這是一種自信者的姿態。雖然李書福也坦承汽車業表面看上去反應慢,實際下面已經是波濤洶涌,不過,在他的重要性排序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估計還是銷售,互聯網概念仍然是為銷售服務的。
互聯網的精神勝利法
底特律的衰退在汽車業還是沒有引起足夠的反思,很多同行甚至還有些看熱鬧的心態也未曾可知。
與之相比,從漩渦中心暫時逃生出來的通用和福特兩家企業,表現出了更為迫切的創新焦慮。這種焦慮有可能促使它們行動更大膽,執行更堅決。
從事實看來,也確實有此跡象。2013年年初,福特和通用先后宣布開放各自車載系統,此舉的意義與當年大型機操作系統從封閉走向開放一樣,是汽車向一體化架構邁出的關鍵一步。
鈦馬車聯網的董事長葉志華,以前在IBM做過10年,他們一直在緊盯著這兩家公司的最新動向,隨時準備以第三方開發商身份切進去,“汽車互聯網不是汽車企業的私家花園,它一定是個逐步走向開放的過程。”
通用正在努力從底特律破產的陰影中掙脫出來,秘密武器就是把自己打造成電腦科技肌肉男。它希望以此來拉開與行業其他競爭對手的距離,重建底特律低科技和粗線條制造的形象,打造新的核心競爭力。
雖然福特也一直在強調自己是家科技公司,但是,通用更加的富有野心。這是一項需要付出代價和勇氣雙高的計劃。未來3~5年內,通用將招募1萬名軟件工程師和科技宅男,剛畢業的工程師在通用能拿到6~7萬美元一年,有經驗的薪資更高,核算一下成本,光工資就令人乍舌。
這些來自IT業的新鮮血液將主要承擔最前沿的軟件開發工作,他們的成果將用于如何將手機與汽車控制技術連接起來,比如用語音來命令空調的開關。此外,他們還將開發一些嚴格保密的技術和未來科技。“我們正在尋找下一代游戲規則,開創一個汽車創新的新時代。”通用現任CIO Randy Mott,以前曾在惠普公司擔任多年的CIO。
HIS產業咨詢公司的資深分析師認為,如今各大汽車品牌之間質量差異越來越小,唯一可以走差異化競爭的路徑,就是發展汽車控制和汽車電子技術。怎么發展,來自通用的解讀是:未來企業CEO都要具備軟件思維。
什么是軟件思維,就像手機在諾基亞就是手機,但到了蘋果手里就變成了iPhone,后者是一個工作、生活、消遣娛樂等多功能的微信息服務中心。軟件將一塊硬件的價值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延展。這也是現在汽車業的一條發展思路。
在中國圈內人談得更多的是互聯網思路。如果讓王小川來做汽車,他們可能會用互聯網的來改造汽車,比如,讓后視鏡可以變成帶攝像頭功能的可視鏡,它可以掃描你的眼睛,是全自動化的,甚至可以智能地去調節方位。“還有會像谷歌那樣去做激光測量儀的技術,先把測量技術做到精準化,然后再去將數據聯網。”總之,汽車的體驗也要從人的角度出發,現在的汽車給用戶的體驗價值還很不夠。這是一套體系化的能力。
而周航看到的是,“特斯拉的魅力一半在汽車電子,一半在它的實時在線架構。它進入中國市場后,最讓人擔憂的是,怎么解決本地地圖或音樂的問題,因為它所有的應用都在云端。”
特斯拉不愧是從硅谷出來的,它是一個軟件編程專家,把汽車的基因代碼來了一次重寫,融入了消費者基因。在底特律最輝煌的時期,一個工廠動輒投資幾百億上千億美元,汽車的固定資產投資太大,到了現在,工廠已經成為汽車企業對用戶體驗價值最低的一塊。
汽車制造一直建立在大規模消耗社會資源模式基礎上,底特律破產正是對這種模式的一次經濟層面的反思。互聯網經濟模式下,為什么會出現共享經濟,它根本是一種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模式,追求最小消耗,最大利益化。
當前在中國汽車工廠,可以看見大量的工人進進出出,汽車企業對于爭相擴大產能抱有一種狂熱的激情,然而,利潤增長在急速下降。這還是規模經濟的思路,一旦市場日趨飽和,而社會資源消耗到達一個臨界點,底特律式的魔咒可能就會出現。
葉志華的觀點大致是,對于汽車企業來講,變與不變,不是錢掙多還是掙少,而是淘汰別人還是被別人淘汰的問題了。至于互聯網會對汽車形成一個怎樣的倒逼法,工具與服務說,取信力不足。蘋果增值在硬件,服務只是高盈利的一種支持性手段。每個新興產業只能根植在傳統產業土壤之上,不是憑空增長的。谷歌未來是通過對傳統產業利潤鏈的一種巧妙性切入,打破傳統的鏈條,獲得一種重新議價的話語權。建立一條新的博弈鏈。
“未來誰革誰的命很難說,也有可能像當年元朝蒙古入侵中原一樣,互聯網雖然淪陷了,但最終還是把入侵者同化了,最后的精神勝利者還是屬于互聯網。”王小川懷有一種悲觀的樂觀主義精神。
而李書福仍然相信,“IT是IT,汽車是汽車,大家相互依存。特斯拉最后還是汽車工業,也許將來有一天,它會通過收購傳統的汽車廠,去改造它。但汽車業不可能去做IT公司,福特和通用做IT很多年了,是吧。”
看吧!還是在各說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