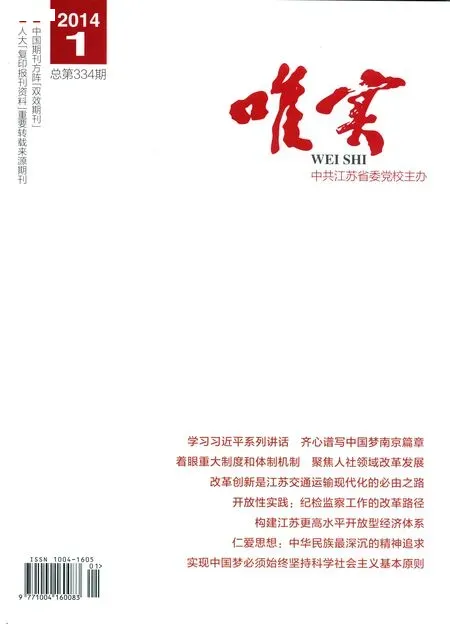構建江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
劉志彪+陳柳

一、構建江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已成當務之急
國際經貿關系格局呈現重大調整的端倪,江蘇作為開放型經濟大省需要提前應對。目前,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力圖通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議)和PSA(多邊服務業協議)形成新一代高規格的全球貿易和服務規則,美國試圖以此另起爐灶建立世界經貿體系的新秩序來取代WTO,全球開放經濟規則的高級化成為一種趨勢。江蘇有必要未雨綢繆,針對TPP、TTIP以及多邊自貿區對國內和省內產業造成的影響作出評估并進行調整,盡可能提前適應國際新規則。
江蘇省傳統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與國內外經濟的新形勢呈現出一定的不適應、不協調。江蘇的外向型經濟依靠大力發展開發區、吸引FDI(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就,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外經濟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摩擦加大,國內勞動力等要素價格持續上漲、生態環境壓力加大,歐美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等。這些條件的變化使江蘇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傳統方式難以適用。比如,江蘇一直是外資高地,但是,當前,蘇州等地的外資正在加速向中西部轉移,蘇南開發區對傳統工業的承載能力接近飽和。對此,我們迫切需要新的手段和方法。
上海自貿區已經開啟,其他東部省市制度創新舉措不斷,江蘇省開放經濟的優勢不進則退。江蘇充分利用了我國加入WTO第一波全球化的紅利,獲得了先發優勢。為爭取新形勢下開放格局的主動,除上海自貿區外,深圳前海、福建平潭、珠海橫琴等東部地區在最近幾年獲得了較多先行先試的機會。如果江蘇不迎頭趕上,那么,在開放經濟的新一波紅利釋放階段就可能落后。
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經濟體是倒逼江蘇省改革的重要手段。過去30多年的實踐表明,通過擴大開放,可以引入競爭、形成示范,對國內各項改革形成倒逼,為發展增添動力。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旋律就是改革,在開放條件下建立國際通行的規則,可以盡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徑依賴,將改革向縱深推進。
二、江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的主要表現
江蘇的開放型經濟發展一直領先于全國,發展水平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那是針對過去單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而言。為了主動適應世情、國情、省情的新變化,江蘇必須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通過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來進一步利用全球資源,為“兩個率先”注入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活力。“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是“升級版”的開放型經濟,主要表現為:
江蘇要為世界提供更大、更開放的“中國市場”。單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簡單地利用別人的市場實現增長,新一輪開放型經濟要轉而實現資源的全球配置,尤其是要重視自身的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因此,從現在起到2020年,在國家實現關稅總水平比當前水平大幅度降低的同時,江蘇首先要爭取破除一系列自己可以掌控的省內市場的行政壁壘和進入管制,使開放度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加強與最不發達國家、低收入國家的合作。在國家層面對世界最不發達國家分商品實施零關稅待遇、擴大援助之前,江蘇可以首先考慮在2020年前進一步擴大與最不發達國家、低收入國家的貿易往來。如可以考慮給予最不發達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更多的無償援助和人力資本援助等,利用“促貿援助計劃”促進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鞏固江蘇作為最不發達國家出口大市場、大貿易伙伴的地位,還要成為他們的官方援助(包括金融貸款援助)、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內最大省份。
江蘇也要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進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服務便利化,尤其要大力開放和發展服務業,建設服務貿易強省。新一輪的開放主要表現為服務業的開放。為此,可以考慮江蘇服務貿易進出口保持30%以上的年均增速,力爭到2020年服務貿易總額比目前翻兩番,占全球服務貿易比重大幅度上升,超越新興小國市場經濟國家,成為國內服務貿易第一省。服務貿易是創造就業的新領域,特別適合于數量眾多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
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重點是培育跨國龍頭和創新型企業國際化。力爭在2020年以前保持年均30%以上的對外投資增長,使江蘇2020年對外直接投資額至少比目前翻兩番。培育一批江蘇走出去的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鼓勵和支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和世界2000強企業、世界同行業前列、世界知名品牌行列。
提高國際話語權,逐步掌握對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能力。在國際組織中增加江蘇人、江蘇項目、江蘇文化等江蘇元素。通過率先建設創新型新省份,江蘇要把在全球價值鏈的底部進行國際代工的角色,改造為在全球創新鏈的中高端進行“江蘇創造”的分工角色,為整個國家爭取核心利益。
為打造江蘇開放型經濟升級版,構建江蘇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需要實現幾個“轉化”。
政府功能上,從政府強勢推動轉向通過制度設計增強市場微觀基礎活力。通過政府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審批等方式增強市場活力,實現微觀主體更加活躍。動力機制上,從出口導向轉向利用開放體系的高級要素實現內外融合發展。在穩定外資和外貿的基礎上,積極利用國內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規模效應的支持,發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國高級要素為我所用,建設各種內需平臺,集聚國外高級要素為擴大內需服務。產業目標上,從被動嵌入全球價值鏈轉向逐步主動實現全球價值鏈的控制力。通過支持企業增強核心技術開發能力和品牌營銷能力實現全球價值鏈的攀升,對跨國公司實施“反控制”、“反鎖定”,擺脫價值鏈的從屬地位和跨國公司的“依附性”。將高級生產要素普遍內生化,將本土企業打造成全球價值鏈的鏈主。微觀主體上,從吸引FDI轉向著力培育江蘇的大型跨國公司。將引進外資的工作轉移到提升層次和水平上來,重點支持國內大型企業在全球范圍通過跨國并購、股權置換、境外上市、聯合重組等方式,增強本土企業國際化的經營能力,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結構轉化上,從“江蘇制造”的競爭優勢轉向重點發掘“江蘇創造”、“江蘇服務”潛力。鼓勵企業出口從傳統的生產成本優勢向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新優勢轉化,增強外貿企業自我轉型的內生動力,加快服務業開放,發展服務貿易,加快培育出口競爭新優勢。合作范疇上,從單一的投資貿易對外合作轉向全方位、多層次對外合作體系。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內涵不僅包括對外貿易、跨境投資、國際金融等,而且還要與國際合作、境外援助、全球治理等領域形成協同效應,加強技術、環保、人才、文化交流的多維合作,提升國際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endprint
三、構建江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現實路徑
以TPP、TTIP、上海自貿區等的有益原則倒逼政府部門體制改革。TPP、TTIP等的要求雖然主要代表了發達國家經濟體自身發展階段的訴求,但不少規則符合江蘇當前市場發展和經濟升級的內在規律要求。TPP不僅要求成員所有產品實現零關稅、服務貿易全面開放、實質性取消外資審批,還引入了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勞工權益、國有企業競爭中立等升級條款。這些要求并不妨礙我們利用有益的成分指導當前的開放經濟工作,尤其是利用市場化的原則倒逼體制改革,促進政府部門加快簡政放權,增強市場活力。上海雖然在自貿區建設上先拔頭籌,但如果江蘇能夠按照國際規則和標準提前加快開放經濟的制度建設,一旦中央政府更大范圍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改革,那么江蘇將在新一輪開放中大大受益。
靈活運用先行先試政策。研究前海、平潭、橫琴等地的先行先試政策在我省的適用性,考慮在省一級政府的權限內率先推進吸引國際化人才等政策。這些政策涵蓋通關、稅收、金融、人才、土地等多個方面,有些內容江蘇可以爭取,有些內容江蘇可以利用自身條件先試。對于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江蘇也可以由政府按內地與境外個人所得稅負差額給予補貼,并對差額部分個人所得稅減免;可以建立各類境外專業資格的規范化認可制度,盡快出臺境外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士在江蘇開展相關服務的制度;對設立試點區的土地使用指標,省政府也可以單列,并進行政策傾斜。
在雙邊協議中做出特色,為江蘇構建新型開放載體,乃至建設自貿區熱身。現階段,ECFA(經濟合作框架協議)、CAPA(亞太會計師聯合會)是重要的雙邊貿易協定,而蘇臺、蘇港合作是我省開放經濟的重要特色,ECFA、CAPA等制度框架在江蘇理應落實得更好。根據昆山和臺灣的產業優勢正在實施的“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建設,就可以借鑒平潭對臺資開放的模式,爭取相似的政策條件。充分研究上海自貿區的重大借鑒意義,力爭創新若干開放載體試點,加大對各類海關特殊監管區的功能整合,支持全省出口加工區積極創造條件升級為綜合保稅區,加強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聯動。力爭在南京、蘇州、連云港三個區域性國際商務中心和蘇州創新示范區形成先行先試的條件。
強化服務功能,加強國際經貿網絡建設,整合江蘇海外經貿代表處。優化海外網絡布局,加強與經貿往來密切國家聯系,加快海外經貿代表處和中介組織工作網點建設,強化駐外機構功能,實現統一協作,重點建立貿易摩擦海外預警、對外合作園區協調、大型跨國公司聯絡等功能。順應雙邊FTA(自由貿易協定)逐步成為國家和區域間貿易談判的趨勢,江蘇努力利用中國與東盟、新加坡、新西蘭等簽訂了雙邊FTA。加強這些國家或地區的項目推介力度,積極探索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園區的可行性,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機會。
解決重要民生領域供給瓶頸,制定江蘇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舉措。在民生服務業領域擴大開放、吸引優質資源進入市場,既是開放工程,也是幸福工程。比如,近一段時間輿論反映突出的全國很多城市優質兒童醫院資源嚴重不足的現象,在江蘇南京等大中城市也很突出。這就可以考慮在ECFA框架下落實細則,引進臺資相關醫療機構。
形成更為高效綜合的管理體制,積極為對外經濟工作的機制體制改革創造經驗。進一步加強對擴大和深化開放經濟工作的領導,統籌全省開放布局、開放重點、體制機制創新等工作,建立涵蓋商務、海關、外匯、質檢等的多部門協調的工作機制,加強各部門在開放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協作,共同促進開放型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提高服務效能,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積極探索多部門協調工作的組織形式和機制,積累放松政府管制的經驗,力爭為全國開放經濟工作的改革提供借鑒。
(劉志彪:江蘇省社科院院長;陳柳: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戴群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