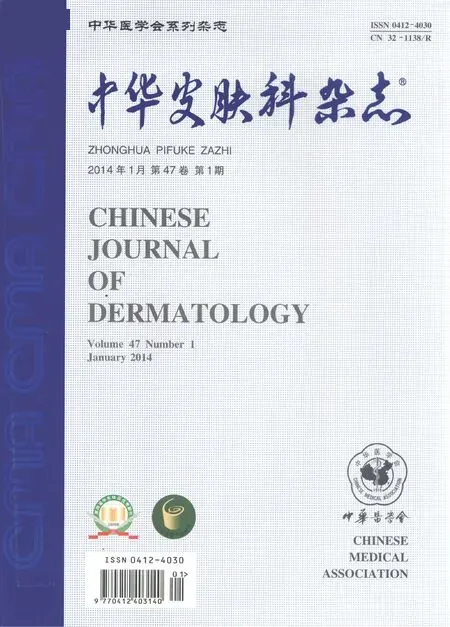皮膚微生態的研究進展
方紅
·專論·
皮膚微生態的研究進展
方紅
皮膚微生態學是研究皮膚微生物群的結構、功能及其與人體相互關系的一門生態學科,即皮膚的細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生態學,它是微生態學的一個分支[1]。皮膚是人體內外環境交界的一個生物活性界面,皮膚的生態環境為微生物群的定居和繁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所。30年前已有相關研究顯示[2],皮膚表面棲居著大量的微生物群,包括細菌、真菌、病毒、衣原體和某些原蟲等,它們與人類在共同的歷史進化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生態結構,稱之為皮膚正常微生物群。以往曾認為它們是“無用的”,甚至是“致病的”,近年來隨著研究手段和方法的不斷進展更新,尤其是微生物分子生態學的發展,宏基因組學技術的應用,使得人們改變了傳統的認識,對皮膚的正常微生物群與宿主、環境之間的生態體系即皮膚微生態有了深入的了解。
一、概述
皮膚微生態的研究顯示,皮膚常駐菌具有占位保護作用,有層次有序地定植在皮膚上,猶如一層生物屏障,使致病菌及外籍菌無法立足于皮表;多達20%的常駐菌可產生抑制病原菌的化合物。如革蘭陽性共生菌,包括乳酸菌、鏈球菌、葡萄球菌可產生殺菌素,表皮葡萄球菌可產生一種抗菌肽酚可溶性調控蛋白(phenol soluble modulin,PSM),對金黃色葡萄球菌、A組鏈球菌、大腸桿菌具有選擇性殺滅作用,但不針對其他表皮葡萄球菌及常駐菌[1,3];常駐菌可分解皮脂甘油三酯為脂肪酸,形成乳化皮脂膜,既對自身及表皮角質形成細胞具有營養作用,又可防止皮表水分蒸發,由于呈弱酸性可抑制一些化膿菌及皮膚癬菌的定植;一些暫駐菌中的機會致病菌作為抗原刺激機體免疫系統,促進免疫器官發育,增強機體免疫功能[2]。相關研究顯示對皮膚致病菌的保護性免疫有依賴于皮膚正常微生物群而非腸道微生物群[4]。
正常皮膚每平方厘米定居著大約100萬細菌,有上百種的類型,用傳統的皮膚拭子和活檢標本培養,在標準的實驗室條件下能培養到的細菌真菌等尚不及1%,而且許多細菌和真菌的生長會被生長更快的微生物群超過,其結果只能得到易培養的細菌或真菌種群,如葡萄球菌和馬拉色菌等[5]。因此,單靠傳統的培養鑒定方法,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人們無法對皮膚微生態進行深入研究。
二、宏基因組學的發展開拓了人們對皮膚微生態學研究的新思路
宏基因組學(metagenomics)又稱微生物環境基因組學,是1988年由Handelsman等率先提出的[5],為免培養直接提取特定生境中全部微生物(包括可培養和不可培養)的總DNA,對微生物群的基因總和進行功能基因篩選和(或)測序分析的一種新的應用學科。它包括下列4個步驟,即生態區樣本中微生物群總DNA提取,宏基因文庫構建,序列測定分析以及功能基因篩選鑒定。分析細菌微生物群的方法包括擴增原核生物的小亞基核糖體RNA(rRNA)和用PCR直接擴增來自皮膚樣本的基因。16SrRNA基因存在于所有的細菌和古生菌,包括保守區域作為PCR引物的結合點,可變區域用于PCR產物的高通量測序后的系統分類。將>97%相同的序列歸為一個操作分類單元(operational taxonomy unit,OTU)。在一個物種中,序列的差異被假設為是種內的種屬變化。在1個物種中,序列的數量代表這個種屬在生態區樣本中的相對豐度。宏基因組學方法通過對所存在的種屬鑒別及其相對豐富度,可提供皮膚微生態正常細菌群落的全景象圖。對于真菌生物通常選擇18SrRNA基因和內轉錄間隔區進行真菌通用引物的PCR擴增。
采用宏基因組學方法,研究者們已著手對皮膚不同生態區的微生物群的多樣性、種群結構、進化關系、功能活性、相互作用以及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研究。
(一)建立皮膚正常微生物群數據庫:2007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采用宏基因組學方法啟動了人類微生物組對242例健康成年人的微生物含量的研究計劃,最近公布了人類微生物基因序列的參考目錄,包括整個基因組及16SrRNA基因序列的數據庫[5]。通過該項系列研究及近10年的相關研究,人們較為全面地了解了健康人群的皮膚微生物組群在不同的空間、時間和個體變化。人們發現人類皮膚在胚胎期宮內環境中是無菌的,但由于人類生存在一個充滿微生物的環境中,出生后的幾天內,新生兒皮膚表面很快出現細菌等微生物,最初定植較為簡單的低多樣性微生物,如早期以葡萄球菌為主,在生后第一年其數量顯著下降有助于增加其他細菌的定植。嬰幼兒皮膚以厚壁菌為主。隨著皮膚的功能、結構的持續完善,不同部位的皮膚由于濕度、溫度和腺體分泌的不同出現越來越多樣性的微生物群,且隨年齡的增長、不同環境的接觸、不同的遺傳背景而發生一些改變。
最近一項研究對28名2~40歲的健康人皮膚正常菌群進行了評估[6]。結果顯示,兒童各部位皮膚細菌群落與成人有明顯不同,最為顯著的改變是在鼻孔,兒童以厚壁菌門(鏈球菌),擬桿菌,變形桿菌占優勢,成人則以棒狀桿菌屬和丙酸桿菌屬占優勢,兒童鼻孔可以隱藏更多的潛在的致病菌種,如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鏈球菌。隨著年齡的增長,到青春期后,會被親脂性的細菌和其他細菌如表皮葡萄球菌所替代,這或許可解釋特應性皮炎患者在青春期后病情會明顯減輕。
利用16SrRNA測序的宏基因組學研究顯示,成人皮膚菌群和腸道菌群的絕大多數可分為4個門:放線菌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和變形菌門,在這些門中存在上千種特殊種類。例如,一項關于51位健康志愿者手掌微生物的研究顯示,有4 742種特殊類型,平均一個手掌上有158種類型[7]。
新近研究發現,正常皮膚微生物群不僅存在皮膚表面,在真皮層和脂肪層組織以往一直認為是無菌的也能檢測到細菌,這些皮膚的正常共生菌與基底膜下方的宿主細胞之間進行相互接觸、信息交流[8]。有研究[9]表明,如在人生早期階段,及時建立正常皮膚微生物群對于阻止外來感染性微生物的入侵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有助于建立皮膚的穩態和調節炎癥反應,并可顯著影響皮膚免疫功能的發育。盡管正常皮膚微生物群在不同個體或同一個體的不同部位之間存在差異,但與皮膚處于一個相對平衡狀態[10]。
對20個不同皮膚生態區的微生物研究顯示,相似的生態環境如腋下和腘窩有相似的微生物構成。所有個體,痤瘡丙酸桿菌在皮脂腺豐富的生態區,如前額、耳后皺褶處和背部占優勢。葡萄球菌和棒狀桿菌則在潮濕的部位如腋窩占優勢。
除了不同的物種組成,每個生態區有其特有水平的微生物群多態性和暫時性的波動。例如,不同受試者的肘窩在物種構成上有很高的多態性,稱之為β多態性。但對于同一個體的肘窩卻很少有多態性,稱為α多態性。研究者發現將微生物群從一個棲息地移植到另一個棲息地,如從舌部移到前額,這些舌部的微生物群僅短暫地出現在前額,最終又恢復到前額的微生物群。
人類皮膚任何生態區,除了最為豐富的丙酸桿菌、葡萄球菌、棒狀桿菌三大屬以外,大部分微生物的種屬構成少于總菌群的1%。這些少數的物種以往未能得以很好的認識,且以往的研究方法人們也無法知道其在皮膚定植。如以前認為革蘭陰性微生物很少定植在皮膚,但采用宏基因組學方法研究者發現干燥的皮膚生態區如前臂或腿部,也有著豐富的革蘭陰性微生物群。這些低豐度的物種不僅被發現,有些可能是皮膚生態系統的關鍵菌群[11]。
(二)正常微生物菌群結構改變與皮膚病的關系:
1.痤瘡:最近Fitz-Gibbon等利用宏基因組學和基因測序相結合方法[12],在菌株水平和基因水平比較了49例痤瘡患者和50例健康人鼻部皮脂腺單元的皮膚微生物群。他們將每個樣本的16SrDNA進行擴增,對約400個克隆測序,平均分析了311個幾乎全長的16SrDNA序列,比較了71個基因組,發現痤瘡患者和健康人鼻部痤瘡桿菌的相對豐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核糖體型1(RT1)和RT2、RT3痤瘡丙酸桿菌菌株相當均勻地分布于痤瘡患者和健康人鼻部。但痤瘡患者中RT4和RT5痤瘡丙酸桿菌的菌株占優勢,RT6菌株則主要見于正常人群的鼻部。提示RT4和RT5痤瘡丙酸桿菌菌株與痤瘡的發病密切相關,RT6菌株則與健康皮膚相關。該項研究從菌株水平分析了共生菌痤瘡丙酸桿菌的不同菌株在痤瘡發病中的作用。這給人們帶來啟發,今后痤瘡的治療有必要采用微生態制劑來調節皮膚微生物群使其回到健康的菌群結構狀態,即進行自然共生菌結構的靶向治療,而非采用抗生素來殺滅所有的痤瘡丙酸桿菌。
2.特應性皮炎:特應性皮炎是一種慢性復發性炎癥性皮膚病,在美國大約15%兒童發病,通常認為其病理機制包括表皮絲聚合蛋白缺陷所致的屏障功能受損,金黃色葡萄球菌定植和免疫超敏反應。用培養方法可確定金黃色葡萄球菌定植和感染常與其發病相關。因而經驗性治療措施包括采用抗生素和類固醇激素。宏基因組學研究[13]顯示,在AD的發作期金黃色葡萄球菌比基線時或治療后要明顯增多,并與疾病的嚴重度密切相關。治療后鏈球菌屬、丙酸菌屬、棒狀桿菌屬增加。但令人驚訝的是,急性發作期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均增加,葡萄球菌物種從35%增加到90%,且與發病無關的非葡萄球菌在豐度上也發生改變。進一步的研究顯示,表皮葡萄球菌可產生一些細胞因子如,PSM選擇性地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雖然目前還無法解釋表皮葡萄球菌的增加是為了拮抗金黃色葡萄球菌還是由于與金黃色葡萄球菌相互作用促進彼此定植。但這一結果提示特應性皮炎的發病可能與皮膚正常微生物群的結構改變和失衡有關。
3.銀屑病:Fahlén 等[14]采用宏基因組學方法研究10例銀屑病患者皮損(活檢標本)處菌群結構變化并與12例正常人皮膚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銀屑病患者軀干部皮損變形菌的比例較健康人皮膚明顯增加(分別占52%和32%,P=0.0113);銀屑病皮損中鏈球菌屬占32%,而健康對照為26%;另外皮損中葡萄球菌和丙酸桿菌含量則顯著低于健康人皮膚。這項研究提示,銀屑病皮損其菌群結構有別于健康人皮膚。這些差異是否是導致銀屑病發病的病因還是繼發于銀屑病的病理改變而改變,尚待研究。
三、結語
皮膚的微生物群可能通過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對人體的生理和疾病產生影響,動態平衡機體的免疫應答,需要我們對其變化加以重視。科學家們雖然能夠將某種疾病與某些微生物的存在或缺乏相聯系,卻無法將許多疾病的“罪魁禍首”鎖定在某種病原微生物上。事實上,很可能是多種微生物群落的結構變化起著共同的作用。盡管宏基因組學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手段,但皮膚微生物群組成結構改變與皮膚病關系的研究還僅是一個開端,目前的工作大多局限于對細菌菌群的改變,對其他微生物群的變化了解甚少。皮膚微生態這一微妙神奇的世界仍然有太多的東西值得人們深入了解。如微生物群是如何影響皮膚的信息儲存和新陳代謝?為何不同個體同一生態區微生物構成有所不同?相信隨著皮膚微生態與皮膚病之間相關性的深入研究,對皮膚微生物的調控有可能成為一種相關皮膚病的預防和診治手段。
[1]李蘭娟.感染微生態學[M].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3,208.
[2]Webster GF.Skin microecology:the old and the new[J].Arch Dermatol,2007,143(1):105-106.
[3]Cogen AL,Yamasaki K,Sanchez KM,et al.Selective antimicrobial action is provided by phenol-soluble modulins derived from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a normal resident of the skin[J].J Invest Dermatol,2010,130(1):192-200.
[4]Naik S,Bouladoux N,Wilhelm C,et al.Compartmentalized control of skin immunity by resident commensals[J].Science,2012,337(6098):1115-1119.
[5]Chen YE,Tsao H.The skin microbiome:current perspectives and future challenges[J].J Am Acad Dermatol,2013,69(1):143-155.
[6]Oh J,Conlan S,Polley E,et al.Shifts in human skin and nares microbiota of healthy children and adults[J].Genome Med,2012,4(10):77.[Epub ahead of print].
[7]Fierer N,Hamady M,Lauber CL,Knight R.The influence of sex,handedness,and washing on the diversity of hand surface bacteria[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08,105(46):17994-17999.
[8]Nakatsuji T,Chiang HI,Jiang SB,et al.The microbiome extends to subepidermal compartments of normal skin[J].Nat Commun,2013,4:1431.
[9]Capone KA,Dowd SE,Stamatas GN,et al.Diversity of the human skin microbiome early in life[J].J Invest Dermatol,11,131(10):2026-2032.
[10]Kim BS,Jeon YS,Chun J.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mise of the Human Microbiome[J].Pediatr Gastroenterol Hepatol Nutr,2013,16(2):71-79.
[11]Zhou Y,Gao H,Mihindukulasuriya KA,et al.Biogeography of the ecosystems of the healthy human body [J].Genome Biol,2013,14(1):R1.[Epub ahead of print]
[12]Fitz-Gibbon S,Tomida S,Chiu BH,et al.Propionibacterium acnesStrain Populationsin the Human Skin Microbiome Associated with Acne[J].J Invest Dermatol,2013,133(9):2152-2160.
[13]Kong HH,Oh J,Deming C,et al.Temporal shifts in the skin microbiome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flares and treatment in children with atopic dermatitis[J].Genome Res,2012,22(5):850-859.
[14]Fahlén A,Engstrand L,Baker BS,et al.Comparison of bacterial microbiota in skin biopsies from normal and]psoriatic[J].Arch Dermatol Res,2012,304(1):15-22.
2013-10-21)
(本文編輯:吳曉初)
10.3760/cma.j.issn.0412-4030.2014.01.001
310003杭州,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皮膚性病科
方紅,Email:fanghongz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