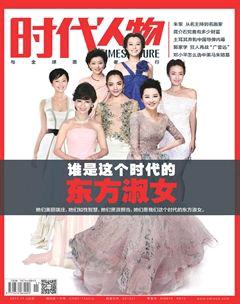“憑自己的良心去書寫歷史”
時代人物:據說《北平無戰事》創作7年,投資方7次更改,因為這里面有風險,你覺得風險來自哪些方面呢?
劉和平:風險無非是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是認為這部劇與現代主流收視人群接不上,收視一失敗也就意味著投資的失敗。這個擔心我覺得他們也是對的,大家都形成了這么一種共識,覺得主流收視人群一般都是看不懂這個戲,也不會喜歡看這個戲。另一個原因比這個原因那就更可怕,擔心審查通不過。盡管這樣,他們不少人都是舍不得這個項目,希望我能不能多考慮一下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做修改,一是盡量迎合今天的主流收視人群,二是盡量收斂一點,降低過審風險。他們都很有誠意,但你想這兩個方面我都不可能妥協。因為一妥協就不是今天這個《北平無戰事》了,這個劇我是有整體的構思,也有自己的總體追求、構想和目標,它無法討價還價。
時代人物:最后這家投資方是怎么確定的呢?
劉和平:最后這個投資方,我跟他們說,你們有沒有一種信念,你們以一億甚至一億多的資金來投資這部劇,而我用接近晚年的6到7年的生命來投資這部劇,我這不是時間是生命。我不是年輕人,創作《北平無戰事》,我從53歲到60歲,這7年,可以說是7年的生命黃金期,我不會對自己的生命和時間不負責任,是不是。
我說,如果我來經商,以我的智商和我的人緣,7年賺一個億沒問題;但是我選擇了創作這條路。后來也是這種誠意感動了對方,感動了以后在取得對方高度信任的前提下,把控權給了我。這也是事實,因為你想我們這個戲,大家都能看到我還打了個名字,叫總制片人,但是在我們內部有一個名字應該比這個還要高,因為這個戲有一個核心決策團隊,叫制作小組。制作小組就是兩個投資老板加我,3個人,投資成本多少?請什么樣的團隊來拍?選什么樣的演員?達到什么樣的制作高度?最后投資最高控制在多少?最低不少于多少?這都要三人制作小組做決定,最后公推我為制作小組組長,在協議上寫了一個我有一票否決權。
時代人物:其實《北平無戰事》遭遇重重障礙,一方面是審查原因,另一方面是宏大敘事與家國之憂與現在的娛樂氛圍不搭。你怎么看待現在這種文藝思潮整體都追求淺表娛樂?
劉和平:它是一個合理的存在。西方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經歷了400年,我們才短短40年。要完成從農業文明的傳統到工業文明,乃至于后工業時期信息化時代的現代人,怎么變?最快的途徑就是讓人瘋狂的填鴨式的去接受西方那種娛樂信息。我曾經跟湖南廣電的魏文彬對過話,他就問我,你怎么看待湖南廣電和湖南衛視?就我們娛樂化程度這么高。我說你們對把中國這些人從傳統人變為現代人是有功勞。他說這個怎么講?我就說了這個道理,一群剛剛還在山溝溝里的人,只要看了湖南衛視,他走到城里來,不過半年就分不出他是農村人還是城市人,從穿著、打扮、唱歌、言談、舉止,就立刻過渡到了城市人——當然,他的骨子里還是農民。這個就是我反過來又要說的,這種催生的辦法,把一個人變成真正的現代人是不可能。但是,這是我們轉型期無法回避的一個階段。等到我們把娛樂的這種程度適當的降低、步伐放慢,再去多追求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的時候,可能我們就開始回歸到成熟和理性。
但現在這個階段肯定會出現,它又沒有不合理,它是自發出現的現象,不要去說人家搞娛樂不對。使傳統人變為現代人,最快的辦法莫過于娛樂,只是這種現代化是淺表的,沒有了精神和理想對于一個民族是很可怕的,所以我相信這種狀況只是暫時的。
時代人物:《北平無戰事》劇中的道具極為考究,你覺得歷史劇除了史實考究外,還應具備哪些特質?
劉和平:歷史劇需要尊重歷史的真實,但如果每件事,都按照史書記載寫出來,那它肯定不是歷史劇。看歷史劇,就應該看這部歷史劇是不是傳達歷史之神?它對歷史文化的真實和歷史精神的真實有沒有走樣?如果一個人看文藝作品的時候,卻拿著二十五史對照下來,這樣就沒有所謂的歷史題材作品了,《三國演義》《水滸》等也都沒有了。
時代人物:你在創作歷史劇時,追求一種怎樣的真實?
劉和平:之前曾經有人把戲劇界的歷史劇分為3種,即寫真史劇,如吳晗的《海瑞罷官》;演義史劇,有一定的歷史依據,更多的是側重演義;還有就是很難創作也達到了一定高度的傳神史劇,傳歷史之神,追求歷史文化、歷史本質的真實。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就想把《雍正王朝》寫成傳神史劇,所以我不承認它只是“清宮戲”的原因就在這里。現代人看了這部戲既能感覺到強烈的現實關照,但誰也不能說它不是歷史劇,就是因為它傳了歷史之“神”,我追求的就是這個“神”,也就是藝術的真實。
時代人物: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對當今生活有怎樣的影響?
劉和平:我們看歷史就是看它的文化,看歷史上形成了哪些文化符號在深刻地影響著每一代人的文明進程和生活。
從來沒有人敢說,我們今天的文化與祖祖輩輩的文化沒有關系。歷史從來就是深刻地影響著后世。在這一點上,所有的歷史學家基本上都持一個觀點: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現實永遠是歷史的延續和發展。
因此,我們在任何一個現實時空中回顧歷史、重提歷史,甚至把它寫成歷史題材的作品,都是與現實密切相關的。對此,完全粗暴地用影射、翻案來界定是錯誤的,它們不是歷史劇的代名詞。如果說,現實生活與歷史題材作品有強烈的關照和感情共鳴,也可以說,我們今天的文化是來自于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依然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今天所有的人。
時代人物:一直以來,只要是出自你手的歷史劇,都堪稱精品,你是如何做到的?
劉和平: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高密度思維的產物,而這種高密度的思維都要通過準確的文字表現出來。作為編劇,他的語言風格、思維方式無不體現了這種唯精唯一的態度。作品是創作者本人和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綜合發生關系所碰撞出來的焦點。文化和藝術要走在生活的前面,但是搞歷史劇創作,要注重以歷史文化作為根基。
時代人物:好像現在的編劇圈言必稱美劇,也總用好萊塢的那一套來套內地電視劇。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劉和平:有一點我很明確,就是我們確實要去學習國外的尤其影視藝術上面的一些先進經驗和先進的表達,藝術表達和藝術表現都要學習,但是始終不要忘記一點,他們的那種手段和形式,都是表達他們自己的文化形態。現在我們去學他的形式,但表達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形態,這才出現我們最大的問題。電影和電視劇都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中國卻是個農業文明為主要文化形態的國家;現在影視的手段和形式都是人家工業文明下發現和總結的經驗,在中國并不一定合適。怎么能夠很好地把人家的那種形式和我們自己內在的文化形態結合起來,這才是重點。從《雍正王朝》,包括《大明王朝》到現在,我能堅守的一點,就是怎么樣運用他們的器來表現我們的道——用他們的手法來展示中國人所處的歷史環境、人情世故、情韻態度。
時代人物:我們時常聽到編劇抱怨創新難,在這一方面,你的創作經驗是什么?
劉和平:優秀的電視劇一定要有自己的立意和創意,立意是指創作時一定要找到隱藏在我們現實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質和意志。創意是整個創作過程中的產物,它充滿在寫劇本的整個過程之中,有時也可能是我們創作之前大家在一起討論的一個點子,但那個點子很可能在你創作的時候并不合適。創意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不斷地尋找藝術形象的過程,只要你找到他們,可能這個時候你的作品才會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不可復制性。這就是眾里尋他千百度,不是一次就能找到的,而是一個尋找的過程。一旦尋找到了,它就像遠方的一盞明燈,那盞燈是不會變的,但是怎么走是可以變的。前面定的調子是不會變的,而后越來越豐富,往那個方向去靠攏。
總之,我認為,編劇創作應該憑自己的良心去寫,憑著正確的價值取向和感情傾向去寫,只有這樣我們就有自信會是一個不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