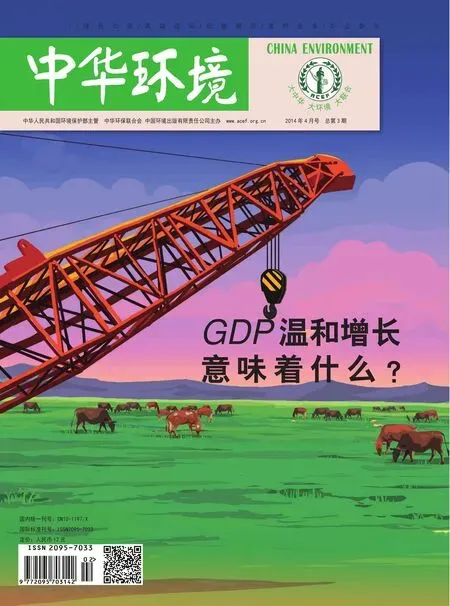卷首 資本和權力如何分配?
卷首 資本和權力如何分配?
編輯第二期雜志的過程中,編輯部的同事們始終糾結于“環境權”的問題:環境權這種提法準確嗎?為什么在發達國家環境權沒有入法?生存權不能涵蓋環境權嗎?整個編輯過程竟成了大家學習和統一思想的過程。
此時提出環境權,是環境保護形勢所迫,2.8億人使用了不安全的飲用水,20多個城市飽受著霧霾之苦,人們本應享有呼吸新鮮空氣、飲用干凈水等最基本的環境權被嚴重忽略。在夏光《邁進環境權益時代》一文里我們認識到:環境問題的本質是人類生存需要和承載人類經濟活動兩種功能發生了沖突,生產性環境權益侵蝕了生存性環境權益,污染侵蝕了健康。出于經濟優先的客觀現實需要,生存性環境權益不得不給生產性環境權益“讓路”。現在人們享有清潔和安全的生活環境放在較高的位置,更強地反映生存性環境權益的需要,提高了環境保護的門檻和強度,突出了環境保護的民生價值目的,與當前我國提出建設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的戰略目標是相符合的。
為了保障公眾的環境權不再受侵害,必須在制度設計、政策制定、市場導向和技術扶持等方面全方位傾斜于環境保護,從原來經濟優先轉型為經濟與環境保護并重。今年我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目標定為7.5%,就是個信號,持續高速發展的經濟占用了大量的資本和權力資源,在經濟政策刺激下,環境保護的危機提早到來,致使整個社會不得不重新考量其配比。
但同時也要防止矯枉過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不應該割裂或對立起來,既反對權力和資本集中于經濟發展,又要反對集中于環境保護。事實證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非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據專家測算,《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付諸實施,將增加非農就業崗位260萬個,1元大氣污染防治投資可以拉動GDP增加1.25元,環境保護的“加法”與經濟發展的“減法”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關鍵是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建立起良性互動關系,以發展為環保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術保障,以環境改善目標倒逼經濟轉型升級,這是7.5%的現實意義。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保護生態環境關鍵靠制度,7.5%能不能實現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維護經濟、民生與環境的平衡,法治和制度是重要力量。通過法律規范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明確社會各方自已的責任,提高破壞環境的違法成本,才能真正樹立起對環境和生態的敬畏;對于那些仍不能迷途知返者,需要出重拳揮利劍,以更嚴格的監管、更嚴厲的處罰、更嚴肅的問責,打擊污染環境的“傷天害人”行為,打擊監管中的失職瀆職行為。
因此能不能把環境擺在正確的位置,使權力和資本平衡運用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中,檢驗著治理者的眼光和能力。
《中華環境》編輯部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