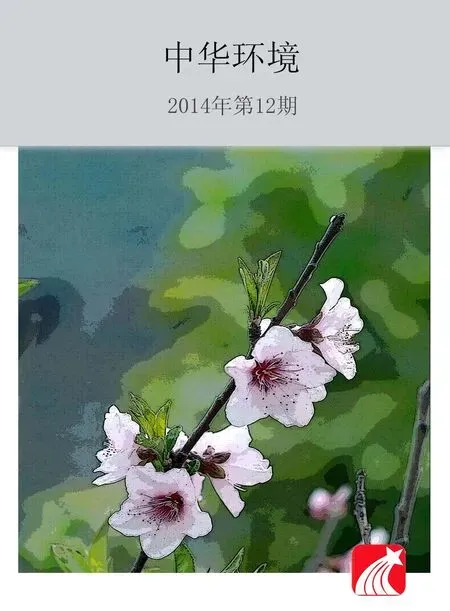慈善捐助怎樣尊重受助者感受?
杜江茜
慈善捐助怎樣尊重受助者感受?
杜江茜
回顧這些年,從陳光標備受爭議的“暴力慈善”,到校園里久被詬病的助學金“比慘”評選,資助者期待得到的贊揚和感恩與受助者保留隱私和尊嚴,似乎總是“難以平衡”。
14歲的四川女孩玲玲(化名),最近正因為“被資助”而備受關注。因態度“冷漠”,她在第一次見到資助了自己4年的好心人馮師傅后,馮師傅表示,將拒絕繼續資助。媒體繼續調查發現,玲玲所謂的“冷漠”,是因為自己糾結的自卑感和自尊心,不知道如何面對資助人。
“究竟是玲玲不懂事,還是老馮太虛榮?”此事引發上萬網民激辯。一時間,資助者和受助者的關系,二者應有的心態,個人慈善的困局等問題,競相進入公眾視野。
“我會悄悄地提供幫助”
部分網民認為,“拿了別人的錢,見到資助者就該感恩。”但在另一部分人看來,資助者和受助者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后者的隱私和尊嚴,同樣不容“踐踏”。
“在小孩子的成長中,誰天天見得到她,愛護她,她就跟誰親。對一個長期沒有見面的人,孩子是不會有太多感情的。更何況,即使某個人對我有支持和幫助,每個孩子表達感激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看來,玲玲的反應不宜被過度指責。
“事實上,任何小孩面對陌生人都會有壓力,不會第一次見面就很熱情。”這位長期關注兒童福利的社會工作專家向記者感嘆,“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
某師范大學學生李娟,對此深有同感。來自國家級貧困縣的她,一路拿著助學貸款、勵志獎學金、助學金讀到大三。
李娟告訴筆者,她最大的希望是可以快點畢業,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等到自己有能力了,去幫助和她一樣的“苦孩子”。
“但是,我會悄悄地,不會讓他(她)知道我是誰,更不會讓周圍的人知道‘他(她)在被資助’。”李娟抬起頭,認真地說道。
我們需要怎樣的慈善文化
回顧這些年,從陳光標備受爭議的“暴力慈善”,到校園里久被詬病的助學金“比慘”評選,資助者期待得到的贊揚和感恩與受助者保留隱私和尊嚴,似乎總是“難以平衡”。
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慈善文化?
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看來,這已經成了一個亟待重新思考的問題。
令劉開明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他接待的來自美國某大學的考察訪問團。
這個訪問團中,所有參與項目的少數族裔和外國留學生,都由學校全額資助。“甚至不需要你自己申請,學校只要知道你的經濟情況,就會提供資助”。而更打動劉開明的是,學校從不會告訴學生“資助人是誰”。實際上,從這些學生進入中國開始,資助人就以校友的身份,一直陪在他們身邊。
“那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臺灣企業家,他和學生在一起一個多月,卻始終沒讓任何學生知道他就是這趟考察的資助者。他很清楚,拿錢出來不是為了‘被感謝’,而是給年輕的校友提供一個了解中國、走進中國的機會。”劉開明無不欽佩地表示,“他真是充分考慮到了學生的自尊心。”
在童小軍看來,健康的慈善文化中,資助者的支持應該是不求回報的。這意味著,一方面,受助者有權對資助者的探望要求表示拒絕;同時,資助者有權了解受助者的情況,但是這種了解,應該是規律性的。
“比如,在你決定資助的時候,雙方就約定好,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內,受助者定期給我寫信、打電話,讓我知道你的生存和學習狀態。”童小軍舉例,但一個原則是,資助者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資助效果,需要征得受助者的同意。
“特別是對未成年人。除了錢,孩子的成長還有情感需求。資助者可以通過定期交流,給予受助者更多的關懷、鼓勵和正向引導,以便雙方建立起更加親近的關系。”童小軍告訴筆者。
而在中國的“點對點”慈善里,期待受助者有一種感恩的心態,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童小軍看來,“對于個體慈善——尤其是資助未成年人的慈善,資助者對效果的期望,更應該是針對孩子的成年家庭成員的。比如,期望他們能利用你的資助,給孩子更好的照顧,這個照顧包含生活、學業、社會行為,當然也包含感恩教育。”
“我們需要的慈善文化,就是能夠引導和教育受助者和資助者雙方,讓孩子和家人、資助者,都能夠健康地看待資助這件事。”童小軍說。
誰來呵護“冰桶挑戰”背后的個人慈善
從資助玲玲的馮師傅,到給廣西男孩“楊六斤”匯款的善心人士,再到近日紅遍網絡的“冰桶挑戰”,個人慈善在中國蓬勃興起,又似乎難掩脆弱。
馮師傅見到玲玲后停止資助,“楊六斤”所獲500多萬元的捐款遭遇“誰來監管”的追問……一系列問題,直指亟待完善的慈善體系。
“行善也是一種專業化的工作。在健康慈善文化缺失的背后,我們更加缺乏的,是完善的慈善體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華俊感嘆。
高華俊告訴筆者,近年來中國慈善事業快速發展,專業慈善基金會3年間翻了一倍,達到4000多家,民間個體慈善行為也越來越普遍,“‘月捐’、‘日捐’逐步成為一些人的時尚生活方式”。因此,當下對建立現代慈善體系的需求,也就越來越急切。
在專家們看來,我國社會慈善體系的“短板”,仍是專業性的機構和人才。“國外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公益社會,‘個人對個人’的慈善行為并不多見,都是由公益機構去完成的。同時,公益機構有專業的雇員,去‘跟蹤’捐助款項的去向。”在劉開明看來,目前我國的問題是,慈善救助系統不完善,現有的慈善機構不受民眾信任。
“而建立在個人行為基礎之上的慈善關系是脆弱的——資助者隨時可以收回資助,受助者受到的幫助不具有穩定性。此外,還缺少第三方去評估,捐助資金是否得到有效利用、是否達到預期效果。”他表示。
“在健康的慈善文化里,應該有人來告訴資助者,怎么樣的資助動機才是健康的。”童小軍說,“同時,在長期資助過程中,也需要專業人士在監護人、資助人、受助人之間,進行服務和溝通。”
“比如,資助者要見受助者,如果有專業人士在的話,就應該提前就告訴他這個孩子可能會有什么反應,而不是事后再來解釋。像玲玲這個事件,如果馮師傅事先就有對孩子反應的預期,也許就不會如此不理解、失望乃至憤怒,孩子也不會被說成‘冷漠’。”童小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