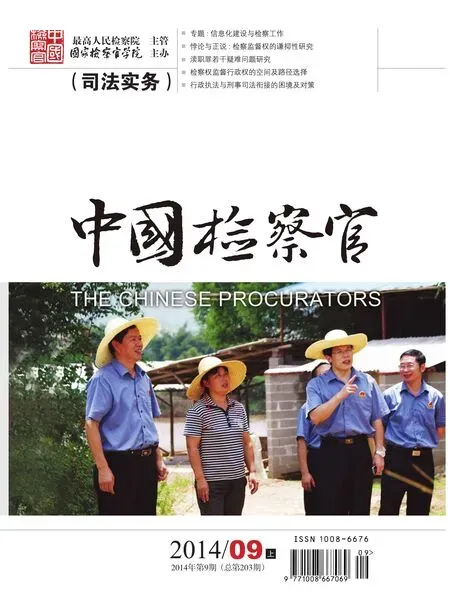悖論與正說:檢察監督權的謙抑性研究
文◎鄧志宏
悖論與正說:檢察監督權的謙抑性研究
文◎鄧志宏*
毋庸置疑,不斷繁榮進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時代在呼喚我們必須堅定加快建設一個嚴正有效的法制社會的步伐。我們必須堅定認真地擔負并切實地完成這一使命。然而在大量的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又須謙抑性地正確處理一些法制建設問題。如何適應和諧社會對法律制度的新要求,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需要怎樣一種全新的角色定位,便成為了現階段一個需要嚴肅討論的命題。
一、檢察監督權謙抑性的概念解讀
(一)檢察監督權的含義及內容
檢察監督權是指檢察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對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糾正,以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一系列訴訟活動的權利,是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性質和職能的重要體現,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檢察院的重要職責。從現有的法律規定看,檢察監督權僅指包括刑事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刑事審判監督、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監督、民事審判監督、行政訴訟在內的監督訴訟監督權和職務犯罪監督權兩大部分。
(二)謙抑原則的含義及功能
檢察權的謙抑性實際上來源于權力謙抑原則。權力謙抑原則是現代法治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其基本含義是,國家公權力機關,特別是司法機關,在行使權力時要保持克制,要盡量避免與其他機關的沖突以及對于公民生活的過度干預。現代法治理念中的權力謙抑原則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在國家公權力機關行使職權時相對于其他國家公權力機關的職權的謙抑,另一個是國家公權力針對公民權利的謙抑。
二、檢察監督權的謙抑性的合理定位
檢察監督權的謙抑性并不意味著檢察機關訴訟監督權力的縮減,而旨在強調訴訟監督權的理性回歸和準確定位,避免由于權力的過度膨脹而干涉其他權力和公民權利的行使。
(一)科學界定監督的內涵和外延
首先,訴訟監督的對象是對公權力的監督,而非私權利的監督,訴訟監督不能指向公民個人,不能以監督為名干涉當事人、訴訟參與人權利的行使,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各項辯護權利的行使。其次,訴訟監督是對司法機關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的監督,不能將監督與正常行使權力下的制約與配合混為一談。最后,訴訟監督是檢察機關對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監督,是同等權力主體之間的監督,這就要求要將訴訟監督與社會生活中一般意義使用的監督區別開來。監督的主體不同,也使得監督呈現出管理、制衡、提示、發揚民主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
(二)承認訴訟監督作用的有限性,避免訴訟監督權力的過度行使
應當明確“檢察機關訴訟監督的作用的有限性。監督的效力主要是依法啟動相應的法律程序或啟動有關機關內部的糾錯機制。”[2]比如偵查監督中,對于檢察機關對于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中發現的違法行為提出糾正意見,僅僅具有啟動偵查機關自身的違法責任追究的作用,并無直接處分違法人員的實體權力;審判監督中,檢察機關對法院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提出抗訴,僅僅是引起法院對已作出判決的重新審查。因此,檢察機關要避免過度的行使訴訟監督,不能以監督權代替偵查權、審判權或者刑罰執行權的行使,破壞分工。同時,對于法院的審判活動,如果法院最終判決與公訴的請求并不一致,此時,檢察機關不應該馬上拿出監督者的身份,而是應該首先從法律上分析,法院是否存在違法裁判。如果只是檢察機關與法院在對法律的理解上有分歧,并且法院的判決并非背離法律規定的違法判決,就不應該進行所謂的訴訟監督。這也體現了抗訴權行使的謙抑性。
三、檢察監督權謙抑性理念的踐行
檢察權的謙抑性理念,沒有相關的制度革新予以配合和保障,是得不到真正有效的體現的,也不會對我國檢察權運作的科學發展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要真正塑造一種以人為本,充滿人情味又不失嚴正的法律監督體系,實現我國檢察權在新形勢下的謙抑化發展,可以從以下途徑進行制度的革新與保障:
第一,刑事政策的修正。檢察權謙抑性理念下,首要的是要修正對刑事政策本身功用的認識,避免那種刑事政策僅僅是一種統治國家、控制社會的工具的錯誤認識。當檢察工作將重點轉移到以人為本這個主題上來,很多改革就會辨清落腳點之所在。一方面,在檢察系統內部,管理規范不能片面追求企業化管理甚至是機器生產的流程管理模式,而是要充分認識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它以適用法律為基本形態,因此因尊重檢察官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在案件的處理上,檢察機關要正確貫徹刑罰個別化的理念,采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我們務須明白,打擊犯罪不是檢察機關的最終目的,我們必須使程序維護與人的解放同時兼顧。
第二,社會調查的制度化。依照上述刑事政策的變革方向,刑事司法必然需要實現一種從粗放化、到精細化、個別化的過渡,而這種過渡必然需要以檢察機關充分掌握行為人的各方面詳盡的背景信息為基礎。在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尤其是刑事檢察工作的時候,也有必要將這種對行為人的全面社會調查予以制度化、普及化。這一做法目前在我國許多地方的未成年人檢察制度中已經有所開展。筆者以為,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在普通的刑事檢察工作中,這一點似也值得推廣。
第三,不起訴制度的拓展。目前我國檢察機關不起訴酌處權,以法定不起訴為主,輕罪不訴在司法實踐中占案件總數的比例非常小,而且把握的適用對象和情節標準均十分嚴格。這樣的現狀顯然大大限制了公訴的裁量權,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不但沒有形成卓有成效的擴展和延伸,反使其在審判權面前自行萎縮。將輕罪不訴的條件嚴格限制在情節輕重的基礎上是不夠完善的,有必要在現在的基礎上擴大輕罪不訴的適用范圍。它并不應該只針對行為人的具體犯罪行為,而是應該綜合考量行為人的背景之后作出的裁量選擇,也就是說,輕罪不訴的決定也應將更多的情理因素納入進來。
第四,檢察建議的多元化。實踐中檢察機關對檢察建議權的運用明顯有僵化、萎縮的趨勢。檢察建議的內容往往只是針對相關單位的不合法現象,實踐中甚至往往以非常明顯的不合法現象為把握標準,監督面過于狹窄,而對于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卻缺乏一種實質性的考量。這種重形式,輕實質的指導思想實際上是大大束縛了法律賦予的檢察建議權能,從而使其社會效果大打折扣。要克服實踐中檢察建議制度的這種局限性,利用檢察建議的手段向社會輸出人性化的法律理念,達致社會道德與法律價值之間的相互認同,從而切實促進社會的和諧,檢察建議的內容有必要實現一種從合法化審查到合理化評價的擴展。
第五,刑事和解的推廣。從法理上看,刑事和解所導致的賠償客觀上起到了修復社會關系的作用。犯罪是對法秩序的破壞,但是一定范圍內被破壞的法秩序得到了修復則表明刑罰失去了適用的基礎,并且和解的前提滿足了行為人通過賠償贖罪以及法益恢復的要求。因此,刑事和解就具備了適用的空間。但是,為防止行為人借民事賠償逃避刑事責任,確保刑罰一般的預防功能,維護刑法的基本公正,刑事和解又必須有所限制,必須由檢察機關進行密切的監控,防止行為人稟性不改卻以錢買刑的丑陋現象發生,對其減輕罪責或是適用非犯罪化處理必須以其真誠的悔改和惡性的消除為前提。
四、結語
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是一種以人作為主體,同時也以人作為對象的活動,只有充分關注到人的價值,以人為本,才能夠真正體現出司法的文明。只要秉持這樣一種原則,那么任何檢察制度創新的嘗試都應該是有所裨益的。
注釋:
[1]張智輝:《法律監督三辨析》,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
[2]孫謙、童建明:《論訴訟監督與程序公正》,載孫謙主編:《檢察論叢》(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7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