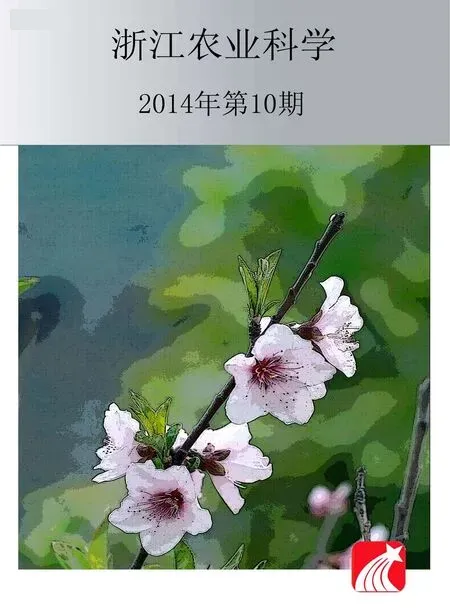基于定居意愿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探討
黃建軍,郭紅東
(浙江大學,浙江杭州 310058)
基于定居意愿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探討
黃建軍,郭紅東
(浙江大學,浙江杭州 310058)
新生代農民工一方面有著強烈的城市夢想,另一方面卻因為多種障礙因素,很難在城市社會中真正適應和融入。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心理層面因素對定居意愿的正向影響顯著大于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因素,其中社會層面因素對定居意愿的影響最小。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定居意愿
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分布在城市建設的各行各業,已經成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不斷流動的過程中,一部分外來務工青年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逐漸適應并且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中逐步完成了由流動到定居的過程。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往往由于社會閱歷不足,工作不穩定等原因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們的生活、醫療、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邊緣化傾向嚴重。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存在嚴重的社會問題[1-2]。為此,對進入紹興市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了融入城市社會情況的調查,現將有關結果報道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本選取
調查地在輕工業發達地紹興,對象為紡織印染、餐飲、建材施工、釀酒4類企業的新生代農民工,樣本分布見表1。本次調查對象絕大部分為符合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的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的離鄉工作者,不符合的予以剔除,共發放問卷332份,回收有效問卷298份,有效回收率為89.76%。
1.2 調查項目與分析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分析的方式。利用SPSS軟件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并在對紹興本地農民工的預試當中進行信度檢驗然后進行改良,刪除未達決斷值顯著的題項,最后確定5個因子,17個測量項目(表2),每個測量項目得分為5分。
對量表的可靠性進行檢驗,信度和測量項目載荷結果列于表2。由表2可知,每個因子內部一致性系數α均超過0.7,說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測試可靠性值得信任。

表1 被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特征分布情況(n=298)
2 結果與分析
2.1 經濟層面
從表3可以看出,經濟層面因素5項共得分為14.39分,得分率為57.56%,標準差為5.389分。相比于其他層面的融合變量,經濟層面的得分率偏低,這從側面說明了農民工群體在經濟上對社會融合的程度相當低。

表2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因子及其信度與測量項目及其載荷
觀察經濟層面與其他層面因素的相關性,發現經濟層面與社會關系、心理、文化層面因素之間呈極顯著正相關;與結果變量定居意愿之間呈顯著正相關。經濟層面對社會關系層面因素相關系數最大,最具有明顯的相關關系,也最具有預測作用。經濟基礎是農民工的立身之本,經濟層面融合的程度提升可以很大程度地帶動社會關系層面融合的提升。

表3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2.2 社會關系層面
從表3可知,社會關系層面因素5項共得分16.63分,得分率為66.52%,標準差為4.277分。均值超過了60%的得分,說明大部分的農民工擁有著不錯的社會關系層面的融入,與本地人的關系和聯系都比較融洽和強烈,有著較強信心的社會歸屬感。標準差的值相比心理層面和文化層面因素較大,這也反映了農民工的社會關系層面融合狀況參差不齊。這大體是由于農民工本身的情商所決定的:心態良好、吃苦耐勞的農民工更傾向于高社會關系層面融合;悲觀消極、怕苦怠工的農民工則更可能在社會關系層面融合程度較低。
觀察社會關系層面與其他幾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發現,社會關系層面與心理、文化層面因素呈極顯著正相關,與定居意愿有顯著正相關關系。社會關系層面與心理層面因素相關系數最大,有著較為強烈的相關性。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社會關系層面融合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心理層面融合的好壞,他們與周圍環境的相互聯系、相互匹配越多,他們內心對環境的接受、融合程度也會越深。
2.3 心理層面
從表3中觀察到,心理層面因素3項共得分為9.79分,得分率為65.27%,標準差為2.990分。與社會關系層面因素相同,得分率也超過六成,這或許可以解釋為大部分農民工群體對所在地的心理接受狀況比較理想。表現為農民工對本地人的生活習俗、語言習慣、鄉土人情、消費水平等都有著較為正面的心理主觀接受,易融入所在的城市與周圍環境。標準差較社會關系層面因素低,這可能是相對于更為具體、直觀的社會關系層面因素,農民工對心理層面因素的內涵更為理解和接受的緣故。
2.4 文化層面
由表3得知,文化層面因素3項共得分為7.51分,得分率為50.07%。農民工對本地的文化、習俗、觀念的接受程度僅僅只有5成。這說明,對本地的文化、觀念的接受程度較大地影響、制約著農民工群體的社會融合。標準差為2.612分,說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文化層面因素的意見分歧較小,比較集中于融合與非融合的區段之間。
文化層面融合與定居意愿呈極顯著正相關,文化層面融合對定居意愿的相關系數為0.277,則決定系數為0.076 729,即文化層面因素的變異可解釋定居意愿7.7%的變異效果。相較于其他3個變量,文化層面因素有著對結果變量最為強烈的解釋變異、預測效果,也即新生代農民工文化層面融合的程度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們在務工地扎根、定居的意愿的強烈程度。
2.5 各層面間的相互影響
將心理層面與文化層面因素合并成一個層面后,把4個變量歸納為經濟、社會關系、心理等3個層面變量,利用SPSS 19.0軟件進行分析。結果如表4。

表4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3個層面變量及定居意愿間的相關系數
由表4可知,心理層面因素對定居意愿的正向影響顯著大于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因素,其中社會層面因素對定居意愿的影響最小。另外,社會層面與心理層面因素之間的相互效應達到了非常顯著的相關性,強于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因素之間和經濟層面與心理層面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其中,經濟層面與心理層面因素間的影響最小。由此可見,心理層面因素對農民工的最終定居意愿動機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只有心理和文化等精神層面因素做到契合,農民工群體才會有內在驅動力產生定居的動機和行為。因此,心理層面的融合程度大部分取決于社會層面的融合程度。
3 小結與討論
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心理層面因素對定居意愿的正向影響顯著大于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因素,其中社會層面因素對定居意愿的影響最小。
隨著年齡的增長,第1代農民工逐漸離開城市,回歸故里,新生代民工已經成為中國農民工主體。如果說農民工還有著重回故里的想法,可以讓我們有時間在解決農民工城市適應與融入問題打個盹兒的話,那么,解決上億人口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與融入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的適應與融入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根本之道,是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小康社會、推進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關鍵環節,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應有之義。要徹底解決和改變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與融入困境,則必須采取全面、系統的反社會排斥對策,逐步消除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排斥,切實保障其合法權利,實現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心理認同的快速發展,以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的解決,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1] 蘇飛,龐凌峰,馬莉莉.生計資本對杭州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的影響[J].浙江農業學報,2014,26(3):241-246.
[2] 韓帥,朱喜鋼.城鎮化視角下農民工流動歷程與規劃應對[J].浙江農業科學,2013(6):636-639.
(責任編輯:張才德)
D 422.7
:A
:0528-9017(2014)10-1640-03
文獻著錄格式:黃建軍,郭紅東.基于定居意愿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探討[J].浙江農業科學,2014(10):1640-1642.
2014-07-09
黃建軍(1983-)男,浙江嵊州人,助理研究員,本科學歷,從事農村與區域發展研究工作。E-mail:huangjj@usx.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