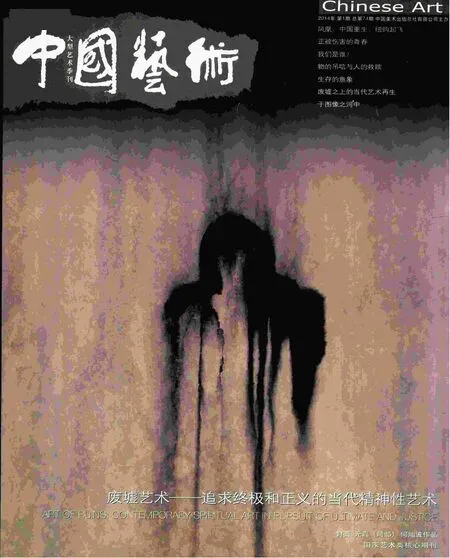淺析草原石人符號下的宇宙觀
于萬玲/文
在廣袤的大地上各個民族繁衍生息,他們在與大自然的斗爭與適應中創造著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映射出不一樣的民族精神面貌。在我國西部遼闊的草原上駐守著一群容顏不會隨時間的流逝而衰老,不畏酷暑嚴寒、執著地堅守一方,默默無語地與天地同在的“人”,它們就是草原石人。雖然我們無法親見草原石人的形成,但是可以從現存遺址的規模和空間布局上展開推論,因為“在使用某種信息解釋過去時仍然需要假定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人們對空間的態度”[1]。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烏恩先生認為:草原文化作為東方文化的組成部分,其中包含濃郁的“崇天”、“敬天”思想[2],我們同自己傾談,同大自然交流的過程,就是自古以來所說的“天人合一”、“與天地萬物同流”的至高境界。
數量不等的草原石人被放置在墓葬前面,因為人為的破壞和搬遷,石人和墓葬結構完整保存下來的少之又少,但是我們可以從幸存的幾例中初步了解其結構特征。突厥時期是草原文化中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階段,尚存有大量的祭祀遺址,草原石人恰恰又經歷了這個時代,我們可以從遺存的石圈墓、石碓墓中尋找消逝的石人文化。例如1972年吉發習等考古工作者在巴彥圖嘎蘇木所在地對石碓墓和墓地石人做過調查工作,從石頭表層看是由圓形或橢圓形的石塊組成,有的在中間豎立有石柱或石人像,這些墓地遺址的發現為解釋草原石人在空間上的構成提供了事實依據。
一件事物的產生不是憑空而降,不僅需要歷史的鋪墊,創作過程中的藝術意志也很重要。關于藝術意志的說法最早是由里格爾提出來的,“而其中的‘絕對藝術意志’就是那種潛在的內心要求,這種要求是完全獨立于客體對象和藝術創作方式的,它自為地產生并表現為形式意志”[3]。草原石人的存在是歷史的必然,它們作為人們情感寄托的產物順理成章地出現了。在廣闊的草原上,它們與大量的祭祀遺址交雜分布,縱觀其發展歷程,既有前期圓形或長方形石圈墓的形制,也有后期中間有石柱或石人的結構。它們能夠在空間上以這種形式存在,不僅與歷代的墓葬習俗分不開,而且還受當時人們宇宙觀的影響。
如在中國早期文獻中就有“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的說法,北方民族又有“天父地母”的說法,天與地在民族的心理上是不可分割的,人們在心理上對這種關系的分量是有權衡的。在自然崇拜盛行的時期,人們的宇宙觀只是停留在天空與大地的關系上,“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只是人類直觀的見解,因為從形狀上看方形比圓形更穩固,從日常的吃、住、行、用各方面分析,肥沃的土地又是生命的來源,相對于變幻莫測的天空來說,大地在心理上給人更多安定、踏實的感覺。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探索未知能力的增強,文化的變遷是必然的,當偶像崇拜或祖先崇拜代替了自然崇拜成為主流,人們對宇宙的探討主流也已經從大地與天空的關系轉移到了地球跟太陽之間的問題上,如在《張衡渾儀注》中“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的渾天說,有關薩滿成為犬戎之祖的“高辛氏有老夫居宮中得耳疾,取之得物大如繭,盛瓠中復之以盤,俄頃化為犬……”記載,這位老夫對天地萬物的認識有了新升華,進而產生了天方地圓的宇宙觀。
天方地圓觀念的產生相應地影響了人們情感造物的形式,這種形式主要存在于驍勇善戰的突厥時期,當時構造墓葬結構主要是圓形和方形。草原石人從開始就從屬于墓地,鄭隆在《略述內蒙古北部邊疆部分地城的“石頭墓”和“石板墓”》[4]中對西拉木倫河中游、西岸和中蒙邊境的海留吐溝附近地段的石頭圈和石頭堆做了考察,從遺留的石圈和石堆看,我們更加肯定墓地石人與墓葬是有關聯的。因為國內早期青銅時代、突厥時期大面積的地面遺址幾乎都缺失了原來的面貌,視覺上很難把握它們在宏觀上呈現的地貌特征。我們以境外蒙古國地區尚存的大面積遺址為例來看草原石人與祭祀遺址之間的關系,想象和還原國內草原石人所在墓地曾經宏觀的空間布局。
在原始社會先民已經存在“天人合一”、“萬物有靈”、“天圓地方”的思想觀念,人們認為大自然在周而復始地變幻著,大地是靜止不動的,他們依靠于賴以生存的大地,族群中有一種人定勝天的氣勢,但是也包含著對“天”的畏懼與崇拜,這些方面的考證最有利的證據當屬巖畫藝術。比如青銅時代在蒙古國境內巖畫中的圖案,曾經有一些研究認為“在北方巖畫上——無論是陰山巖畫,還是西伯利亞、哈薩克及黑龍江的巖畫上,都有許多使人神秘莫測的圈點圖案是星辰圖案”[5]。這個論斷似乎太絕對化,雖然兩者之間有相似性,同為圓形符號,但排列的方式卻不同,被認為是星辰圖案的多比較零散、布局不規則,而蒙古國伊和騰格爾巖畫中的圓形雖然大小不一,排列卻比較整齊。圓形的排列與草原上居住的蒙古包如出一轍,方形的線代表著大地,而圓形符號就是逝者的安居之所。大面積的墓葬遺址就是先民巖畫中表達意識的擴大化,在發展中逐漸改變它的結構,如蒙古國境內的呼都格陶勒蓋墓地大面積的圓形墓葬散落分布在河邊,與游牧生活中“逐水草而居”的觀念吻合。
把青銅時代巖畫的圖案與同時期存在的石圈墓、四方墓聯系在一起,就會發現它代表的意義更值得深思。存在于青銅時代的石圈墓和四方墓,如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阿敦喬魯石頭城的墓葬,保存比較完整,圓形的石圈外用巨型片石或小卵石圍砌,在蒙古國境內也有眾多石圈墓被石塊圍成的矩形邊框圍繞,有四方形的邊框與單獨的圓形石堆構成的數個墓葬或者圓形墓葬的排列,“這些都是當時禮儀和觀念的需要,而不是藝術激情的結晶”[6]。一些石堆中間或者周圍豎有鹿石或石柱,鹿石最主要的特征是以鹿紋為主,在兩側鹿紋的上方有圓形圖案。對圓形的理解,有研究者認為是太陽,有的則認為是耳飾,總之概括來講它既代表了圖騰崇拜,也有太陽崇拜的信仰,所以鹿石或者繪有符號的石柱出現在石圈墓或者四方墓中,說明人們在潛意識中已經有了追求人、天、地完美統一的思想暗示。
石圈墓與石人的結合還有另一種形式,就是《隋書·突厥傳》中記載的“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7]的突厥時期的石人像,這時的墓地石人被雕刻成勇士的形象。他們一生的英勇戰績用豎立的石柱數量來衡量,也有的只用石塊來表示,“殺一人則投一石”,所以在墓地石人身后的石堆具有同樣的意義。“這種石圈常常圍繞著墓堆或中央有石墓標,存在墳墓朝向供奉著被埋葬的首領或先知之精靈的神殿的傾向十分明顯,所以這類由石墓構成的圈同樣也是神殿”[8]。在隋唐時期,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內的阿日夏特石人墓外圍都是用卵石做圓形或方形石陣,圓形的周長可達100米左右,方形的邊長有的達到35米左右,在石陣外面立有石人,或者被認為是石人前身的象征標志物——石板,草原石人在這里被作為偶像和英雄來崇拜。
草原石人的安置受到“天方地圓”思想的影響,并不是被賦予了某種形式,而是在“空間觀念建立起來后才在藝術中取得了作為基本因素的地位”[9],就好像文化尚不發達的古人熟知天圓地方的思想,卻不能夠以確切的資料或者實物去表達。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產生新的宇宙觀并選擇了草原石人作為依托,這也是石人作為地域文化符號產生的一個原因。
草原石人是中國的本土文化,草原石人對時空、方位的選擇受到民族心理的影響,帶有顯著的民族特色。它與墓葬結合呈現的排列形式不僅有宏觀的視覺效果,也是個體思想在空間中統一的展現。從空間布局中來看草原石人的起源與發展,帶有人們對宇宙觀和空間的選擇。草原石人自始至終和墓葬為一體:有帶有象征性石柱的墓葬,有繪有圖騰符號的鹿石的墓葬,有隱現人面的石人像的墓葬,有突厥石人的墓葬,一直到草原石人發展的成熟期,蒙古石人與墓葬的結合。墓葬圓形和方形的結構,不管是分散的還是有序的,我們都能感受到天、地、人的和諧統一。這里面不僅帶有人們對自然、對宇宙的認識和理解,也帶有人們對生的向往,對靈魂不滅的追求。
注釋:
[1]伊恩·霍德、司各特·哈特森著,徐堅譯.《閱讀過去》.岳麓書社.2005年12月.第110頁
[2]李鳳斌等著.《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11月.第62頁
[3][德]沃林格著,王才勇譯.《抽象與移情》.金城出版社.2010年9月.第10
[4]鄭隆.《略述內蒙古北部邊疆部分地城的“石頭墓”和“石板墓”》.《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1990年1期
[5]姚風.《蘇聯遠東地區1983年考古發現》.《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1990年1期
[6]鄭巖.《中國表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64頁
[7]《隋書·突厥傳》
[8][英]愛德華·B.泰勒著,連樹聲譯.《人類學——人及其文化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326頁
[9][德]阿道夫·希爾德布蘭德著、潘耀昌等譯.《造型藝術中的形式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