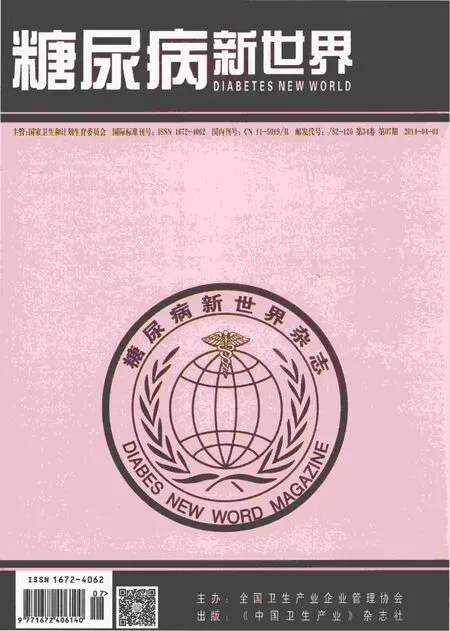糖尿病中醫治療的現狀芻論
馬文心
山東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2010級,山東濟南 250014
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以高血糖為特征的內分泌代謝性疾病,長期代謝紊亂會導致全身特別是眼、腎、心血管及神經系統的損害及其功能障礙和衰竭。嚴重者可引起失水,電解質紊亂和酸堿平衡失調等急性并發癥酮癥酸中毒和高滲昏迷。近30年來,我國糖尿病患病率顯著增加。2007—2008年,在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組織下,全國14個省市進行了糖尿病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20歲以上的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為9.7%,成人患者總數已達9240萬,糖尿病已成為我國第一大病。據WHO預測,21世紀糖尿病將在發展中國家流行,到2025年世界糖尿病人將上升為2.99億,我國患病人數將比現在翻一番,并呈逐年上升趨勢。糖尿病嚴重威脅著我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加強糖尿病的防治工作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大事及重點。今結合文獻資料及省內外中醫大師的臨床經驗,就糖尿病的中醫治療提出初步想法,略述如下。
1 歷史沿革及發病主因
糖尿病屬于中醫“消渴”范疇。“消渴”是臨床常見、多發病證,備受歷代醫家重視。兩千多年前《黃帝內經》就有關于此病的記載,稟賦不足,五臟柔弱為發病主因、內因,即“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之論,其中《素問·奇病論》中提到:“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金匱要略》有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并治專篇,彌補了《內經》重“消”輕“渴”之不足。晉代《小品方》中指出內消之為病。唐代《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對本病認識較前又有進步。從宋代開始明確的用上中下三焦分型作為辯證論治的旨歸。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劉完素在其《三消論》中提出三消燥熱學說。名清代發展的特點是,上消側重治肺,對腎的病機地位更為重視,進一步闡述命門火微不克蒸騰的病機。近代名醫施今墨對本病也頗有見解,認為:“除滋陰清熱外,健脾補氣實為關鍵的一環。”
《糖尿病中醫防治指南》中提出本病因嗜食肥甘厚味、情志內傷、喜逸惡勞,致脾失健運,統攝失常;或腎精虧耗,氣化不及、水谷精微不歸正化,變生濁邪,不得宣泄,留于血中而成痰濁。日久則脾腎兩虧,氣陰俱損,氣虛無力推動血行;脾虛生痰濕,阻礙氣機,致氣滯血瘀,痰淤互結,最終為患。
2 糖尿病的中醫治療現狀
2.1 20世紀90年代之前
古代文獻中只有“消渴”而無“糖尿病”之名,近代醫家根據消渴的“三多一少”(多食、多飲、多尿、消瘦),將“糖尿病”歸屬于“消渴”的范疇,辨證分型以陰虛燥熱、脾腎兩虛、氣陰兩虛、陰陽兩虛為主。在此時期,中醫多以改善癥狀為療效追求目標,探索治療方劑不少,但難有滿意療效,因為對于血糖的控制并不重視,中醫藥物無法有效的降糖已成為中西醫學界的共識,其降糖始終處于輔助地位。在過去的研究及臨床經驗中,中醫藥仍然遵循傳統理論與治療模式,未能在糖尿病領域取得重大突破,遠遠落后于國際醫學水平。
2.2 20世紀90年代之后
這個時期醫療衛生條件大大改善,所以糖尿病人群較過去的以消瘦人群為主變為以肥胖人群為主,多數糖尿病患者并無三消表現,患者不再滿足于單純癥狀改善,對中醫降糖的需求加大,以陰虛燥熱理論指導糖尿病治療難以取得滿意療效。進入21世紀,中醫中藥在糖尿病臨床治療方面解決了單純中藥降糖的難題,取得了重大突破,這一成果首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由小樣本研究過渡到大樣本研究,開展了單純中醫降糖的的臨床研究,確認了中醫降糖的準確性,由自身對照逐漸轉向隨機對照研究。而在并發癥研究方面相比過去,無論臨床治療還是理論研究,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奚氏提出糖尿病足奚氏分離法,拓展了診療糖尿病足的思路和方法;于氏提出淤血損絡市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發病的關鍵病機;南氏針對糖尿病腎病,提出解毒通絡保腎是根本治法。
近幾年來,在全國知名中醫糖尿病專家共同努力下,制定了行業第一部專病指南《糖尿病中醫防治指南》,起草了行業第一部專病標準《糖尿病中醫防治標準》。指南與標準的制定標志著中醫的研究開始走上規范化道路。綜上所述,現階段中國醫藥在糖尿病領域取得了重大進步,不僅在病機分析上有所創新,在治法方藥上也突破了傳統,逐漸轉以“泄實”為主,改革了原來以“補虛”為主的局面,解決了單純中藥降糖難題。
同時,中醫精英還逐步探討其他糖尿病治療方法,如針灸治療、按摩治療、理療、氣功、食療、心理療法和外用藥膏貼服等,治療效果也十分有效,各具特色。
3 糖尿病中醫治療存在不足
雖然中醫治療糖尿病(現代說法)數千年,尤其近幾十年我國中醫治療技術和理論水平不斷發展,糖尿病治療水平取得一定成績,但與西醫相比,與國外現代醫學相比,仍有不少不足和問題。
3.1 降糖療效不十分迅速
在我國,治療糖尿病的藥物主要分為中藥和西藥兩大類。其中西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磺脲類藥,這是人類最早發現的糖藥,以優降糖等為代表,其特點是短期降糖作用強。但是長期使用會加重胰島負擔,加速胰島功能衰竭。第二類是雙胍類藥物。以二甲雙胍片為代表,能增加外周組織對糖的利用,是Ⅱ型糖尿病人的首選藥物。第三類藥物是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以拜糖平為代表,其主要作用機理是阻止小腸對葡萄糖的吸收,以降低餐后血糖為主。西藥雖然降糖療效明顯,但長期服用有一定的副作用。而中藥是天然植物藥品,副作用較小,所以很多病友偏愛用中藥。但真正的純中藥降糖作用是很慢的,并不是迅速起到降糖作用,無論是國際上還是國內,無論用怎樣高科技的方法,還沒有發現短期內能很快降糖的純中藥。
目前某些廠家或糖尿病專科多采用中西藥摻在一起的辦法,雖然打著純中藥的旗號,短期內也有一定的降糖效果,但往往好景不長。如何使糖尿病病人的血糖長期保持穩定,是擺在全世界醫務工作者面前的主要課題。
3.2 治療思維橫向聯系少,普及率低
中醫幾千年來為炎黃子孫的繁衍、為祖國醫療事業的形成、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其自身發展是緩慢的,導致這種狀態的發生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其他行業間的橫向聯系交融機會少,當今學科間的相互促進是發展的重要途徑。中醫因其自身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和獨特的治療模式,難于被行業外人士理解,尤其相對于西醫,因此推廣中醫科普知識是發展中醫藥的重要手段。在西方醫學中,他們更重視“營養學”的研究(即保健,就是中醫里的“養生”),他們的保健已經普及到了每個國民,每個人都有一身的保健知識,所以,他們生病的機率較小。另外各種對人體深具副作用的藥品雖然是他們發明的,他們很少應用,中國人卻在大量使用,比如:青霉素這種抗生素藥品,西方國家每年使用率只有約5%,而中國人的使用率達到了80%以上。從這點來看,在國內中醫治療思維方面應多學習西方優勢,加大如何提高國民普及意識。
3.3 中醫工作者存在脈診缺陷
西醫診病的科學性,突出表現在臨床數據及影象異常的實在反應。如體溫、血壓的高低;心律、呼吸的快慢;并通過實驗室數據檢查報告,來判斷診治病情。中醫則憑三個手指,一只脈枕就能獨立診治疾病,與西醫相比,省卻很多設備和輔助醫務人員,但這樣的診療活動,在新世紀對于祖國醫學,難以有質的飛躍。在中醫專業某些認識導向下,如針對復合病癥的診斷提法“舍脈從證”,而由此誤解甚至忽略了中醫在整個辨證論治的重要環節——對脈診的重視。至今,諸多臨床病歷及專業期刊雜志罕見有三部九候脈象的完整規范的描述。在糖尿病治療中尤為突出。
3.4 臨床治療及統計分析不規范,中醫治療手段應趨于綜合性
糖尿病的各種并發癥尚無統一的中醫診斷、辨證分型、療效評定標準。臨床個案較多,但是治療資料及積累不完善,不規范,缺乏數理統計等有效分析處理,缺乏系統分類處理,難以對長系列資料進行分析得出有價值結論,不利于大宗病例的前瞻性研究以及有效的方藥篩選。古人和前人許多方藥散在歷代文獻中,系統整理文獻中對于糖尿病的描述治療是亟不可待的。同時糖尿病中醫治療術語缺乏規范,因歷史條件限制,中醫許多的診斷主要是依靠傳統手法進行,缺乏規范的診斷標準,針對多數常見病、多發病,中醫治療相對于現代西醫治療較缺乏統一及可行的診斷和治療標準,與現代科學發展需要不相適應。另外,中醫治療糖尿病僅僅局限于方劑、方量和診斷上等,缺乏較為完善的綜合性治療方法。
3.5 病人服藥方法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
在臨床工作中,療效問題是每個醫生極為關心的,其中辯證是否正確,處方是否恰當,無疑是影響療效的主要因素,也是為每個醫生所重視的。但是影響療效的因素遠不只這兩個方面,中藥的服藥方法也占有很大程度影響作用。中醫對服藥時間是不太重視而且是相當刻板的,甚至連教科書中也只寫“水煎服”,而無服藥時間的具體規定。不分疾病種類,病情輕重,不論藥物特性,方劑作用,大都是每日一劑,水煎服,早晚分兩次口服。當對病人服藥后的效果感到不滿意時,又往往只從辯證、用藥方面調整,很少從服藥方法尤其服藥時間對療效的影響這方面加以考慮。
3.6 與西醫治療相結合有待進一步加強
目前臨床治療方案多以西醫為主中醫為輔,但是筆者認為中醫有獨特的療效,我們可以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西醫介入治療,會產生很大的依賴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現在雖然中醫治療糖尿病與西醫相比在降低血糖方面的優勢并不明顯,但是在防治糖尿病并發癥、治療腆島素抵抗方面很有優勢,中西醫應兼顧各自優勢,相互治療,綜合起到治療作用。
4 提出合理建議和對策
4.1 國家制定促進中醫發展政策,加大中醫藥財政投入
目前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建有中醫藥管理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駐地建有中醫院,尤其是“中醫乃中國根基之醫學”、“中國乃中醫之國”,所以國家在現有基礎上應高度重視中醫藥發展,把中醫藥作為國家重點發展事業和民族事業,作為國家基礎產業發展,中醫主管部門制定政策政府扶持中醫藥事業發展,制定中醫藥發展規劃,并落到實處,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每年遞增對中醫藥政府投資力度,在醫學發展上優先發展和支持中醫藥,使中醫藥在國際醫學上成為中國王牌醫學。如加大對糖尿病中醫藥治療研究和人才培養,成立專門研究和治療機構,提高治療該病水平和能力,達到逐年減少患病人數。
4.2 積極培養中醫藥專業人才,提高國民中醫治療意識
全國雖建有幾十所名牌中醫藥大學,各省市縣均建有中醫院,但目前中醫藥人才相對于西醫數量相當有限,眼下社會各階層對中醫也缺乏應有重視和普及,甚至有西醫工作者貶低中醫作用,特別中醫院與西醫院相比就診率相差巨大,足以看出國人對中醫的認識程度。因此,在這樣大環境下,一是國家應制定促進中醫加速發展方針政策,像節水節電、環保等人人知道、人人保護,逐步加大和提高國民中醫普及意識,普及到每個國民,每個人都有一身的中醫保健知識。二是加大培養中醫藥大學生等高層次知識分子,國家優先照顧和安排優秀畢業生到重點中醫院和科研院所,推動中醫藥新時代發展,同時分層次培訓現有中醫藥工作者,練素質練能力。三是普及全民中醫意識,在各中小學、各個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推廣中醫養生和中醫保健知識,提高國民中醫意識。尤其對于糖尿病患者最多的我國,在中醫治療和預防該病方面應技大推廣和普及全民中醫意識。
4.3 增加中醫藥人員業務培訓,加強中醫基本功訓練
中醫從業人員必須掌握的技能之一就是按脈知病。所以說準確熟練的脈診,疑難病癥和急癥診治過程中有著很大的作用。但現實多數臨床醫生,會背誦《脈訣》、《脈經》者、會應用者都是寥寥無幾的。正因為中醫辨證關鍵——脈診的缺失,治療上或許相應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對證治療和根據教科書上教條的隨意性治療。與現在的情況相比,從漢代到清代的著名中醫學家,無不重視分部脈診,在此期間還有很多詳細的脈診論述。“醫圣”張仲景曾言:“按病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所謂窺管而已。”在目前同等的醫療位置上,與西醫的多項數據和輔助診斷人員加設備相比,我們中醫工作者診治疾病,用獨立的三個手指,同樣有很好的療效,憑的就是千百年經驗。因此中醫不能忘本,在治療糖尿病過程中要加強中醫基本功的訓練,各中醫醫療機構經常或不定期加大對基本功培訓鍛煉,通過技術練武和技術比賽,提高中醫工作者技術水平和業務能力。
4.4 提高中醫治療水平統一規范性,提倡綜合治療性
中醫個體化辨證思維的培養以及運用存在一定難度,將糖尿病中醫中的共性部分標準化必將利于臨床、科研和教學。臨床應該按照“隨機、對照、盲法”的原則進行更深層次的病機研究,充分了解疾病的復雜性,建立符合臨床實際和發病機制的穩定的可靠的動物模型,使研究過程更加標準化,以便更加客觀地評價中醫中藥療效。
同時,在中醫治療方面,應該加強針灸、食療等綜合治療,尤其對食療的重視。中醫飲食療法要求比例平衡、性味辨證、食量有度,甘酸苦辛咸五味要平衡。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保證各類食物比例的科學性。在糖尿病食療中不僅包含食物種類的搭配、食量的調控,同時也包含食物的性,即食物對人體五臟功能以及陰陽寒熱的調節作用,這點在糖尿病食療領域是獨有的。總之,藥物配合食物治療對提高療效有很大的作用,緩解了患者的經濟壓力。
4.5 要科學確定服藥方法及服藥時間
要根據病情輕重緩急而確定不同的服藥時間,在病情輕重緩急不太明顯的一般情況下,服藥時間大多為一日三次,在病情特別危機的情況下,不但要求藥力峻猛,而且在服藥時間上要求果斷迅速。同時也要根據服藥后病情變化而確定不同的服藥時間,也就是說初服后,再根據服藥后的病情變化而確定是否再次用藥及用藥的劑量、方法和時間。再者,相同的方劑根據不同的病情而確定不同的服藥時間,法隨病而立,方隨法而設,是以病有主方,方有主病。要根據藥物的特性的不同而確定不同的服藥時間,為了達到藥物恰中病機,且又不致產生副作用,不但要掌握好藥物配伍、煎取得當等環節,在服藥時間上也要有科學的安排。
4.6 發揮中醫主導作用,兼顧西醫輔助治療,提倡中西醫綜合治療
中醫與西醫治療糖尿病各有長短。單純的西醫治療雖然降糖效果迅速但是會有不良反應,比如耐藥性差、容易引起胃脘不適、皮疹等。單純的中醫治療雖然可以控制并發癥和臨床癥狀的發生,無不良反應,但是降糖力度較小,作用緩慢。只有中醫與西醫結合治療,即可以避免藥物的不良反應和耐藥性,又可以改善臨床癥狀和防止并發癥。
加大對中藥降糖的研究,同時要兼顧西醫治療。我國醫學界許多著名的專家、教授在這方面做了大量辛勤工作,終于探索出了一套以生物活性療法為主、中西醫結合、標本兼治的治療糖尿病的新方法——梓榕綜合生物療法。其主要臨床思路是:以重點解決代謝紊亂、胰島素抵抗,全面恢復胰島功能,防治并發癥為主,融中西醫思路為一爐。短期利用西藥降糖快的治表優勢,長期發揮生物活性優勢,治本求源,重在人體內環境的改善、血液質量的改善、臟腑功能的改善,在不增加胰島負擔的情況下,提高受體的敏感性、增加胰島素的活性,不僅使許多患者血糖迅速降至正常,同時并發癥得到徹底緩解,也避免了西藥對肝腎的副作用。現代藥理研究證明,很多單味中藥具有降糖作用,其特點是重視患者的個體差異性和復方的使用,起到提高生活質量和延長壽命的作用。所以我們要加強對于單純降糖的中藥還有復方降糖的方劑的研究,同時也要配合先進的西醫療法,相互發揮各自優勢和特點,達到實現雙贏。
5 結語
雖然中醫治療糖尿病的研究及治療存在上述諸多問題,但是有問題就會有解決方法,解決方案需要不斷地摸索,不斷地提高,不斷地修正,因此相信在我們這個“中西醫并重,大力發展中醫藥”方針政策的指導下,雖然有很漫長的路要走,但只要結合西醫先進的技術,“立足中醫,為我所用”,在科學的研究下大膽創新,對中醫基本功的訓練有所重視,加大對于中醫中藥降糖的藥理研究,就一定會取得突破性發展,為攻克糖尿病做出貢獻。
[1]仝小林,劉文科,甄仲,等.糖尿病中醫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展望[J].中國新藥雜志,2011,20(21):2044-2047.
[2]林蘭.糖尿病的中醫研究[J].中國醫藥學報,1998,13(4):3-5.
[3]姜建國.傷寒思辨[M].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248-254.
[4]全小林,胡潔,段軍,等.糖尿病中醫治療中的幾個問題及對策[C].中醫藥學術發展大會論文集:185-187.
[5]周仲瑛,蔡淦.中醫內科學[M].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67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