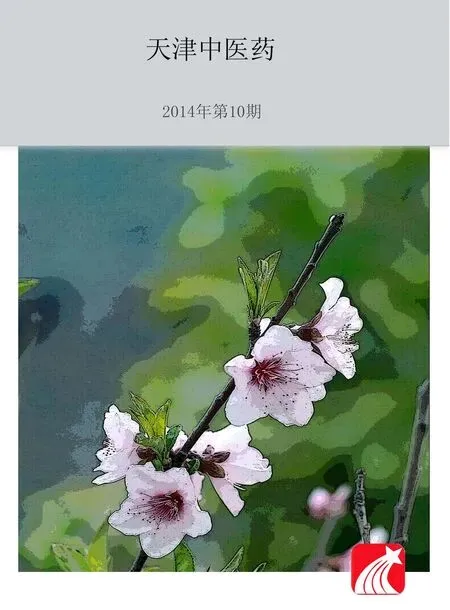漿細胞性乳腺炎的中西醫研究進展*
丁志明,王 軍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193)
漿細胞性乳腺炎的中西醫研究進展*
丁志明,王 軍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193)
漿細胞性乳腺炎;粉刺樣乳癰;自身免疫性疾病
漿細胞性乳腺炎(PCM)是以輸乳管竇或乳腺導管擴張為基礎,導管周圍漿細胞浸潤為前提的慢性、非細菌性炎癥,好發于非哺乳期、非妊娠期[1],臨床多表現為乳頭凹陷、乳頭溢液或溢血、乳暈下或乳暈旁膿腫、局部瘺管形成、乳房非周期性疼痛,因其化膿破潰后膿中常常夾雜著粉渣樣物質,故中醫學稱其為“粉刺樣乳癰”。阮華等[2]報道,本病發病率約占乳腺良性病變的1.41%~5.36%。但由于本病發病機制目前仍不甚清楚,臨床表現也比較復雜,臨床上容易誤診,尹俊平等[3]統計表明該病誤診率高達56.9%,因此,對本病的研究必須進一步深入。現將國內外對PCM的最新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1.1 西醫學 西醫學對此病大致認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蘇莉[4]通過免疫組化檢測發現該病患者的乳腺小葉、乳腺間質及乳腺導管周圍白細胞分化抗原20、3、45(CD20、CD3、CD45)陽性,淋巴細胞浸潤,有少量白細胞分化抗原68(CD68)陽性的巨噬細胞浸潤。漿乳是由于各種原因引起乳腺導管阻塞,局部導管擴張,管內分泌物聚積,從而誘發自身免疫反應的免疫性疾病。趙紅梅等[5]提出本病是以乳頭周圍主導管引流停滯為病變基礎的乳腺導管擴張綜合征,當病變發展到一定階段,局部出現漿細胞浸潤時才稱為PCM,所以漿乳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病變,而是由乳腺導管擴張發展而來,是同一疾病的不同階段。孫俊平等[6]提出漿乳可能還與以下因素有關:1)乳頭發育不良。如乳頭凹陷、乳頭皸裂等使得乳腺分泌物排泄不暢,分泌物淤積于輸乳管竇及乳腺導管內,淤積物多為脂性物質,能侵蝕管壁,從而脂性物質外溢,引起化學性炎癥,誘發淋巴細胞、漿細胞浸潤,形成炎性包塊,逐漸成膿、破潰,膿中常有粉刺樣物質。2)炎癥。既往有乳腺炎病史,使得該區域乳腺導管因炎癥而增生,進而出現管腔狹窄甚至閉塞,管內分泌物積聚,不能排出,誘發漿細胞浸潤。3)乳腺退行性變。如多次妊娠、中老年婦女因卵巢功能減退都能造成乳腺導管退行性病變,表現為管壁松弛,肌上皮細胞收縮功能減退,不能及時將導管內分泌物排出,誘發漿細胞浸潤。4)生育哺乳。乳汁分泌障礙有哺乳期乳腺炎患者、哺乳習慣、衛生條件不良的患者容易引起乳腺導管閉塞,管內分泌物積聚,誘發漿細胞浸潤。5)乳房外傷。乳暈部手術或其他外傷造成乳腺結構損傷,引起乳腺導管閉塞,管內分泌物積聚,誘發漿細胞浸潤。6)內分泌失調。例如垂體泌乳素升高也能引起導管擴張,管內分泌物積聚,從而誘發漿細胞浸潤。7)亦有報道認為本病與吸煙有關[3]。
1.2 中醫學 古代文獻中對本病的記載較少,從其臨床癥狀來看本病應屬乳癰、乳漏、瘡瘍等范疇。例如清代《外科真詮》記載:“乳漏,乳房爛孔,時流清水,久而不愈,甚則乳汁從孔流出,多因先患乳癰,耽誤失治所致。”現代中醫對本病病因病機認識較多。萬華[7]指出本病病位在乳房,女子乳房屬胃經,而乳頭屬肝經,因此本病與肝胃關系密切,屬木郁土壅,肝胃郁熱之證,乳絡不暢是發病的條件。卞衛和等[8]認為漿細胞性乳腺炎是本虛標實、因虛致實、虛實夾雜的乳腺疾病,先天稟賦不足是本虛,情志不暢、肝郁氣滯、沖任失調是標實。李佩琴等[9]認為漿細胞性乳腺炎是因情志不暢,致使肝氣郁滯,脈絡瘀阻,肝經巡行乳房,瘀阻凝聚成塊結于乳房,瘀阻日久化熱,蒸釀肉腐,經脈瘀阻致使營血不從,肌膚失養,肉腐不能修復而成膿。病變初期以氣機不暢為基礎,腫塊期以氣滯血瘀為特點,化膿期以熱毒蘊蒸為核心,瘺管期以營血內敗,正氣不足,無力祛邪外泄為病機。陸炯[10]認為本病除肝氣郁結外,還有痰瘀交阻,氣滯痰凝結聚成塊,日久化熱,蒸釀成膿,正氣不足,破潰經久不愈。方秀蘭[11]認為本病除肝經瘀阻外還有脾經瘀熱,木郁土壅,肝郁胃熱是本病的發病機制,乳頭凹陷,乳絡不通是發病的條件。楊毅等[12]認為本病應屬陰證瘡瘍范疇,病機為痰,本病發病緩慢,病程較長,耗氣傷陰,致使氣虛無力運化水濕,水濕積聚,而陰虛火旺,又灼津成痰,痰毒蘊結阻于乳絡,正虛無力與邪抗爭,故初期多無皮色紅、皮文高等表現。陰虛內熱,正氣不足致使邪毒擴散,膿毒旁竄,遷延日久而不愈。基本病機為氣陰兩虛,痰毒蘊結。
2 臨床表現
初期可表現為乳頭溢液,多為間歇性、自發性,溢出物多為白色脂質樣物質,常帶有臭味,因量較少常被患者忽視。中期往往發病迅速,由某些原因,如外傷等造成乳房局部突然腫大疼痛,腫塊多位于乳暈部附近,或向某一象限延伸,腫塊較大,形態不規則,質地又硬又韌,邊界不清,常與皮膚粘連,甚至出現橘皮癥,但無胸壁粘連,局部可出現紅腫熱痛,患側腋窩淋巴結往往腫大、壓痛,但其疼痛程度及全身炎癥反應較輕,一般血象不高,無發熱畏寒,使用抗生素治療效果無效。晚期腫塊成膿,膿中挾雜粉刺樣或脂質樣物質,經久不愈形成瘺管,乳頭更加凹陷,形成惡性循環,炎癥反復發作,從而形成復雜性瘺管。
3 超聲檢查
李霞[13]對27例PCM患者的超聲檢查分析認為,PCM超聲表現復雜多樣,早期表現為單純性導管擴張,急性期表現為實性病灶,常位于乳暈后或乳暈周圍,腫塊內部回聲不均勻,并呈低回聲,邊緣不規則,無包膜,導管呈囊狀或串珠樣擴張。王超等[14]認為PCM為實性包塊或囊實性包塊時,形態不規則,多數長徑與前后徑比>1,邊界不清,無包膜,內回聲不均勻,可見粗光點、光斑及條索狀的強回聲帶,周邊見回聲減低帶,常伴有不同程度乳腺導管擴張,峰值流速<25 cm/s,RI<0.7,PCM伴有同側淋巴結腫大者,多為皮髓質分界清楚的扁橢圓形,多單個存在。
4 病理檢查
唐文等[15]提出PCM早期病理一般表現為導管上皮的不規則增生,乳腺導管擴張,管腔內有大量的上皮細胞碎屑,并有脂質性分泌物在管腔內積聚,乳腺導管周圍組織出現纖維化,伴有淋巴細胞浸潤。尤其到了后期,病變腺體可見導管壁增厚并纖維化,導管周圍出現脂肪壞死,并有大量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及漿細胞浸潤,尤其是漿細胞浸潤明顯。馬榕[16]根據其不同病理過程將PCM分導管擴張期、炎塊期、膿腫期和瘺管期。
5 治療
5.1 西醫治療 西醫學對于本病治療一般采用手術手段,切除病變組織,如病變導管切除術、病變乳腺小葉區段切除術,甚至單純乳房全切術,原則是盡量多切,保證病變組織被完全切除,否則極易復發。這種處理方法對乳房外形破壞太大,尤其是病變范圍較大或病變位于乳頭乳暈下時手術切除治療對患者的生理、心理均會造成二次傷害。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口服西藥治療PCM的方法,如蔣國勤[17]提出三苯氧胺治療PCM,馬祥君等[18]提出服用地塞米松及甲硝唑治療PCM急性發作期患者。蘇莉等[19]提出將利多卡因、阿米卡星、曲安奈德配成混合液在病變乳腺周圍進行局部封閉治療,遠期有效率可達93.33%。
5.2 中醫治療 粉刺性乳癰在臨床上可分為4期:溢液期、腫塊期、膿腫期、瘺管期,根據各期不同的臨床特點采用不同的治療方法,原則是內外結合治療,溢液期、腫塊期偏重內治,膿腫期偏重外治,瘺管期內外并重,各期均可配合針灸治療,劉志良等[20]提出取肩井、太沖、天宗針刺治療可取得良好效果。
溢液期患者臨床表現多無明顯疼痛或腫塊,患者一般以乳頭乳暈區輕微疼痛,擠壓乳頭有淡黃色滲液或“奶酪”樣物質為主訴就診。此期治療乳房按摩為主,輕輕捋壓乳暈及乳頭,盡量排出乳管內積聚物,捋壓動作要輕柔,防止乳管損傷,并可用生理鹽水經常清洗乳頭,利于乳管通暢,必要時用乙醇或碘伏消毒乳頭,防止病邪逆行侵入乳房。張珺等[21]認為本病初起時形癥未成,內服中藥應以消法為主,方用逍遙蔞貝散。
腫塊期又分腫塊靜息期和腫塊急性發作期,腫塊靜止期患者臨床多表現為皮色不紅,皮溫不高,腫塊疼痛不明顯;腫塊急性發作期臨床多表現為腫塊范圍急速增大,局部紅腫疼痛劇烈。朱燕[22]認為本病靜止期治療以溫陽化痰,軟堅散結為主,當以陽和湯加減治療;急性發作期當以疏肝理氣,清熱解毒為主,方用丹梔逍遙丸加減。樓麗華[23]對本病腫塊靜息期也選用陽和湯加減治療。林毅教授[24]指出腫塊急性發作期當用金黃散箍圍法外敷,以清熱解毒,局限病變范圍。
膿腫期患者治療以外治法為主,同時輔以內治法。以手術切開引流排膿為主,術后配合中藥內服外敷,此方法是治愈本病的主要手段。朱燕[22]指出成膿期治療以排毒外出為主,中藥內服治以疏肝清胃,排膿透毒,方用瓜蔞牛蒡湯加減。方秀蘭[11]對此期中藥內服治療也以泄肝清胃法為主,其選用方藥有柴胡、桃仁、牡丹皮、王不留行、穿山甲等,據其對35例本病患者統計,總有效治療率為97.14%。
瘺管期患者以正氣虛弱,余毒未清,正虛邪戀,傷口久不愈合為臨床特征。任曉梅等[25]認為在漏管內無分泌物流出的情況下可進行進行掛線療法,徹底切割瘺管的內外口及瘺管管腔,此方法操作簡單,療效確切。張珺等[21]認為此期病變進入慢性期,緩則治其標,治療以補托為主,扶正托里排膿,方用托里消毒散加減。
6 結語
PCM是臨床少見的一種無菌性乳腺炎,由于乳腺導管的阻塞、擴張等導致漿細胞浸潤引起周圍脂肪組織的炎癥反應,屬于乳腺導管擴張癥晚期表現[26]。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情志不暢尤其是在女性群體中越來越普遍,一定程度上使PCM的發病率越來越高,各學者對本病病因病機、辨證論治各有論述。文獻中西醫治療手段多以手術擴切無菌縫合為主,甚至行乳房全切[27],此法雖能縮短療程,立竿見影,但忽視了女性對乳房美的追求,造成患者二次心理傷害。中醫學對本病認識較多,治療多以內外同治,早期中藥內服外敷,以消為主;中期以中藥內服,多用疏肝解郁、溫陽托毒、化痰散結、清熱解毒等法治療[28];后期膿成配合手術切開引流清創術,由于此法創傷小,較之西醫單純手術擴切更能被患者接受,但中醫切開引流清創治療愈合時間長,有復發可能,因此PCM的治療應以中西醫結合,內外同治為基礎,不斷優化治療方法,以提高臨床療效。
[1] 耿翠芝,吳祥德.漿細胞性乳腺炎的診斷與治療[J].臨床外科雜志,2007,15(6):376-377.
[2]阮 華,楊紅健.漿細胞性乳腺炎診治體會附76例報告[J].浙江臨床醫學,2003,5(2):108.
[3]尹軍平,王愛武,李文華,等.漿細胞性乳腺炎診治分析[J].中國醫師雜志,2005,7(1):109.
[4]蘇 莉.漿細胞性乳腺炎CD3、CD20、CD68表達及其免疫機制研究[D].銀川:寧夏醫科大學,2009.
[5] 趙紅梅,雷玉濤,侯寬永,等.乳腺導管擴張癥和漿細胞性乳腺炎差異的探討[J].中國現代普通外科進展,2005,8(4):234-236.
[6]孫俊平,胡文秀,周先保.乳腺導管擴張癥48例診治體會[J].中級醫刊,1995,30(6):342-334.
[7]瞿文超.萬華教授治療漿細胞性乳腺炎經驗[C].第十一屆全國中醫及中西醫結合乳腺病學術會議論文集,2009:330-331.
[8]卞為和,任曉梅.漿細胞性乳腺炎病機探討[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17(4):212-213.
[9] 李佩琴,韓雙平.漿細胞性乳腺炎35例診治體會[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4,24(1):80-81.
[10]陸 炯.清熱活血法為主治療漿細胞性乳腺炎16例[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0,16(3):188.
[11]方秀蘭.泄肝清胃法為主治療漿細胞性乳腺炎35例[J].實用中醫藥雜志,2001,17(12):35-36.
[12]楊 毅,梁 棟,遲均敬.肉芽腫性乳腺炎的中醫藥治療探討[J].河北中醫,2010,32(2):208-210.
[13]李 霞.漿細胞性乳腺炎的超聲診斷[J].實用醫技雜志,2013,20(5):506-507.
[14]王 超,趙 暉,付士地,等.漿細胞性乳腺炎超的聲特點與鑒別診斷[J].醫學影像學雜志,2012,22(7):1217-1219.
[15]唐 文,何 山,鄭 軻,等.漿細胞性乳腺炎的臨床研究[J].中華實用診斷與治療雜志,2008,22(11):810-811.
[16]馬 榕.乳腺導管擴張癥臨床病理特征與治療對策[J].中華實用外科雜志,2009,29(3):215-217.
[17]蔣國勤.三苯氧胺在漿細胞性乳腺炎治療中的應用[J].江蘇醫藥,2006,32(10):987-988.
[18]馬祥君,汪 潔,高雅軍,等.應用地塞米松和甲硝唑治療急性期漿細胞性乳腺炎的療效觀察[J].中華乳腺病雜志,2008,2(1): 110-111.
[19]蘇 莉,余建軍,劉長虎.局部封閉治療腫塊期漿細胞性乳腺炎30例效果觀察[J].寧夏醫科大學學報,2009,31(3):356-358.
[20]劉志良,滕 輝,肖道梅,等.中醫外治法治療早期乳癰40例療效觀察[J].天津中醫藥,2010,27(5):335-335.
[21]張 珺,潘立群.托法治療漿細胞性乳腺炎[J].山東中醫雜志,2010,29(10):719.
[22]朱 燕.漿細胞性乳腺炎腫塊期治療思路淺析[J].光明中醫,2010,25(12):2159.
[23]樓麗華.溫陽散結法治療漿細胞性乳腺炎[J].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96,20(5):24.
[24]徐 飚,戴 燕,關若丹,等.林毅教授活用外治法治療復雜性漿細胞性乳腺炎經驗簡介[J].新中醫,2010,42(6):124-126.
[25]任曉梅,卞衛和.掛線療法治療乳暈部瘺管32例體會[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5,14(11):1470-1471.
[26]張淑群,紀宗正,薛興歡,等.漿細胞性乳腺炎的診斷和治療[J].臨床外科雜志,2007,15(6):378-380.
[27]寧連勝,方志沂.現代乳腺疾病治療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4-6.
[28]祝東升,趙立娜,張董曉,等.中西醫結合法治療漿細胞性乳腺炎153例[J].中國臨床醫生雜志,2007,35(6):36-37.
R655.8
A
1672-1519(2014)10-0638-03
2014-05-26)
(本文編輯:滕曉東,高 杉)
10.11656/j.issn.1672-1519.2014.10.17
天津市高等學校科技發展基金計劃項目(2007 0316)。
丁志明(1979-),男,碩士,主治醫師,主要從事乳腺病、甲狀腺病、肛腸病、周圍血管病、糖尿病足壞疽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