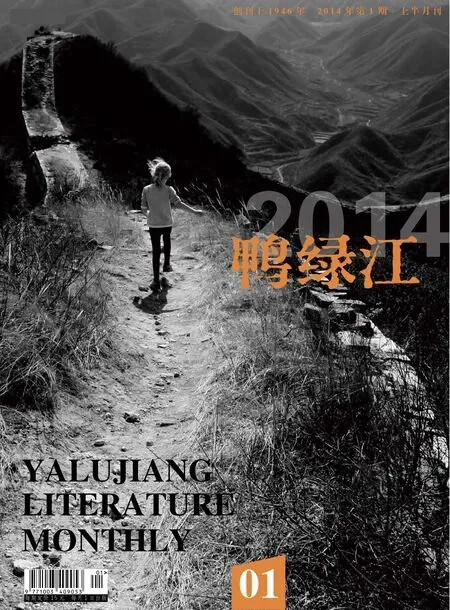懷念史鐵生(外一篇)
趙會喜
懷念史鐵生(外一篇)
趙會喜
HUAI NIAN SHI TIE 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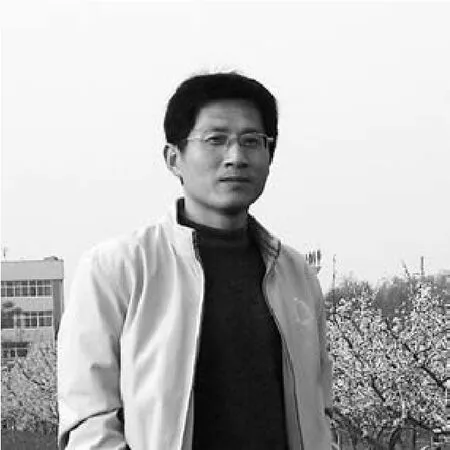
趙會喜,網(wǎng)名三月雪,1970年5月生,河北省魏縣人,現(xiàn)供職于魏縣文聯(lián)。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邯鄲市青年詩人學(xué)會副會長,現(xiàn)為《魏州文學(xué)》雜志執(zhí)行主編,曾有作品入選多種選本,2010年出版詩集《風(fēng)中的故鄉(xiāng)》等。
一
深邃的天幕上,星斗像是無數(shù)只螢火蟲在跳舞,在唱著奶奶講給童年的歌謠。它們每飛舞一下閃一下,亮光都是在輕輕地歌唱,這不是夢幻。
螢火蟲在歌唱,這是真的,我常常為此感到生命只是旅途上的一次邂逅和意外。寫到這里的時候,內(nèi)心是疼痛的,在我無數(shù)次的敬畏和祈禱里,那位為病魔所抗?fàn)幍淖骷乙呀?jīng)離我們而去了,他多像一只會跳舞會講故事會唱歌的螢火蟲啊!
《我與地壇》這篇文字我給學(xué)生講了很多次,每次都不能深刻地理解他對人生的追問,每次都想著要是能夠和他說說話或者聯(lián)系一下該多好,但這些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成為了不可能,文字僅僅代表了一種歷程一種訴求。
他這樣說道:

“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后事情終于弄明白了: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jīng)順便保證了它的結(jié)果……這樣想過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上帝在召喚”,那是他說他的母親受了太多的苦難,上帝實在不忍心才讓自己的母親到天堂安息的!而現(xiàn)在他呢?還能夠給我們說這樣的話么?我們只能夠聽見蕭索的風(fēng)從林梢上穿過,從心的湖面掠過,很干凈地掠過。
在此引用他的文字,也是對他最好的追憶和懷念的方式,他需要安靜下來,需要把所有的病痛所有的事情都靜靜地放下來,這是上帝用另一種安詳?shù)姆绞皆诟嫖靠嚯y作家的靈魂!

1991年夏,史鐵生(前坐者)、劉震云(后左一)、莫言(后左二)、余華(后左三)來遼寧文學(xué)院講
地壇上沒有他的墓志銘,只有淡淡閃耀著的辰星!
二
他對瓢蟲的童真對蜂兒的叮嚀對蟬蛻的寂寞對草葉的聆聽,都詮釋著他的生活也像眼前的大自然一樣素凈和美好。我不能夠用太多的詞語來說明一位作家對文字的疼惜,因為那是他生命和苦痛的化身,也是他生命的長度和深度的提純與陳釀,所以我在句式的表述方面也有意貼近史鐵生的語氣,不厭其煩地表述也許正是他想在人間多給我們留下一些叮嚀和諦聽。
——活著多好,像一個音符一樣飄來飄去,在荒涼并不荒蕪的地壇的濃蔭里,在蜿蜒的撲朔迷離的胡同里,在高大的合歡樹葉子掩映的小窗戶上面!
是啊,還可以在那對兒中年夫婦不經(jīng)意成了老年的米色或者黑色的風(fēng)衣里,還可以在一直唱著《貨郎與小姐》交了好運氣的那個小伙子的暮靄時分的音色里,還可以在老頭飄忽不定的酒葫蘆里以及生不逢時的苦苦練長跑的那位中年漢子的期望里,也可以在高大的欒樹下漂亮而又弱智的姑娘的淚水里,也可以在粗壯的海棠樹下奶奶無盡的張望里!
唉,濃得化不開的葉和花啊,有一天會有意或者無意地落滿地壇落滿這院子的小徑而又無影無蹤!
史鐵生這樣說道:“離開我,在窗上老海棠樹的影子那兒停留一下,繼續(xù)離開,離開一切聲響甚至一切有形,飄進黑夜,飄過星光,飄向無可慰藉的迷茫和空荒……”
三
這些天,我一直在教學(xué)之余閱讀史鐵生的小說,因為我的學(xué)生還在等著我給他們講“欄桿拍遍”呢。我身邊的人很少能夠堅持看他的小說,我這樣說并不是他的小說不好,而是那樣的氛圍和氣息,他們無法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都無法耐住那樣的寂寞和苦痛,更不要說一顆忘塵的心了!
他的小說《原罪》里那個整天整夜都躺在狹小的床上,用一面面相互映照的鏡子隔著窗戶看外面的世界來為阿冬和我講述一個又一個所謂的“神話”故事的十叔,不就是他的一個同病相憐的縮影嗎?十叔能夠望到“墻那邊的一大片灰壓壓的屋頂和幾棵老樹,最遠(yuǎn)處是一座白色的樓房和一塊藍天……十叔永遠(yuǎn)看到的就只是這些東西,但那兒有他永遠(yuǎn)也講不完的故事”,一直看到那位女孩慢慢長成大姑娘,直看到有小伙子來追求她。我多想問問那湮沒在晨昏里的凈土寺的兩個尼姑她們的愛情呢,又在哪里尋找呢?
十叔也應(yīng)該有愛情的,當(dāng)他講到這里的時候他不說話了沉默了好久好久哎!
還是聽聽史鐵生為玩到阿冬用鐵皮制作的手槍是怎樣給阿冬講神話故事的吧,那才叫絕呢——
“你知道為什么會刮風(fēng)嗎?”阿冬搖搖頭,“你不知道吧?刮風(fēng)是老天爺出氣兒呢。你知道為什么會刮特別大特別大的風(fēng)嗎?”阿冬又搖搖頭。“那是老天爺跑累了喘呢,不信你試試。”……我就瞎胡編:“你知道為什么會下雨嗎?”
“為什么?”我隨口說道,“那是老天爺撒尿呢。”不料阿冬卻笑起來對此深覺有趣,于是我也很興奮而且靈感倍增。我又說:“下雪你知道嗎?是老天爺拉屎呢。”阿冬使勁笑使勁笑。“打雷呢?打雷你知道嗎是老天爺放大屁呢!”“老天爺——放大屁——!”阿冬就喊,笑個沒完。“轟隆轟隆,老天爺放屁可真響,是吧阿冬?”
“轟隆——!轟隆——!”我們倆便坐在臺階上齊聲喊,“老、天、爺!放、大、屁!轟隆——!轟隆——!老、天……”這時候阿夏跑出來了,站在門檻上聽我們喊了一會兒,讓我們別胡說八道了。我們反而喊得更響,更高興了。
當(dāng)我看到這里的時候,我的心不由得一震,那不就是史鐵生快樂幸福而又充滿純真的童年么?他多需要這樣平凡而又歡愉的日子啊!而他真的不能夠,一個癱瘓而又患有尿毒癥的人是沒有這樣的自由的,他把那份最美好的純真給了眼前這個讓他無比眷戀的灰暗的世界!
盡管這篇小說的結(jié)尾我不想或者不同意作家以科學(xué)真知的方式結(jié)尾,我想讓十叔以夢幻的想象像飛得滿屋子泡泡該有多好啊。泡泡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飛得滿屋,飛出窗口,飛得滿天。十叔說:“阿夏你看哪,飛得多漂亮!”,這樣就會讓我們的心里好受些,而不至于非要把十叔的病痛和結(jié)局揭穿不可。
四
“莽莽蒼蒼的群山之中走著兩個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兩頂發(fā)了黑的草帽起伏躦動,匆匆忙忙,像是隨著一條不安靜的河在漂流。無所謂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也無所謂誰是誰……”這源自《命若琴弦》的文字再次震撼了我們的心靈。我們何去何從?宿命和罪孽是否存在?我們能夠抵償么?它會不會隨著時間的淘洗而隱去它的本色?比如我們看到一片葉子上所附著的生命,慢慢變黃變焦變枯直至撲向大地的懷抱?
直到有一天,老瞎子用一輩子彈斷的八百根琴弦,才知道一切都是枉然,他的心弦斷了,也空了;但他知道他的徒弟還在,還在等待著他的歸來,等待著能夠也讓他重新看到光明,再看到茫茫而又清晰的愛情!
而這些真的沒有發(fā)生。
他們沒有能夠選擇,這些都擋在了大山之外,而隱現(xiàn)在眼前的是野兔子、山雞、野羊、狐貍和鷂鷹和茫茫的土坡……
人生又何嘗不是一把琴弦,拉不緊就彈不響的琴弦!也許只有永遠(yuǎn)地扯緊歡跳的琴弦,只有無休無止地彈奏下去,不必去看那張無字的白紙……
我又想到他的《最后的練習(xí)》有這樣的話:
最后的練習(xí)是沿懸崖行走
夢里我聽見,靈魂
像一只飛虻
在窗戶那兒嗡嗡作響
在顫動的陽光里,邊舞邊唱
眺望即是回想
誰說我沒有死過?
出生以前,太陽
已無數(shù)次起落
悠久的時光被悠久的虛無
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義
卷土重來
我們以前都曾以各種存在方式來過這里,來到這陌生而又靜默的這里,都有一次或無數(shù)次生命的盛典;不曾邂逅的邂逅,不曾相聚的相聚,感覺到歡愛、陽光、空氣和藍色的自由,無拘無束地存在著,歌唱著,這些永遠(yuǎn)都需要用我們的溫暖相互擁抱!
不能夠忘懷的人兒,永遠(yuǎn)都是眷戀的微笑和潸然的淚水,“永遠(yuǎn)”這兩個字在人生中一定要用好,當(dāng)我們不懂的時候,我們無意苛責(zé),無意憐惜!
他在隨筆《重病之時》中說道,妻子沒日沒夜地守護著我,任何時候睜開眼,都見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個。我說,這一回,恐怕真是要結(jié)束了。她說,不會。我真的活過來。太陽重又真實。晝夜更迭,重又確鑿。我把夢里的情景告訴她,她反倒脆弱起來,待我把那支歌唱給她聽,她已是淚眼婆娑。那就是為心愛的妻子希米寫的文字《希米,希米》:
希米,希米
你這順?biāo)瘉淼暮⒆?/p>
你這隨風(fēng)傳來的欣喜
聽那天地之極
大水渾然、靈行其上
你我就曾在那兒分離
希米,希米
你來了黑夜才聽懂期待
你來了白晝才看破樊籬
聽那光陰恒久
在也無終,行也無極
陌路之魂皆可以愛相期?
夜空的星光現(xiàn)了,那是彼此的追憶,我們不再迷惘,螢火蟲又都在我們的眼前搖曳,開始了歌唱,開始了輪回……
懷念孫犁
人生蕪雜,該從何處說起?
點點斑痕,都將隨風(fēng)而慢慢隱去;而他的文字卻像那抹不掉的星輝,縈繞在我們的心頭愈加明晰。當(dāng)生活讓我們感到疲憊或者無法逾越的時候,這抹星輝更是照徹了我們內(nèi)心的灰暗和塵埃,讓我們在生活的旋渦里永遠(yuǎn)不要停下前行的腳步。
不虛美,不隱惡,是他所期望的;其文直,其事核,是他所恪守的。每一個字都應(yīng)該由心而發(fā),由骨髓而發(fā),這正如泉水一定要濾過巖石、沙粒以及深扎在泥土里的根須,才能夠清冽和甘甜。
孫犁生于戰(zhàn)亂年代,其顛沛流離,可想而知。他在《生辰自述》中有這樣的文字:燕南塞北,雨雪冰霜,屢遇危險,幸未死亡。由于常年在外奔波,飯食無著,最終導(dǎo)致了他身體上的病痛——幾乎不能夠再度握筆寫作,十年的時光都在醫(yī)院里療養(yǎng)度過;隨之而來的“文革”,再次熬過了他十年的精神生活上的磨難。也許正是這樣,他的文字才澄澈如溪,流露出人性中最美好、最善良的東西!正如孫犁自己所說的,這些作品“有所見于山頭,遂構(gòu)思于澗底,筆錄于行軍休息之時,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題擬高巖而挺立”。
“簞食瓢飲,青燈黃卷,與世無爭,與人無憾”。一位作家不論在時事多難還是風(fēng)平浪靜的年代,都能夠堅守心中的那份平淡、那份高潔,不以惡、不以虛美而轉(zhuǎn)移,在駁雜的歲月里顯得平凡而又神圣!這些,孫犁先生做到了,他的文字成了自然和生活中最美的歌唱,隨著時光的淘洗而愈漸深邃和幽廣。
在戰(zhàn)爭年代,在阜平的日子,這窮山惡水,這地瘠民貧,都浸入了他的骨髓。孫犁回憶說:“我們想起來,那在全中國,也算是最窮最苦的地方。好年月,農(nóng)民也要吃幾個月的樹葉……但是阜平,在我們這一代,該是不能忘記的了,把它作為搖籃,我們在那里成長。那里的農(nóng)民,砂石,流水,紅棗,哺育了我們。”他在《山地回憶》中這樣說道:“我看了看我那只穿著一雙踢倒山的鞋子,凍得發(fā)黑的腳,一時覺得我對于面前這山,這水,這沙灘,永遠(yuǎn)都不能夠分離了。”在這貧瘠的土地上,我們看到的是人們的淳樸和善良而愈加豐厚。這就是要生存下去的理由,這就是那個時代最簡單的夢和想——活著,生活,命運的抗?fàn)帲?/p>
作家的生命是大自然賜予的,當(dāng)我們無望甚至絕望的時候,就將本真的目光投向養(yǎng)育自己的一方水土。孫犁在《關(guān)于果》這篇文字里流露出對酸棗樹由衷的敬意,那樹梢上的一顆最紅的誘人的果子,對于饑餓中的人來說是無法抗拒的。他環(huán)繞著樹身走著,望著,計劃著,無法將那枚果子投擲下來,卻反而脖頸僵了,筋疲力盡了,只好望著天空,面對著四方。第二天行軍的時候就暈倒在山路上,再次醒來時,是一棵眼前的酸棗樹救了他——他就一把將它的果子、葉子、樹枝和針刺都塞到了嘴里。
依稀,孫犁在生活困難的時候,老家里的人讓他在天津買本小《新華字典》還不忘將發(fā)票一并匯過去,這樣對方可以把這一筆微薄的款項再還給自己家里以供妻兒老小作生活上的用度。有一次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來看望他時,他沒有更多的生活盈余給她們母子作路費,而她們恰恰又滯留在任丘的半路上,當(dāng)他接到她們的時候,妻子半埋怨似的說,為什么不昨天來接我啊,我們已經(jīng)餓了兩頓了!而他一句話也沒有說,所有的話語和酸楚的淚水都默默地流在心里了。作為丈夫,他不是不愛自己的妻子,他深切地知道自己常年在外奔波和工作,整個家庭的重?fù)?dān)都落在妻子的身上!有生之年,妻子看望他的次數(shù)也是屈指可數(shù)。
他在《亡人逸事》里這樣說道“……雖然我們結(jié)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說的:相聚之日少,分離之日多;歡樂之時少,而相對愁嘆之時多耳。我們的青春,在戰(zhàn)爭年代中拋擲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變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過去,青春兩地,一別數(shù)年,求一夢而不可得。今老年孤處,四壁生寒,卻幾乎每晚夢見她,想擺脫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說法,這可能是地下相會之期,已經(jīng)不遠(yuǎn)了……”
作為作家,作為詩人,作為那個時代的履歷者和見證者,他用自己的良心浸潤了每一個文字,支撐了它們固有的清骨。按他自己的話說,生活就像那時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隨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塊,隨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來。
“夢中每迷還鄉(xiāng)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故鄉(xiāng)的人物風(fēng)貌,對孫犁來說是難以割舍的,魂牽夢繞的。饑寒快樂的童年在那里度過,兒時的玩伴,也許像夢一樣在他的眼前浮現(xiàn),他們還會在漫天野地里奔跑著,尋視著,歡笑并打鬧,追趕和競爭。還有清晨,還有露水,還有霜雪,他們的小手凍得通紅……瞎周、楞起叔、根雨叔、疤增叔、秋喜叔、大嘴哥、大根、刁叔、老煥叔,也許他們還都在,夢里,幻里,他們都還在講述著各種故事,也不長,也不短,走著,而后又是慢慢地隱現(xiàn)著……那坍圮的老屋還在,而做飯的人早已逝矣。“那總是一個標(biāo)志,證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戶。人們路過那里,看到那破房,就會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會把我忘記了。”愈到晚途而愈感覺到故鄉(xiāng)離自己越來越遠(yuǎn)了,再也無法回到桑梓了。
也許故人的包袱皮兒還在,那“人造絲”白底紫花的包袱皮兒讓他在淚水里回味了多久啊:年輕時,最喜愛書,妻最喜愛花布。妻子一直用著,經(jīng)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又帶到天津,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多次翻箱倒柜地抄家,一直到她去世。她的遺物,死后變賣了一些,孩子們分用了一些。眼下就只有兩個包袱皮兒了,經(jīng)歷了整整五十年,而喜愛它、使用它的人,亡去已經(jīng)有十年了。有一次,自己在北平作小職員的時候,曾經(jīng)買過兩丈花布寄到妻子的家里。妻子在臨終前再次問起這件事,“你那時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他說,“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妻子閉上眼睛,久病的臉上,展現(xiàn)了一絲幸福的笑容。在笑容里妻子的嬌嗔也許還在,記得從外地回來路過妻子的家門,想讓她跟自己一起回家,而妻子卻說:明天你套車來接我吧。
人生中還有多少個明天啊?還有多少個明天來等待至親的人來相逢和相聚啊!
也許案頭上的菜花還在,它亭亭玉立,明麗自然,淡雅清凈;它淡遠(yuǎn)虛無,不可琢磨,只能引起惆悵。“人的一生,無疑是個大題目。有不少人,竭盡全力,想把它撰寫成一篇宏偉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寫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頭菜花一樣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為文章的題目。”(《菜花》)
我想:當(dāng)你擁有了像菜花一樣清淡的心境,又這樣執(zhí)著和堅守,那還有什么悔恨呢?
人生就是這樣,這樣就是人生!
當(dāng)我再次回首的時候,孫犁大師的文字正如浩瀚夜空里的一抹星輝,在我們的頭頂上空依然照耀!
責(zé)任編輯 葉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