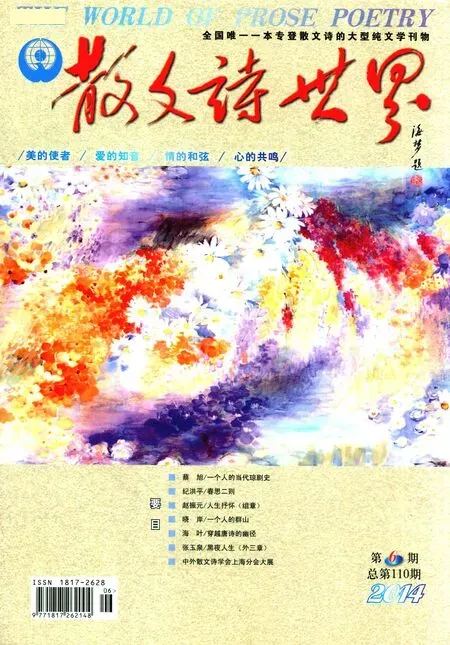我是一條消失的弄堂(外一章)
朱鎖成
我是一條消失的弄堂(外一章)
朱鎖成

朱鎖成,上海人。插過隊(duì),當(dāng)過礦工,做過記者編輯。1992年出版散文詩集《最后的傾訴》。作品入選多種選本。安徽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
魚鱗瓦、黑磚墻、白熾燈,這個(gè)城市最具特色的記號(hào)消失了。
黃浦江、輪渡、萬噸輪,這個(gè)夢里常常擁在枕邊的聲浪離我遠(yuǎn)去了。
因?yàn)橐粋€(gè)并不了然的動(dòng)詞,我這條滾過鐵圈、縈繞過煤煙、響過糞車搖鈴,炸響過除夕鞭炮的弄堂消失了。
消失的是繁華背后的身影。消失的也許是底層的潮濕和嘈雜。但我是這個(gè)城市組成的最廣大最普通的系列。
我舉過十月的手臂,和鮮花紅旗一起揮舞在人民廣場。
我舞過五月的銀鐮,響應(yīng)過黃昏的那一次潮漲。
我這條窄窄的弄堂開始遠(yuǎn)離城市,遠(yuǎn)離生我養(yǎng)我的搖籃,第一次孤單地瑟縮在異鄉(xiāng)。
我自信,我是一條精選的弄堂。雖然我的手掌有點(diǎn)稚嫩,雖然我從沒出過遠(yuǎn)門,可我以一代人的誓詞握緊了鋤把,以浦江之水澆灌了我的飽滿和憂傷。
弄堂,許許多多的城市的種子,是搖曳在小村的大面積播種,匍匐在小村的另一種偎躺。
如今,我又一次告別,不再有痕跡。
這里會(huì)是一座公園,有我棲息的長椅。
這里會(huì)是一間教室,有我旁聽的燈光。
這里會(huì)是一張病床,有我詢問的診筒。
可這里又崛起一幢住宅、酒樓和咖啡吧。
懸掛的窗簾濺滿了燈紅酒綠,這里原不是車鈴的停車場。
我只是隱隱約約聽到,地毯褻瀆的地方,舉行過一次開業(yè)典禮,被邀請的席卡當(dāng)然不會(huì)有弄堂。
我是一條消失的弄堂。
也許,城市就是在一次次消失中變得美麗和強(qiáng)大。如若那樣,我不也消失得其所,消失得還有分量。
而我也有了一個(gè)屬于自己的走廊,我傾聽這個(gè)城市每天的潮聲,收集這個(gè)城市一樣美的陽光。
城市已經(jīng)沒有我的狹長。
我只是希望,我這個(gè)分散的走廊,有一天會(huì)變得更加的敞亮……
撫 摸
撫摸是最初的哺乳。
背上生出痱子,手碰破了皮,母親的撫摸是滑潤的痱子粉,清涼、消毒。
暑假是一堵密不透風(fēng)的墻。老師的家訪是撫摸的清風(fēng),飄拂在瘦瘦的小弄堂。
即使到農(nóng)村插隊(duì),大嫂端來的手搟面是一碗撫摸,鄉(xiāng)妹子給我縫的夕陽是絲絲縷縷的撫摸,老隊(duì)長的旱煙袋也是撫摸。空曠的不墜的篝火,夜,不再漆黑,思念,由暗轉(zhuǎn)紅。
來到高高的井架,來到黑塵和硝煙叢生的掌子面,培訓(xùn)是一種撫摸,礦帽和礦靴是一種撫摸,老書記坐在床沿的談心是一種撫摸,培育卑微的種子更是一種撫摸。
撫摸無處不在:房子漏了,瓦趕來撫摸。被絮破了,聞風(fēng)而動(dòng)的棉花伸出潔白的纖手。不幸躺倒的手臂,白色的床單和罐頭笑吟吟地?fù)崦倚乜凇?/p>
即使大地冰凍,還有月色撫摸。
即使大霧鎖江,還有城市輪渡。
即使電閃雷鳴,還有彩霞等待飛虹。
撫摸是人世間最偉大的母乳。是天空遼闊的甘霖,是弄堂拐彎處一盞路燈,是開啟心靈之鎖的一把鑰匙,是戀人的一記輕吻,是垂危時(shí)親人的一聲撫慰。
只要?dú)q月有淤積和堵塞,人有跌倒和低落,就期盼撫摸。
浪撫摸船,歌撫摸夜,愛撫摸心。
現(xiàn)在還有撫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