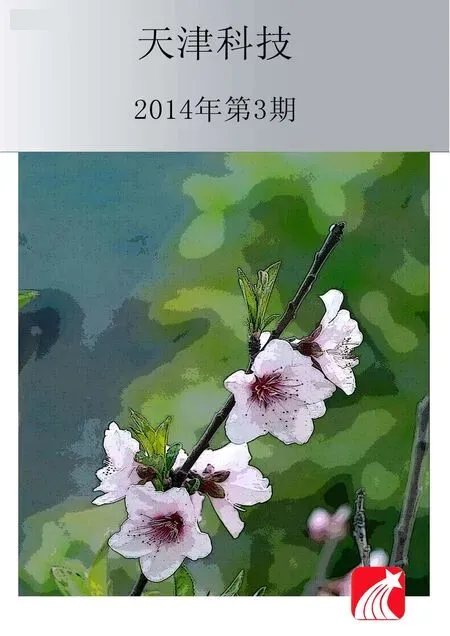斜視弱視的臨床與基礎研究
趙堪興
(天津市眼科醫院 天津 300020)
0 引 言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到 2020年全球根治可避免盲,并將兒童盲作為“視覺 2020”行動的 5個重點領域之一。兒童盲的特點是盲齡長,對患者的生活及社會就業的影響更大。在各種兒童致盲性眼病中,弱視是引起兒童盲與低視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斜視嚴重影響視覺發育及雙眼單視,是造成兒童立體盲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引起弱視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些遺傳性眼病嚴重影響視覺發育和正常雙眼視功能的建立,具有極高的致盲率。在我國,斜視患病率為 3%,弱視的患病率為2.8%。該項目將基礎與臨床研究相結合,從疾病相關結構與功能的各個方面展開深入系統研究,在兒童斜視弱視的流行病學、學齡前兒童弱視的診斷標準、弱視的多導 VEP、細胞電生理、分子生物學與功能磁共振研究,眼外肌直肌滑車(Pulley)的臨床研究,先天性顱神經發育異常疾病群(CCDDs)的臨床表型、神經影像學、遺傳學特征,復雜性斜視術式創新,斜視手術的微創技術與規范化,相關遺傳性眼病的發病機制及快速遺傳學篩查技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技術創新和科學發現。
1 弱視的臨床與基礎研究
1.1 開展了首個唯一以人群為基礎的大樣本兒童斜視與弱視的流行病學研究,確立了學齡前兒童弱視診斷標準[1,2]
弱視是視覺發育期內由于異常視覺經驗引起的單眼或雙眼最佳矯正視力下降。兒童弱視如果不能早期發現和及時治療,可造成終生視力低下和缺少完善的立體視功能。但長期以來我國兒童弱視的診斷沿用成人視力標準,機械地根據原弱視診斷以視力低于0.9為標準,由此造成了學前兒童弱視診斷擴大化的情況。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即便是高估 1個百分點的患病率,造成的影響也是很嚴重的。弱視的過度診斷影響了兒童身心健康,造成數百萬家庭不必要的經濟與社會負擔,浪費了醫療資源。2004年趙堪興教授組織團隊開展了首個以人群為基礎的大樣本兒童斜視弱視與視力發育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機械地根據矯正視力低于0.9作為弱視診斷標準,受檢人群中“弱視”檢出率可高達 5.4%,其中3~5歲兒童“弱視”檢出率達10%以上。但是,如果結合正態分布法和百分位數法計算結果,將不同年齡段兒童設立不同的正常視力下限,該組兒童的“弱視”檢出率為 2.8%,且各年齡組兒童的“弱視”檢出率無明顯差異。由此表明,以矯正視力低于 0.9作為弱視診斷標準對于低齡兒童顯然偏高,易將一些視力發育緩慢的低齡兒童歸入弱視范疇,錯誤地提高了弱視檢出率,導致部分兒童誤診和誤治。該研究明確了我國3~15歲兒童視力發育的規律,提出了學齡前不同年齡兒童的正常視力標準,即:年齡在 3~5歲兒童視力的正常值下限為 0.5,6歲及以上兒童視力的正常值下限為 0.7。該標準已被國內專家廣泛接受,取得了專家共識,并寫入我國高等醫學院校本科規劃教材《眼科學》(第7版、第8版)。該標準的推廣規范了學齡前兒童弱視診斷,抑制了弱視診斷的擴大化,極大降低了在弱視診療中醫療資源的浪費,弱視亂治現象得到有效控制。如按每年減少 1個百分點的擴大診斷,每年即可減少約 22億元衛生資源浪費。同時,該研究成果也推動了弱視的早期篩查,推動了國家衛生計生委《弱視防治技術服務規范》的修訂和《兒童眼及視力保健技術服務規范》的實施。
1.2 開展了一系列弱視及視覺發育的基礎研究,創新了弱視功能評估方法[3,4]
傳統觀點認為單眼弱視對側眼是正常的,弱視患者的非弱視眼與正常眼有無區別一直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常規的視覺功能檢測手段如視力檢查、傳統的 VEP檢查等均難以解決這一難題。趙堪興教授在國內率先研發了多導VEP地形圖電生理系統用于弱視兒童的功能研究。該研究在國際上首次發現了內斜視弱視非弱視眼全視野圖形刺激也有輕度半視野刺激的效應,同時半視野刺激內斜視弱視非弱視眼鼻側視網膜的反應小于刺激顳側視網膜。該研究表明了多導 VEP地形圖可以發現傳統單導 VEP不能揭示的現象,為重新認識“非弱視眼”提供了嶄新的機會。該研究提示對內斜視弱視的對側眼稱“正常眼”或健眼顯然不妥,提出了對側眼并非“健眼”的理論假說。在此基礎上,在國內率先開展了一系列的有關弱視及視覺發育的細胞電生理、分子生物學、功能磁共振和眼球運動功能研究,取得了創新性發現。對單眼視覺剝奪后視覺發育關鍵期內以及非關鍵期內貓視皮質神經元內即刻早期基因的表達變化進行觀察,發現其表達受到視覺經驗的調控,即單眼剝奪可抑制其表達,視覺刺激可以促進其表達,提示了弱視及視覺發育過程中表觀遺傳學機制的參與,為弱視的早期治療提供了理論依據。血氧水平依賴的功能磁共振是具有高空間分辨力的無創傷性腦功能研究方法,本研究對斜視性弱視患者的功能核磁共振改變進行研究,發現斜視性弱視組雙眼像素指數下降,在較高空間頻率刺激時,弱視眼驅使皮層神經元平均活動水平較對側眼降低,這與單細胞電生理、視覺誘發電位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首次發現了斜視性弱視患者雙眼像素指數較屈光參差性弱視患者雙眼像素指數減少更明顯,提示兩種弱視類型存在不同的皮層機制。既往觀點認為弱視的發病部位主要位于視皮層,本研究通過功能磁共振研究首次發現小腦及皮層下結構活動的異常,提示弱視除了視覺感知系統的異常,可能存在眼球運動處理相關區域的異常。這一假說被本項目組隨后運用高速視頻眼動記錄的方法對弱視患者進行的研究結果所證實,研究成果被著名期刊引用,并被美國科學促進會作為 Breaking News報道。
2 斜視的臨床與基礎研究
2.1 從多角度開展了斜視的病因學研究
采用顯微解剖、影像重建、臨床觀察等手段創建了眼外肌 Pulley異常性疾病的術前病因診斷及術中 Pulley定位技術,采用分子遺傳、神經影像、臨床觀察等手段驗證和豐富了CCDDs疾病群的“神經發育缺陷”假說。[5,6]
斜視的病因既存在中樞性因素也存在外周性因素,但長期以來關于斜視的具體發病部位及發病機制卻不甚清楚,這嚴重影響到對各種復雜性斜視的明確診斷以及治療方式的創新。趙堪興課題組借助多種技術手段,從多角度開展了斜視的病因學研究,在斜視的中樞性與外周性病因學研究方面均取得重要創新性研究成果,并推動了相關手術技術的創新。在斜視外周機制的研究方面,眼外肌 Pulley被認為是由膠原纖維、彈力纖維和平滑肌形成的包繞在眼外肌周圍的環狀結構。但 Pulley是否存在、是否具有功能,Pulley異常是否導致斜視等問題長期存在爭議。此外,眼科醫生所熟悉的是 Tenon囊、節制韌帶、肌鞘這些與眼外肌有關的經典解剖結構,如何在術前確定患者存在 Pulley位置異常,如何在術中尋找 Pulley的位置并通過手術矯正因 Pulley異常引起的疑難斜視是臨床醫師面臨的迫切問題。趙堪興課題組在國內率先開展了眼外肌直肌 Pulley結構組織學、生物力學和影像學的再創新研究,明確了 Pulley具有改變眼外肌力作用方向的功能,確認了 Pulley位置異常是引起某些復雜的非共同性斜視的病因,首次明確了 Pulley在眼眶中的空間分布、臨近組織關系、術中直視下解剖定位標志,豐富了國際該領域的研究成果,為非共同性斜視的臨床診斷和手術設計提供了指導。該項研究成果寫入我國眼科學權威著作《中華眼科學》。在中樞機制的研究方面,既往國際主流觀點認為先天性眼外肌纖維化(CFEOM)、Duane眼球后退綜合征(DS)、Moebius綜合征(MS)等特殊類型斜視的病因是肌源性的。Brown于 1950年首次報道了這類疾病,并根據其眼外肌運動限制性的臨床特征,以及在手術和眼外肌活檢中發現大量纖維結締組織取代了眼外肌,而將此類疾病歸因于眼外肌原發性纖維化所致。趙堪興課題組利用天津市眼科醫院作為全國斜視疑難病診治中心地位的有利條件,對此類疾病開展了長期的病例與家系收集工作,采用分子遺傳學、神經影像學并結合臨床特征觀察等方法,以多個方面的有力證據改變了傳統的觀點。趙教授課題組在國際上率先鑒定了數個先天性眼外肌纖維化KIF21A 突變位點(2860C>T、2861G>A、84C>G),KIF21A是一個編碼驅動蛋白的基因,趙教授首次提出CFEOM與KIF21A不能輸送第III顱神經運動軸突、神經肌肉接頭和眼外肌發育所需的物質有關,進一步支持了這類特殊類型斜視是由支配眼球運動的顱神經發育異常所導致的嶄新觀點。為進一步證實和豐富這一新的學說,趙教授課題組又利用神經影像學手段對 CFEOM、DS、MS等特殊類型斜視開展了深入研究,揭示了這一系列疾病存在共同的神經影像學特征,即存在一條或多條顱神經先天發育異常。由于上述系列發現,這類疾病目前已被歸類為一組新的疾病群,即先天性顱神經發育異常疾病群(CCDDs)。趙教授課題組關于 CCDDs所開展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先后寫入《眼科學》(第 7、8版)、《斜視弱視學》(第1版)等我國醫學院校本科規劃教材。
2.2 基于斜視病因學研究成果
創新了CCDDs疾病群、旋轉性斜視、高度近視眼限制性斜視、垂直分離性斜視、合并斜視的先天性眼球震顫等復雜性斜視的手術術式;發展了斜視微創和顯微手術技術,參與確立了斜視手術技術評估國際規則。[7,8]
基于斜視病因學研究成果,趙堪興課題組創新改進了 CFEOM、DS等 CCDDs疾病群的手術矯正方法,創新改進了矯正外旋斜視術式及矯正高度近視眼限制性內斜視術式,創新了合并斜視的先天性眼球震顫手術術式,研究和再創新了矯治垂直分離性斜視的上直肌后固定術和下斜肌轉位術。傳統觀點認為,對存在明顯的斜視和代償頭位的DS患者行手術治療,而對于原在位無明顯斜視但有明顯的眼球后退的DS患者不予手術。趙堪興教授突破禁區創新了拮抗肌同時后徙技術,改善了 DS患者眼球突出度,效果顯著。旋轉性斜視為常見的復雜性斜視類型,因造成復視、物象傾斜、眩暈等癥狀使患者工作生活及精神心理受到嚴重影響,由于其病因多由于上斜肌麻痹所致,而上斜肌的特殊解剖學特點使其具有復雜的力學機制和生理功能,這給手術矯正這類斜視增加了難度。日本學者 Harada-Ito曾提出利用上斜肌前部纖維主要行使使眼球內旋的功能將上斜肌前半部分予以簡單加強,趙堪興教授在國內首次對該術式做出了創新改進,使上斜肌前部纖維平面與視軸跟趨于垂直,加強了上斜肌的內旋作用,更加有效避免手術引起的垂直斜視,該改進術式已在國內廣泛推廣。高度近視眼限制性斜視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獲得性斜視,表現為進展性內下斜視及后期眼球外轉和上轉運動障礙。以往傳統的內退外縮術或 Jensen直肌連接術的手術效果不理想,術后易復發。趙堪興教授采用影像學手段證實此類斜視存在眼外肌移位和后鞏膜葡萄腫及眼球后極向顳上疝出,據此對矯正此類斜視的Yokoyama術進行了重要創新改進,有效糾正了高度近視眼限制性內下斜視的眼球后極顳上方脫位,同時眼位及眼球運動獲得明顯改善。先天性眼球震顫的手術矯正常采用 Anderson法、Kestenbaum法或Parks法,但此類手術主要適用于單純先天性眼球震顫有代償頭位者,一旦同時還合并斜視,則使得手術的設計變得復雜,增加了術后效果的不確定性,甚至難于一次手術獲得良好的效果。趙堪興教授首次提出了對于有代償頭位合并斜視的先天性眼球震顫病人采取主導眼手術矯正頭位并另眼手術矯正斜視的術式,使得此類復雜性眼球震顫患者通過一次手術獲得滿意效果,該法在全國獲得廣泛推廣。長期以來斜視手術屬于外眼手術范疇,普通水平斜視手術操作相對單純,易于掌握,但是對于垂直斜視、旋轉性斜視、CCDDs等復雜性斜視因涉及專門的理論知識、檢查技術和手術設計,令非專科醫師望而生畏,又由于垂直肌和斜肌解剖及功能的復雜性,更增加了手術的復雜性和難度。趙堪興教授帶領課題組通過 10余年顯微手術實踐以及對相關手術器械及技術的改進,逐步形成了斜視手術微創理念和操作體系,把顯微外科技術成功引入斜視手術領域,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直視下手術”,實現了術后眼球運動和雙眼視功能的最佳恢復,降低了各種并發癥的風險。趙堪興教授的手術理念及一系列手術創新獲得了國際認可,并受邀作為高級作者參與制定并發表了國際斜視手術評估規則。
3 相關遺傳性致盲眼病的研究[9,10]
遺傳性眼病在兒童中具有極高的致盲率,嚴重影響視覺發育和正常雙眼視功能的建立,其中視網膜色素變性(RP)是以夜盲為主要特征的重要致盲性遺傳眼病。趙堪興教授帶領團隊通過對中國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 RP(adRP)進行分析,定位了一個新的 RP連鎖位點,被國際基因命名委員會(HGNC)命名為RP33。此位點為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首個(目前唯一)RP位點。本項目還首次克隆了SNRNP200基因,并通過在酵母上的功能實驗,證實其為 RP致病相關基因,提出了 adRP發生的新機制:即 pre-mRNA剪接缺陷的分子基礎可能是源于 SNRNP200依賴的U4/U6解旋功能的缺陷,而非 U4/U6-U5的組裝缺陷。佛羅里達大學的Swanson教授指出:“U4/U6解旋功能的缺陷是研究RNA剪接與疾病關系的重要發現之一”。[11]本研究成果獲多國科學家追蹤研究,被瑞士及英國科學家證實 SNRNP200也引起歐美高加索人 adRP。[12,13]基于 pre-mRNA 剪接基因是 adRP的重要病因,課題組建立了對 RP患者進行快速遺傳學篩查的有效方法,在全國廣泛推廣。
4 項目的推廣
通過該項目的開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斜視與小兒眼科”的學科建設。共主辦全國性學術會議14次,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學習班 34次,主持各類專題講座200余次,完成斜視弱視進修學習班72期,促成了與美國斜視與小兒眼科學會(AAPOS)合作,創辦了中國斜視與小兒眼科學科帶頭人培養項目(AAPOS-TJEH Project),舉辦該項目培訓 19期,完成國際化人才培訓600余人次,為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打造了發展平臺。通過本項目的開展,已為全國培養了百余名學科帶頭人和千余名的學術骨干,培養畢業博、碩士研究生 100余人,其中 48人已取得博士學位,一批學生已成長為“985”和“211工程”院校的學科帶頭人和學術骨干。本項目發表論文 289篇,其中 SCI論文 44篇,最高單篇 IF=12.3,他引1,455次。主編人民衛生出版社《眼科學》教材和專著 5部,副主編專著 2部,參編教材和著作多部。項目成果在國內各知名院校和醫療單位以及基層單位普遍推廣,開發的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無保留地輸出給全國各地,有力推動了學科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1] 趙堪興,鄭曰忠. 要特別重視兒童弱視診斷中的年齡因素[J]. 中華眼科雜志,2007,43(11):961-964.
[2] 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斜視與小兒眼科學組. 弱視診斷專家共識(2011年)[J]. 中華眼科雜志,2011,47(8):768.
[3] 劉虎,趙堪興,陳敏,等. 斜視性弱視皮層功能損害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J]. 中華眼底病雜志,2004,20(1):19-22.
[4] Martinez-Conde S,Otero-Millan J,Macknik SL. The impact of microsaccades on vision: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saccadic function[J].Nat Rev Neurosci,2013(14):83-96.
[5] 韓曉梅,趙堪興,錢學翰. 人眼外肌滑車在眼眶立體空間的分布和組織形態學研究[J]. 中華眼科雜志,2005,41(9):821-825.
[6] Jiao YH,Zhao KX,Wang ZC,et al. Detail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 of the ocular motor nerves in Duane’s retraction syndrome[J].J Pediatr Ophthalmol Strabismus,2009,46(5):278-282;
[7] 劉明美,趙堪興,張偉,等. 內直肌與外直肌同時后徙治療后退綜合征的療效分析[J]. 中華眼科雜志,2012,48(9):776-780.
[8] Golnik KC,Motley WW,Atilla H,et al. The ophthalmology surgical competency assessment rubric for strabismus surgery[J].J AAPOS,2012,16(4):318-321.
[9] Zhao C,Lu S,Zhou X,et al. A novel locus(RP33)for autosomal dominant retinitis pigmentosa mapping to chromosomal region 2cen-q12.1[J].Hum Genet,2006,119(6):617-623.
[10] Zhao C,Bellur DL,Lu S,et al. Autosomal-dominant retinitis pigmentosa caused by a mutation in SNRNP200,a gene required for unwinding of U4/U6 snRNAs[J].Am J Hum Genet,2009,85(5):617-627.
[11] Poulos MG,Batra R,Charizanis K,et al. Developments in RNA splicing and disease[J].Cold Spring Harb Perspect Biol,2011,3(1):a000778.
[12] Benaglio P,McGee TL,Capelli LP,et al.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pooled samples reveals new SNRNP200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retinitis pigmentosa[J].Hum Mutat,2011,32(6):E2246-58.
[13] Rose AM,Mukhopadhyay R,Webster AR,et al. A 112 kb deletion in chromosome 19q13. 42 leads to retinitis pigmentosa[J].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2011,52(9):6597-603.